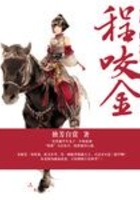来了两个外地牛贩子,一会儿工夫就收了五六头牛,他们把收到的牛赶到一辆卡车上去了,卡车车厢的后面打开来,将一块大木板子搭在上面,跟地面形成一个陡坡,把牛赶上陡坡,赶到车厢里去了。有些牛老实,乖乖地上了车,有些不愿意,扯着脖子犯起了牛脾气,一个劲儿往后缩,恨不能挣断脖子里的绳子逃开去。但是没有一头牛能够实现心愿,几个壮汉子前面拽的拽,后面用棒子打着,牛徒劳挣扎一番,最终还是被弄了上去。一头一头的牛紧紧挨着站立,大眼睛呆呆看着地面上讨价还价的人和犯傻的牛。贩子给马万山出了七千五,马万山要一万一。经过艰难的较量,最后贩子加到了八千五,马万山让到了九千。几个伢子在边上急得团团转,都劝马万山见好就收,八千五已经是最好的价码了。马万山咬着牙就是不松口,贩子问了几回没耐心了,抛下他去招呼别人。马万山眼巴巴扫着人群,他盼望来一个本地的庄稼汉,把这牛买去,养在家里耕地下犊,都是很好的。牛还能多活几年。卖给贩子,牛只有死路一条,而且活不上几天。
他左盼右盼,庄稼汉买牛的不多。有个中年人问过他的牛,他打量对方穿着是个农人,就没多要,只要八千四。但是对方什么都没说就转身走了,看样子并没有买牛的诚意,只是随便问问罢了。
马万山卖牛的过程漫长而熬煎,他在牛羊市场踟蹰逗留着,他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情绪里,纠结着,难以决断。
牛贩子的大车开走了,扬起的尘土高高飞着,又落下,马万山和他的牛站在尘埃里,不远处集市上的人陆陆续续往回走,集临近散去了。他记起今天来的目的,无论如何得把牛卖了,还等着给儿媳买项链呢。
一个本地贩子过来,脸上带着十二分的精明,说老巴啊,您这个年岁的人啥心病我清楚,这样吧,您把牛卖给我,我转给我一个亲戚,他家里刚好缺一头耕地的牛呢,再过两年,您手头宽限了,想买牛时,说不定就会碰上我的亲戚往外卖牛。说不定还给你买回去呢,呵呵,那时候您该多高兴。
他给了八千。马万山摇摇头。但是心里很矛盾。他又加了三百。最后又加了一百。就再也不加了。交易按照乡村买卖牲口的老规矩进行,在衣襟下揣手指头,马万山捏着对方硬撅撅的指头,心头颤抖着,看看天色实在不早了,就答应了。
马万山装上钱,拉着牛犊往回走。
山路的浮土上印着形形色色的脚印,是大家赶集留下的。牛犊突然离开妈妈很不习惯,扯着脖子哞哞叫,走几步回过头看看后面,似乎它知道妈妈被赶到相反的方向去了。马万山不忍心打它,他脚步有些沉重,心里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吃亏了,少卖了钱,而且他知道乳牛不会转到什么“亲戚”手里去,谁不知道那贩子就是个人精,摸准了农人的心思,专捡便宜。然而,他明明知道是这样,但是他宁可把牛卖给他,也不愿意卖给外地贩子。他在心里自欺欺人地幻想着贩子没有骗他,牛真的转到了亲戚的手里,在某一个乡村人家里生活,拉犁,耕地,下牛犊,过着平静的日子。
马万山缓缓地走着,一疙瘩钱揣在怀里,像个砖头块子硌得身上疼,他捏一捏,心里说,我的牛哇,就变成了这个硬块子,唉,想起来就叫人难过啊。
忽然身后传来喊叫声,马万山回头看,几个年轻人追上来,喊着大爷等一等,有个事帮个忙。走近来,是三个半大小伙子,一个手里捏着张一百元的红色票子,说大爷帮忙换个钱,我们着急用零钱呢。
马万山愣住了,下意识地去摸胸口那一疙瘩,说我我我。
一个头发黄叽叽的塌鼻子小伙说行个好换换吧,哥几个急用呢。
一个头发披到了肩膀上的窄脸小伙说别跟我们说您没钱,您刚刚卖了牛,我们亲眼看到的。
马万山慌了,又按了一下胸口。
一个小伙说我帮您拉着牛,把缰绳扯到了手里。
小伙子把钱递过来,马万山接了,一手揭开一扇衣襟,一手伸进去摸钱,摸出一个大砖头块,手指索索抖着要抽出两张五十的。对面的小伙子一伸手夺过钱块子,三个人迅速交换一下眼神,呼哨一声响,三个人猛地蹿了出去,狂奔而去。
马万山傻了一瞬,惊醒了,喊:干啥,你们干啥?抢劫吗?快把钱给我!我一头乳牛全在里头,给儿媳妇买项链呢!你们,你们不能啊……
他疯了一样追赶着。
他在下坡的山路上往前追赶,他恐惧地看见三个小伙子变成了三只兔子,狡猾而快捷地逃窜着,很快挣脱了他的视线,看不见了,找不到了……他栽倒了,吃了美美一嘴土,浮土的味道干爽极了,像烧熟的草木灰,呛着鼻子眼睛,连心肺里都呛满了。
马万山不知道自己追赶了多久,三个小伙子消失了,他还追赶了一阵,在追赶过程中他彻底清醒了,他知道自己被抢了,一头牛的钱全被抢走了。本来他只剩下两头牛,现在一头的钱又丢了,还有另一头牛犊呢,对啊,牛犊呢?可不敢再把它也给丢了。他转过身又跌跌撞撞往回跑,幸好牛犊没有跑远,在路畔啃干冰草呢。他一把抓住缰绳,腿子筛糠似的颤抖着,又转过身往集市方向跑,乡派出所在那里,他得去报案。
天完全黑下来,马万山才拉着牛犊推开家门,一屁股坐在厨房门口喊老婆子给他舀水,说渴死了,舀凉水来。女人舀了一大瓢,他端住咣咣地吞咽,喝完了,说再舀一瓢,还渴。女人又递一瓢过去。他放在嘴边依旧咣咣地吞咽。水从嘴角溢出来,顺下巴淌。湿了前襟和大腿,连脚面都湿了。老婆子端饭来,他推开,说不饿,窝头就睡。第二天,老婆子睁开眼吓了一跳,一夜工夫老汉的头发白了,前额两鬓霜染了一样。
马万山病倒了。
儿子把牛犊卖了,又借了几个钱,凑合着给麦香买了条金项链。
麦香的婚事如期举办,雇了三辆小车来娶亲,每一辆车玻璃上都贴了大红喜字,她的头是理发馆里请来的理发师盘的,还化了个妆,麦香本来长得好看,这一打扮更惹眼了,一套红色喜服,红色短靴,头发高高盘起,别了几朵花,撒了一把彩色塑料屑,红嘴唇黑眉毛粉白的脸,耳垂上的金耳钉闪闪发光,手上一枚黄金戒指闪着金灿灿的光,脖项里一串黄金项链从鸡心领下露出来,配衬得她的肌肤分外细腻。对于她所生活的乡村来说,这完全算得上是一场盛大的婚礼。
麦香嫁过来后公公还病着,卧在炕上起不来。麦香给端吃端喝的时候低着头,不敢看公公的脸。自打公公遇抢的消息传开来,她心里就揣了鬼一样,虚虚的,老觉得事情因自己而起,她有种亏欠着婆家的感觉。她在新婚当夜就卸下了首饰,装进盒子里,锁进柜里,再没有戴。亲戚邻人都夸她简朴,婆婆却不这样看,一次直截了当问她那么跌死绊活地买了,咋不见你戴?难道买回来就为了锁起来。她就又取出来戴了。她觉得最实用的是耳钉,戴上好看也不妨碍干活,最不方便的是戒指,她整天锅灶上针线上活计不少,指头上多了个金黄的箍子,老觉得不自在,生怕被啥挂掉了,又怕磨损了,始终担心着,弄得人一整天心心念念的,她干脆收起来了。
天气热了,就把项链戴出来了,脖子里的纽扣有意不系,露出一段细白的脖子和一圈灿灿的金黄。她怕不小心丢了它,就把搭钩捏得紧紧的。割麦子时,她跟在婆家人身后割,天气热,时不时揭起衣襟偷偷扇扇,汗水把衬衣紧紧吸在肉上。她怀着身孕了,比别人格外吃力些。
有天晚上她睡前脱衣,习惯性地一摸脖子,吓了一跳,项链不在脖子上。这不可能,她起身寻,把脱下的衣裳翻了一遍,每个衣兜都翻了一遍,炕上地下也找了,还是没有。她顿时出了一身汗,打开衣柜,把里面全部腾出来,一寸一寸地翻找,明明记得从地里回来就没有打开过衣柜,但还是怀揣着一线希望,希望自己记错了,顺手把项链接下来放进去了。每一个抽屉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没有找到。甚至连柜底下的一排鞋盒子也翻了一遍。丈夫在父母房里坐了一阵,回来睡觉。问她找啥呢,这么晚了。她忙收了手,装作轻松地说没啥,一苗针掉了,怕扎到人身上所以找找。
第二天来到麦地里,她沿着昨天割过的茬儿细细找,恨不能把每一寸地里的土都捏一遍。她不敢声张,她有一种预感,这事要是说出来,绝对没有她的好果子吃。她心里揣着一坨铁一样沉重,强颜欢笑着参加劳动,麦子割完,拉回来碾了,一直没有见到项链,她终于死心了。
后来婆婆又问过一回,说咋不见你戴金货,买回来就是戴的。她脸上赶紧堆出笑,说自己就是下苦的命,戴那么金贵的东西,总是觉得可惜了,还是收起来心里踏实。婆婆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现在的社会还得了,明知道是个土里刨食的命,还要这要那的,能把人逼死。她听得出婆婆的意思分明是在讥讽自己呢,但是没敢还嘴,她觉得当年项链的事终究是自己一家人理亏。这些年婆婆动不动拿这事敲打,她只能装聋作哑听着。
忽然有一年,男人想和人倒腾个小生意,本钱不够,给她说把你的金货拿出来,我卖了急用,等挣了钱再买新的补给你。
她当下腿就软了,知道再也瞒不住了。幸好婆婆发话说不行,那是人家的嫁妆,嫁妆是女人一辈子压箱底的东西,咋能随便拿出去卖掉呢。
男人就没再提这茬。但是她心里不踏实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香,老是提心吊胆的,生怕有人知道她的项链早就丢了。
她想唯一补救的办法是再买一条回来,和原来那条差不多的。冬天庄里娶了新媳妇,她过去打问了,金子价钱涨了,一克三百多。她算了一下,买一条二十克的就得七千多。她去哪里弄七千多元呢?她一个山村的妇道人家,整天围着锅灶地头打转,身上最多的时候也没超过二百元。啥时候才能攒够七千多呢。
她心里揣着事,就老是不踏实,虚虚的,老是觉得事情已经败露,婆家人知道了,处处含沙射影地作难她。
公公早晨起来站在台子上咣咣地咳嗽,把痰吐在院子里,说现在的人啊,心肠都黑透了……钻进她耳内,心里立时虚了,觉得是在骂绕着弯子骂自己呢。问丈夫,丈夫说,还能骂谁,骂派出所胡所长呢,多少年了,这案子破不了,你说国家养着他们一帮子警察难道是摆设?
虽然不是骂她,她心里还是疙疙瘩瘩的,说到底这事还是和自己脱不了干系。公公等着派出所破案,等了好几年了,每一回去问情况,胡所长都说案子复杂,不好破,那三人是惯犯,到处流窜,一时抓不住,叫他再等等。公公老老实实等着,有人骂他笨,说现在这个派出所长,眼里就认得钱。公公那笔卖牛钱丢得实在窝囊,不甘心就这样不了了之,就拿上三五百元走胡所长后门,希望他早日把案子破了。这样送了好几年,胡所长每一回都喝得醉醺醺,说快了,就要破了,再等等,再等等。公公不敢说什么,回到家心里气不平,记起来就一个人嘟嘟囔囔谩骂。
别人早就习惯了,只有麦香每一回都心惊肉跳的。她不止一次地悔恨,当年娘家人不要中途变卦,强要一条项链,哪会有如今的后患呢。父亲母亲还有姐姐,就知道逞一时的能,却不知道给她身后挖了个坑。她自打嫁到婆家就没法抬起头活人,老觉得心里亏欠着人家,别的新媳妇都是高高兴兴戴着首饰,她看到它们就像心里埋着一堆火星子,这种难受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男人动不动感叹日子艰难,外面挣钱难,恨自己生在了深山沟里的农家,一辈子吃不尽的苦。她听着心里照旧虚,总觉得他在给自己捎话,要她拿出那些首饰来,卖掉了添补家用。她不敢接他的话茬,生怕他提出要看看她的首饰。有一回他直截了当说,把你那些金货拿出来,我给咱掂量掂量看变轻了没有。又说一共是多少克呢我咋忘记了?又说借我看看总能行吧?她的心直接在嗓子门口跳,她不敢张口,生怕口一张心就跳出来。男人不高兴了,说小气鬼,连自家男人都防备着。她还是不敢张口。男人想一想说你给咱好好收着,等到咱儿子,不,孙子手里,最好是重孙子重孙子的重孙子手里,那就值钱啦,变成古物啦。对对,咱现在就是穷死也不能打它们的主意,得藏起来。
男人睡着了,她出了一身汗。
有一天麦香去赶集,在人流中走着走着,一抬头看到一个人面前摆着些五颜六色的玩意。长的链子,圆的镯子,大的小的,黄灿灿的项链,银白色的镯子,啥都有。她呆住了,凑过去看,一个脸膛黑红的男子,穿着藏族袍子,戴着扁形帽子,果然是卖首饰的。她把小圆桌上的一排项链扫了一遍,看到了一款熟悉的。不错,和她丢失的那款真的很像,猛一看简直一模一样,要不是她分外熟悉,她也看不出差别呢。她颤抖着拿起那款项链,通体金灿灿的,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她恍然觉得它就是自己的那一条,一直戴着从未离身,刚从脖颈里取下,还带着她肌肤的温热呢。
多少钱?她迷迷糊糊问。
二十。男子用陌生的口音回答。
她觉得有些晕,难以置信,再问,多少钱?
二十元,一直二十元卖呢,真心想要给你便宜点,十五,十五是最低价。
她觉得有人把她的心揪起来,狠狠摔了一下。
手颤抖着,掏出十五元递了过去。她捏着它转身离开。
一个瘦高个男人也过来买,指甲刮着镯子,问这黄色是铜还是啥?
藏族男子咕哝了句什么。
男人吐点唾沫在上面蹭,问脱色吗,多长时间就脱?
藏族男子说不脱不脱,这是质量好的,别泡水别刮,戴个两三年没问题。
男人问镯子十元钱卖不卖?藏族男子不卖。两人争讨一番,还是以十元成交了。男人把镯子套在自己女人一样细瘦的胳膊上,呵呵笑着说好玩意啊,拿回去哄老婆正好,傻婆娘一定会以为是真金子呢。
藏族男子也笑了,说这个送老婆最好了。
麦香长长出了口气,觉得心里踏实了。这就对了,是铁或者铜做的,才这么便宜,真金子哪有这个价的。
夜里男人和娃娃睡着后,麦香打开柜,拿出从前的首饰盒子,把项链装了进去,合上盖子。过一会儿,又打开来,在节能灯有些寒凉的白光下,她看见项链躺在盒子里,金灿灿的,她眼前有些迷糊,这分明就是从前的那一条啊。
原载《回族文学》2013年第11期
点评
儿童视角、苦难叙述、成长寓言、女性关照一向是与马金莲小说创作密切相关的四个关键词。她的小说无论对黄土地上老百姓苦难生活的描写,对其坚韧品性的表现,还是对无常命运的展示,都深深地打印着西北地区特有的地域特征。
小说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叙述风格单纯、朴素,侧重于展现生活的细节、场景,以小见大地概括出了生活的本质。姑娘出嫁,金银首饰是必备的,而且一般由男方置办。这对收入并不宽裕的马万山一家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为置办婚事,他卖掉三头牛;为给儿媳买“二金”,他又卖掉了一头牛,回家路上,钱却被人劫走;最后,儿子把牛犊卖了,又借了些钱,终于买了条金项链。后来,麦香把金项链给弄丢了,为掩人耳目,她买了一条假项链,放回盒子里。小说构思布局别具匠心,围绕一条金项链展开故事叙述,情节发展可谓一波三折。
这个短篇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莫泊桑名作《项链》。文中的玛蒂尔德是一个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的女人。她因收到参加舞会的请柬而高兴,因没有舞服而懊悔,因参加舞会丢了项链而惶恐,因十年还债而痛苦,而真相是她借的那个项链是假的,可以说,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构成了直接的对应关系。马金莲的《项链》也是以假项链的出场作结,但与前者重在表现女人的贪图享受、爱慕等虚荣人性弱点不同,后者侧重展示乡土地上的人情世态和辛酸生活。尽管作品也细致入微地刻画一个乡村媳妇出嫁、丢项链及买假项链前后的心理状态,但其情感姿态似不在批判,而更多地表现为怜悯。
(张元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