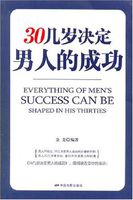和气候条件相比,当地的政治环境更加险恶。龙场驿站是从贵阳府进入水西宣慰司的门户,水西宣慰司处在贵州和四川、云南、广西四省交界之地,其土地东起威清,南抵安顺,北临赤水,西面更是深入四川省境直达乌撒。水西土司分成则窝则溪、于的则溪、化角则溪、六慕则溪、以著则溪、陇胯则溪、朵泥则溪、的独则溪、火著则溪、架勒则溪、安架则溪、雄所则溪、木胯则溪等十三则溪,其中大土司自领“则窝则溪”,其他分别归土司的十二个宗亲管理,号称土地千里,军民四十八万,是整个贵州一省土地最多、实力最强的土司。
明朝建立的时候,派驻当地的都御史马骅曾试图发兵吞并水西,当时的彝族女土司奢香夫人凭着大智大勇化解了这一危机,其后为了表示归顺朝廷的诚意,奢香夫人在其领地上建起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九座驿站,以奢香驿为中心,联结成一个消息传递的网络,使朝廷和土司互通声气,既保证了朝廷的政令畅通,又让中原的文明教化流入水西的深山密林。
水西的大土司是彝族人,但其治下
多民族混居,其中苗族人的势力一向很强。而龙场一带又是汉、苗、彝几个民族杂居之处,其中苗人占大多数。这些苗人既受彝族土司的统治,又遭大明朝廷的欺压,只得结寨自保,逼到急处就会起兵造反。而水西的彝族土司和各大宗亲贵族之间千百年来也一直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血战不断,各族、各寨、各土舍土目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冲突。加之水西宣慰司与普安州相连,而普安又是苗民反抗明军的主要战场,水西土司在朝廷的授意下于普安一带连年交战,在水西土司领地附近又有播州土司、酉阳土司、黎恺土司以及广西南丹、那地一带岑氏土司的狼兵,湖广保靖、永顺一带彭氏土司的土兵……可以说,大明朝西南连续地区各路最凶悍的土司兵马,都分布在水西宣慰司的周边。
就是这么一块错综复杂的是非之地,数十年间,这一带方圆百里战乱不止,小小的龙场驿站,就像这血腥战场中间的一座孤岛,背靠贵阳府城,面对千里蛮荒,仗着朝廷的势力和土司的保证,才能勉强维持下来。在这个地方当驿丞,随时可能染上瘟疫,病死在深山老林,或者不知得罪了什么人而被杀害,又或一不留神被猛兽拖入丛林,或被毒虫咬上一口不治而亡,一个人沦落到此,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是这么一座深山绝谷中的荒凉驿站,仅配置驿卒一名,铺盖二十三副,驿马二十三匹,加上王阳明和他带来的两个仆人,一共只有四个汉人。驿站虽然修了两间土房,可阳明先生是个被贬的犯官,依律他虽然是驿丞,却没有资格住进驿站,只能自己想办法。
面对困境,王阳明束手无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和仆人们一起动手砍树折枝,胡乱凑合着搭了几个齐肩高的小窝棚栖身。然而贵州深山潮湿多雨,几场雨下来,小窝棚全垮了,人根本待不住。没办法,阳明先生只好到附近山上去寻找山洞,不久在驿站附近找到一个潮湿阴森的山穴,当地人管这地方叫“东洞”,虽然阴湿恶臭,好歹还能避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王阳明到这时也无选择余地,只能带着两个仆人钻进洞里安家了。
在这糟烂的破山洞里,衣服、粮食、器具,甚至人的手脚上,没有一处不发霉的,潮地方睡久了腰酸腿疼,咳嗽不止,王阳明本来就身子弱,年轻时又因为不爱惜身体,得过比较严重的肺病,要是在这阴暗潮湿的山洞里住几年,非落下一辈子的病根不可。在洞里住,还真不是个长久之计。
生计艰难倒在其次,对王阳明来说,自到龙场驿站,最难捱的要数这一天到晚无穷无尽的寂寞。
龙场驿站设在荒凉的大山深处,一年到头没有一件公事,寂寞像一条蛇紧紧缠在人身上,乏味到使人没有一丝想头儿。
深山里一年难得见到几个汉人,就这仅有的几个汉人又都鬼鬼祟祟弄不清来历,王阳明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些人。周边虽有几座苗寨,可苗人和汉人素来不和,对驿站上的人冷眼而视,从不往来。当地很穷,又经常打仗、仇杀,人口稀少,粮食短缺,有银子也未必买得到,何况阳明先生身上也没多少银子,弄得三个人经常吃不饱肚子。仆人们虽然想过这趟来贵州怕要吃苦受罪,却没想到把罪受到这个地步,在阳明面前难免抱怨几句,说出来的话很难听。
此时此地,王阳明也没有办法,只能以清高淡化困苦,用穷酸调剂孤独,写诗安慰自己:“岂无数尺榱,轻裘吾不温?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
橼子数尺长的高级房子就别想啦,轻裘看来也是穿不上了,在这个破山洞里睡得好不好,身上暖不暖?阳明先生自己知道。至于说要跟“箪食瓢饮”的颜回比一比心态,阳明先生觉得眼下在这么个破山洞里窝着,又艰涩又委曲,说不出的凄美,道不尽的清高,真有资格跟颜回比一比“清苦”了。
原来初到龙场的时候,阳明先生竟是在用自怨自艾、自伤自怜的消极方式排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在这位未来的心学宗师身上,竟是一点积极因素都没有表现出来。
儒生们的审美观念自古就有一种奇怪的病态美,而这种病态美的最佳代表人物就是孔子门下那位贫穷的弟子颜回。阳明先生很喜欢拿自己比颜回,在京城坐牢的时候就这么比过,现在困居龙场时又说同样的话。其实稍稍分析一下,他和颜回并没有多少可比性。
颜回这位春秋时代的古人是个平民百姓,他的穷是真穷,所谓箪食瓢饮居陋巷,颜回一生过的都是这种日子。可阳明先生实在不“穷”,是个官家少爷出身,家大业大,被贬了官到龙场来受罪,还带着两个仆人伺候他,所以王阳明的“穷”是装出来的,他其实是受不了这份穷困。
颜回虽然穷,却不改其乐;阳明先生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却是满腹牢骚。
颜子穷归穷,毕竟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至陷于绝境;阳明先生如今陷在深山野洞里,一条性命朝不保夕。
再说颜回虽然穷苦,身边还有孔子这位老师,以及一帮同学朋友讲论学问,互相帮助。王阳明独居域外,只有野猪野鹿来看他,从中原逃出来的流民偶尔来“访”他,说穿了就是这些穷苦人没了活路,跑到驿站来弄点吃用,占些便宜,而阳明先生性情又太清高,瞧不上这些穷苦的人,和同是汉人的“亡命”之人没有话题。正是吃没得吃,穿没得穿,住没得住,想没得想,自己把自己的活路一条条都堵上了。
据阳明的弟子后来说,此时的王阳明似乎对自身荣辱渐渐不再重视了,可是对“生死”二字却还不能看透,就弄个“石椁”,躺在里面反思,但反思了很久也没有结果。其实以王阳明现在的处境,哪里弄来一个什么“石椁”?他分明是把自己住的这个山洞比喻成了一个“石棺材”罢了。
躺在“石棺材”里的人,就算是个“活死人”了,两只脚还踩在地上,半个身子却已探进了死路。就是在这么个石头棺材里,王阳明被迫对“生死”二字做一番深刻彻骨的思考。只可惜,“生死”这个题目太大了,光靠坐着发呆,是不会得出什么结果来的。
那么,此时的王阳明真的把“荣辱”看淡了,只剩“生死”二字还参不透?
从精神层面来说,“生死荣辱”四个字是一体的。荣指有信心,有目标,有动力,也就是生气勃勃;辱指受了挫折,失了信心,没有目标,缺乏动力,也就是死气沉沉。王阳明现在不提荣辱,却提生死,其实是他对“荣辱”二字看得太重了,在“信仰”这一方面的疑惑太深了,以至于上升到了“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高度。
像这样一个因为愚忠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他的人生目标已经失去,自信心已经垮塌,在龙场驿站这么一个荒凉偏远、实际上已被朝廷抛弃的地方,他生活的动力也已经消失殆尽。王阳明现在考虑的并不是“生死”二字,而是一个无法突破的“死结”。
所以阳明先生在深山野洞里枯坐的时候,说出了一句非常绝望的话:“吾惟俟命而已”——只是等死罢了。
躺在山洞里等死的时候,阳明先生写了一首《去妇叹》,借别人的事说自己的话,写得好不可怜。
委身奉箕帚,中道成弃捐。
苍蝇间白壁,君心亦何愆?
这哪是“去妇”诗?分明是“弃臣”王阳明在向皇帝撒娇呢!
感此摧肝肺,泪下不可挥。
冈回行渐远,日落鸟群飞。
群鸟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初到龙场的王阳明竟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难怪他要躺在石棺材里等死了。
在困居龙场的时候,王阳明的情绪如此颓丧,如此糟糕,那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的思想忽然发生重大转变,以至于一夜悟道?是长时间思考,精诚所至?还是像他的弟子们说的那样,“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有神仙托梦告诉他的?
都不是。
关于龙场悟道,所有资料都把它解释得很含糊,甚而有些人把这一事件神秘化了,说王阳明静坐沉思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他身边耳语,于是豁然开朗,洞悉大道,以至纵声长啸。这些人也许是不知道“龙场悟道”的真境界,又或是想用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把阳明先生捧成“圣人”,让后人崇敬他,进而崇奉心学,但为了传播学说而造假、造神,其实没什么意思。
实际上龙场悟道本身没有神秘之处,而是一股看起来实在不起眼的力量拯救了王阳明,这就是:跟他一起来龙场的两个仆人病了。
这两个仆人从南京一路追随阳明先生来到贵州,是来侍候这位公子爷的,可这一对“祥瑞”却显然没想到龙场的生活条件竟是如此之差,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加上“瘴气”的影响,两个人先后病倒了。
按说仆人的身体应该不比阳明先生更差,可王阳明还没有倒下,仆人倒双双病倒了。说到底,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平时不读书识字,他们的精神世界过于贫乏,文章诗词一概不通,《易经》、《坛经》一律不读,他们没法像王阳明那样用各种“穷酸办法”去应付面前的困难,结果心里的烦躁怨气愈积愈重,时间一长,两个仆人都被自己的坏情绪压倒了。
对王阳明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龙场气候炎热,瘴气横生,瘟疫多发,又无医无药,外地来的人病死的极多。王阳明自己是个“罪臣”,被贬到龙场来受罪,就算病死了也没有办法,可仆人们并没有罪,只是跟着来伺候他的,如果病死在龙场,王阳明的良心将会永远不安,如今他只有用尽一切力量照顾他们。
服侍病人,不但要处处动手,更需要事事用心。王阳明是个傲气十足的公子哥儿,从来不用做那些杂事,更不懂得用诚心对待下人。现在事到临头,心里的良知逼着他不得不事事躬亲,时时用心,平生第一次学着煮饭、熬粥、服侍别人,关心呵护,问寒问暖。看到仆人意志消沉,就跟他们讲论文章,或者念几首诗给他们解闷。
然而,诗词文章是公子哥儿的玩物,仆人哪有这样的雅兴?根本不爱听他谈诗,也听不懂,王阳明就改了主意,不讲诗文,改成唱歌唱曲,唱余姚小调滩簧腔儿。在这些市井快活上,阳明先生会的不多,很快就没词儿了,只得又搜肠刮肚去编些笑话,总之就是想逗仆人一笑,缓解他们心里的压抑情绪。
许是侥幸,在王阳明的认真照料下,仆人的病倒也慢慢好了起来。
这是王阳明这位贵公子一辈子第一次这么努力地为别人、尤其是为下层人着想,如果他仍然是礼部左侍郎的公子、朝廷里的六品主事,或是一个退职回乡闲居的庄园主,他都永远不会这样做。这一年阳明先生三十七岁,在此之前,他的诗文不可谓不精,学养不可谓不厚,但阳明先生在前面三十七年的人生中只能说一事无成。而现在,就在这荒僻孤寂得像坟墓一样的龙场,在替仆人煮粥做饭,挖空心思只为逗仆人一笑的过程中,王阳明却感受到了自谪居龙场以来所未有过的充实、轻松和快乐。
阳明先生的整个思路,就是在这个节点上转向正常的。
在和仆人们像朋友一样交往的过程中,在照顾病人、煮粥唱曲说笑话的过程中,他忽然明白:原来孔子一直提倡的“仁”,儒家学说奉为至宝的“仁”,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到极点的意思。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他是为自己活着,同时也为天下人活着才对。人生的意义,就是对内实现自我价值,对外服务他人。
王阳明这个正直勇敢、博览群书的才子,就是在与仆人交往的过程中,悟到了孔夫子所谓“仁者,爱人”的真谛!用阳明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这就是王阳明在地狱一样的小山洞里自问自答,给自己寻找出的人生答案。也就是传说中的“龙场悟道”。正如王阳明在《传习录》里总结道:“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如此看来,王阳明前半生的道路全走错了,初到龙场时的想法也错了。以前的阳明时时刻刻想着依附于人、追随于人,从没有自己的主见,也不问本体之良知。现在他才明白,原来“良知不假外求”,每个人在思想上都是平等的、独立的、自觉的,这世上没有什么“弃妇”,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不抛弃社会,不放弃希望,抱定一颗“仁者”之心,就不存在“被抛弃”一说。
当悟到“良知不假外求”的真义时,很多压抑在心底的谜团也就解开了。王阳明在一瞬间感受到了思想爆发的极度快乐,快活到了极点,忍不住纵声长啸,把已经睡下了的仆人们吓了一跳。
龙场悟道,悟到的是一个“仁”,是一个“良知”,一个不假外求的“自我”,这些体悟使王阳明的灵魂得到解脱。后来,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里写下了一段有重要意义的话:“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里的话,被古人认为是从尧舜禹时代起就代代相传的“十六字真言”。对这“十六字真言”,古人解释颇多,内容驳杂,而王阳明竟以“惟务求仁”四个字对这上古“真言”做了最杰出的总结,他理解得既简单精准又富有意义。
在写给儿子正宪的《手墨二卷》里,王阳明更加简明扼要地说道:“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之可致矣。”也就是说,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良知”与“仁”是相同且相通的,不能体会到“仁”的内涵,则“致良知”的工夫也无从做起。
良知,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有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一个人才能真真实实地领悟良知。一旦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古代哲人所推崇的“仁”、“义”、“理”诸多概念,在阳明心中就都能融会贯通了。
激动之余,王阳明在阳明小洞天里写了一本《五经臆说》,把自己对于五经四书的一些想法全都写在里面了。
可惜《五经臆说》并未流传下来,后来王阳明和弟子们讲起自己在龙场悟道的经历,提到了这本奇怪的小书,学生们立刻提出要看这本书,王阳明笑着说:“已付秦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