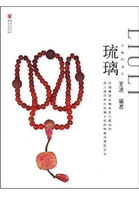本文提示
论点:赵壹并非“专事抨击草书”,而是反对当时习草中的不正之风;也不是“对从事草书研习的人们进行猛烈抨击”,而是反对那些“不思其简易之旨”的“今之学草者”。
论据:有六条:(1)赵壹在草书起源上,观点是正确的;(2)他对草书的实用功能是予以肯定的;(3)他提出正确艺术个性早于曹丕;(4)对草书的功能给予“贵”和“赞”的评价;(5)“故不及草”是赵壹捍卫草书原则的具体表现;(6)赵壹把张芝、崔瑗、杜度和“不思其简易之旨”的习草者是区别对待、区别评价的。
结论:赵壹不是笼统的反对草书。
名著《非草书》问世以后,一直被视做异说,被认为是赵壹站在“弘道兴世”的儒家立场上,对“背经而趋俗”的草书张旗征讨的一篇檄文。“自量可以比于虞、禇而已”的张怀瓘供奉就在其《书断》一文中即称“赵壹有贬草之论”,从而开创了千余年来赵壹否定草书说之先河。后世从其说者众矣!近数十年来,仍有著作认为“《非草书》一篇,专事抨击草书”,“《非草书》一文的确达到了对草书和从事草书研习的人们进行猛烈抨击的目的”。“像这样一篇反书法的文章,从书法发展角度看,是与历史进程完全背道而驰的。”
认为《非草书》是抨击草书的论据,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据文中“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句,认定赵壹“信奉的谶纬学神话传说,认为文字起源于河图洛书”和“反书法宗旨”“草书‘非圣人之业也’与他所崇的‘圣人’是无缘的”。
——列举“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的楷”为证,认为赵壹是用仓颉、史籀否定长于草书的杜、崔。
——“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善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以此为据认为赵壹把草书视做雕虫小技,把习草之人视做无能小人。
——“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等等。
《非草书》的本意,果真是专事抨击草书和反书法的吗?笔者以为尚有商讨的余地。
第一,赵壹在《非草书》一文中,以其进步的历史观,对草书(注)产生的起因作了精辟的、符合事实的论述。“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它认为,草书的产生确实“非天象所垂”、“非河洛所吐”、“非圣人所造”,而是以社会活动的客观需要为基础的。这段记述,作为《非草书》全文立论的根据,及其在结构上所起的作用,作为辞赋家的赵壹,注:目前书学界普遍认为《非草书》所论述的指章草,而史学界如范文澜先生以为是今草,张怀瓘亦认为“张芝变为今草”(《书断》)。存疑,此不影响本文之论述。
不会无以所思。实际上,他在该文中引用崔瑗的话已作了正面回答,“故其赞曰‘临事从宜’”。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独特的人文背景,常将物质和精神的某些产品,归于某一圣人的灵机一动。书法的起源也是这样,常归于“眺彼鸟迹”、“依类形象”等天象地理、飞禽走兽的观察启示,抑或归于伏羲作图、仓颉造字、李斯构篆、程邈写隶等个人所为。对于自然景观在中国文字及书法发展史上的启蒙地位,个人在书体演流中所起的作用,自然不应否认。赵壹的卓绝之处,就是将草书产生的原因置于广阔的社会活动基础之上加以考察。在《刺世疾邪赋》中,赵壹即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他以这种进步的历史观观察草书的兴起,既前无古人,又后启来者。其后,萧衍在《草状书》中即谈到“昔秦人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正是对赵壹草书起源说的继承。
抨击论者以“上非天象所垂”之“三非”句为据,得出赵壹是“反书法宗旨”的结论,完全是南辕北辙,实际上,“上非”三句,虽然是一个(对草书)肯定判断语句,但它是对其上“其于近古乎”问句的回应,也是为下句补叙张本,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判断句。“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见”句,是相对“上非”三句而言。“非圣人之业也”和“上非”三句正好相反,是一个独立判断句,它是对“盖秦之末”句的结论。所以“上非”三句与“盖秦之末”句在文意上和文章结构上都是相关联、相统一的,不能舍弃“盖秦之末”句而孤立地以“上非”三句为据。这里,对“盖秦之末,……示简易之指”段的描述,这一客观事实(判断根据)是否予以承认,至关重要。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无论对《非草书》一文持何种态度,但对这段记载,均认为是真实可靠的。所以把“上非”三句和“非圣人之业也”独立地抽出来以为其据,是不能成立的,也不是赵壹的本意。
第二,对草书所具有的实用功能《非草书》是予以肯定的。“删难省烦,损复为单”,“草本易而速”,“趋急速耳”,这些对草书功能的自觉描述,在书法史上是比较早的。它明确指出,草书解决了以前诸书体所无法解决的“写书速度”问题,这是实用功能;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提出了“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和“学步失节”的问题,这是审美功能,待述。每一种字体的出现、发展和确立,包括书风的形成,都有它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中国书学和文字发展的整个历史表明,书法、文字是一个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往复过程,后者对前者既否定了繁琐、难写、不合时宜的部分,又保留了它的基本特征、可读的连续性。草书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展现,正是这个不断变化着的历史链条上的一环。赵壹从主观上,笔录了这一历史进程,在客观上,从一个侧面阐述了简繁互变这一发展规律,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第三,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提出了草书的审美功能和书家的艺术个性问题。一般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艺术的自觉时期,其标志之一即开始重视艺术个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即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所致。”这里所谓的“气”,即艺术个性。应该说最早注意(书法)艺术个性的,是赵壹。他在《非草书》中即强调:“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强烈的艺术个性,必然产生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为赵壹赞赏的杜、崔、张子之草书,即属一例。同时,赵壹对不具艺术个性、勉强而为的人,予以无情地批评和讽刺,“西施以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一方面用西施捧胸之颦,喻指草书的静态之美,用赵女舞姿之媚,喻指草书的动态之丽;另一方面,对于装模作样、毫无艺术个性的“众愚”和“学者”那种“只增其丑”、“失节匍匐”之态予以揭露,接着在“夕惕不息,仄不暇食”一段中,又给以无情的讽刺。这些都反映了赵壹对草书的艺术特征和书家的艺术个性的重视。
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节”字。言“失节匍匐”在前,写“学步者之失节”于后,前者言失赵女舞步之节,形如匍匐,后者云无益于草书工拙,徒增其丑。节者,法则也,这里是指美的法则,其内容若何?《非草书》未于匡订。但它已与文中之“旨”、“楷”等精神一起,构成了赵壹认为的草书应具有的法度和原则。
第四,赵壹对草书的功能不是述而不评,恰恰相反,是予以歌颂和称赞的。《非草书》写道:“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故其赞曰‘临事从宜’”。此不仅是对崔瑗及其《草书势》的评价,也是赵壹对草书的态度。对“删难省烦、损复为单”给予“贵”的评价,对“临事从宜”赋以“赞”的美誉,可谓至矣!他在批评不遵守草书法度时评道:“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查,“指”通“旨”,具“美好”意。这难道是赵壹“反书法”“专事抨击草书”的吗?
第五,“故不及草”亦是赵壹捍卫草书原则、“惧其背经而趋俗”的又一笔证。全句是“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言少年儿童的习草,任意凑合,不按部就班,私下相赠,几乎独自随意书写,还说是“适应急速”、“故不及草”,这样是达不到草书要求的。不是说“故不宜草”、“故不应草”,而是“故不及草”,赵壹对草书应有一定法规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文章的后半部分叙及,“今之习草者”虽然“十日一笔,月数丸墨”,“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其对草书所持的态度与“故不及草”起着异曲同工的评价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钱钟书先生在论及《非草书》时,有过精辟的描述:“盖草书体成法立,‘旨’虽‘简易’而自具规模,‘趣’虽‘急速’而亦遵格式,必须省不失度,变不离宗;结构之难,今日犹然。”接着,他又写道:“夫张芝,‘草圣’也,赵壹推为‘有超俗绝世之才’者,……‘今之学草书者’学焉尚未能,恐仓卒下笔反失故我,遂以‘不及草’为解。”这是对不守草书法度习草这件事的指评,也是对不守草书法度的人的指斥。
第六,赵壹对张芝以及杜度、崔瑗是十分尊重的。谓“有道张君”、“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杜、崔、张子,皆超俗绝世之才,……后世慕焉!”显然,他认为这些人是当时草书界之代表,而对“今之学草书者”斥以“不思其简易之旨”,“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的“众愚”,一褒一贬,界限分明。
《非草书》中所说的“后学之徒”、“今之学草书者”、“众愚”、“学(舞)者”、“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等,就是指这些不守草书法度的人,并非指杜、崔、张子,因为他们被赵壹划在“超俗绝世之才”的范围。“今之学草书者”这部分人与杜、崔、张子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同。东汉末年,这部分人属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士君子集团”。当时致仕的途径大致有三:一是公府辟召,即三公等大官特聘著名士人做本府的属官,赵壹就是这样郡举为上计吏的;二是郡国荐举孝廉到朝廷,考试合格后授以官职;三是由下吏积资递升。在“今之学草书者”中,大部分是无所政治依靠的所谓“有市籍地主群”,他们在做官前不但受到官僚和无市籍地主集团的压迫,同时还受到下层豪强、地方宗族的歧视,在致仕的道路上常常是苦伴青灯,自力经营,竞争十分激烈,社会上稍有新艺,便蜂拥而至,以求先他人掌一技之长。赵壹用大段文字描述的就是这些“夕惕不息,仄不暇食”的“草书之人”。一方面由于这些人政治地位的低下,另一方面草书的社会地位尚未确立(不如秦诏印之用篆、汉诏书之用隶),所以“伎艺之细者”是整个的社会观念,不足为奇。蔡邕亦有“书画辞赋,才之小者,非以教化取士之本”之论,所以“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只不过是对当时社会意识的真实情况作了客观描述而已,不能以此就说赵壹“对草书和从事草书研习的人们进行猛烈抨击”。
在这里须作说明的是,赵壹对“今之学草书者”,“草书之人”的看法是当时社会观念的反映,对这种人群广泛参与草书活动现象,其客观社会效应和在书法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应予肯定。
在“反书法”观点的论据中,有一条颇使读者迷惑,这就是列举“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句为据,用仓颉、史籀否定杜、崔。和反书法论者的其他论据一样,这仍是没有从《非草书》全文的本意上去把握赵壹的意图。张芝和赵壹是同时代人,如前所述,赵壹对张芝是很尊重的,并把杜、崔与张子视为一体。中国书法各体,虽几经变化,然其脉相承。史籀的籀文与杜、崔之草书均具有字体象形,单字单音,词由字合的共同特征,二者一脉相承,均是音的符号,也是美的表征。因此“皆废”句与“竟以”句应是相容的,至少是并立的。否则无以解释他对杜、崔、张子的赞赏。所以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不能孤立地以杜、崔为楷,应该从学习史籀的基础方法开始,否则,就达不到习草目的,“故不及草”。
据上所述,笔者认为,赵壹对草书是持以肯定的赞美的态度,并非“反书法”,更非所谓“抨击”。
《非草书》有无抨击之意呢?曰然。然抨击的不是草书本身,而是习草中之歪风邪气以及其人。“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因为在“简易之旨”之下,紧接有“杜、崔之法”与之相应,所以其“旨”有“法度”意。“直以为杜、崔之法”句,一向被持抨击论者作为赵壹否定草书之据,笔者以为正好相反,是赵壹肯定草书之雅态。何矣?关键在一“直”字之解。不能把“直”字作“用”、“直接”解,如作此解,亦即作否定意解,便与其上下文意势将抵牾,上者,有“示简易之旨”、“贵删难省烦”、“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这些对草书肯定的评述,下者有“龟龙所见”的判断,所以“直”字应作“简单地、机械地”解,意犹“简单地(机械地、呆板地)运用杜、崔的写字方法”只求形似,不仰神同。只有这样,方能在“杜、崔之法”与今之学草书者的“不思其旨”之间,形成对立之势,方有“龟龙”之区别和“龟龙所见”之结论。前后之意遂以贯通。此其一。其二,对于那些“效颦、学步”者给予揭露、讽刺。《非草书》曰:“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如前所述,在这里赵壹强调的是书家的艺术个性问题,是书画艺术欣赏心理(心)与艺术创作技巧(手)的关系。艺术欣赏心理与其主观审美意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涉及艺术家的综合修养。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只是一种载体,所托载的是书家的胸襟、气度、学问、抱负。未有胸无点墨,见解鄙陋而成为书法家者。赵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讽刺“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才着力称赞“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若舍其“博学”,专在书法上“游手于斯”,即使“十日一笔,月数丸墨”,充其量只能成为写字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就书法练书法的现象,在当今书法界也不鲜见。此正是赵壹所云“余惧背经而趋俗”之本意,“经”亦在此,“俗”亦在此,何谓背道哉!
赵壹对舍本求末、“专用为务”者大段的、带有讽刺性的描述,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惜的是,抨击论者把这段描述作为反书法的根据,显然是有悖于赵壹本意。
其三,《非草书》有“其攒扶拄嫂,诘屈及乙,不可失也”句,查,在《辞海》、《辞源》中均无诸字,《康熙字典》仅录无解,钱钟书先生述及此句时亦无解说。《中华大字典》释为“同弯”。已往诸多书论中,对此句漠然不于提及,抑或提及不释其意。但是,此句正是赵壹对习草中的歪风邪气的痛恨。要阻止旁杂(扶),抵挡(拄)冲击,禁止(诘)邪道(屈),铲除小秽(乙),不可坐失良机。
赵壹的这篇文章,最早见于晚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文章命以“非草书”为题,是题目为赵壹本人所命,还是张爱宾以冠,抑或汉末至元和之间他人所加,尚无法认定,留待今后考证。
本文乃以文论文,将书论书,意在论证赵壹不是笼统地反对草书,而只是反对那种不思其旨反失其节的草书;不是笼统地反对书草之人,只是反对那种“今之学草书者”和效颦的学书者。
本文也没有涉及《非草书》的政治影射。东汉末年,朝廷软弱,群雄异起,官宦斗争更加表面化;书学界经过鸿都门学事件之后,经学传统集团与士君子集团的矛盾愈加尖锐,这是历史事实。赵壹是一个关心时政的政论家和甚为著名的辞赋家,“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政治上“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其完成赴京呈文任务后西返途经弘农求拜太守皇甫规时,连门卒都不给他予以通禀,可见其一生之坎坷,其嫉世妒俗之情在《非草书》中有所寄笔,自不可免。近有章建明、钟明善等先生均有明鉴昭世,颇有见地,笔者深以为是。
为写此文,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有些论文、著述所列资料与史实相去甚远,如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书法史教程》写道:“蔡邕是魏晋时期书法的第一代表人物。”(第36页),《中国书法》1998年第4期第78页在引用《非草书》“人无其衅”时写成“人无其爨”,并解释“爨,即瑕隙之意”,看来并非笔误,二字形似而意远。面对诸如此训,笔者深以为憾,缘因读者有误解作者原著之忧。
在本文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书协副主席、西安交大艺术学院钟明善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志慧教授指教,在此谨致谢意。
1999年1月于西安长庆
参考文献
[1]张怀瓘:《书断》,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06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3]李沅和:《非草书》价值管见,《书法艺术》1994年第四期,第37页。
[4]陈振濂:《书法史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5]江世龙:《谈〈非草书〉的潜在美学价值》,《书法艺术》1992年第2期,第85页。
[6]《辞源》修订本,1980年8月版,第1253页。
[7]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第108条。
[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65年第二编,第140页。
[9]《后汉书·蔡邕列传》,中华书局第1997页。
[10]姚淦铭:《钱钟书的古代书论研究》,《书法研究》1992年第3期,第85页。
[11]章建明:论赵壹《非草书》,《书法研究》1987年第3期。
[12]钟明善:《中国书法史》第五章。
[13]王玉池:《赵壹〈非草书〉》及其在书史上的意义,《中国书法》1983年第1期。
[14]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二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版。
[15]王继宗:《草书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