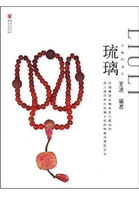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序张葆荣《书画论文集》
张葆荣先生是半个多世纪之前我在西安市二中低年级的同学,在校时彼此知道,但交往不多。后来,他和我都曾就读于陕西的百年名校西北大学,我学中文,他学地质,隔行如隔山,中间又有数年的时差,不记得在学校见过他没有。我提前一年毕业,留校做过助教,但1959年即负笈京华,后又留京工作。他毕业后,则长期在地质石油勘察和科研岗位效力,多有贡献。只是人海茫茫,天各一方,绝少互通音讯。
前些年回陕西省来,我们在蔡克勤老师家里相见。蔡老师是我念高中时的班主任,后来也带过葆荣他们那个班。老师早已年届耄耋,而他的两个学生也是不敢言老的“华甲之后”了。葆荣不像我似的霜雪覆顶,满头黑发中仅见数茎白发,不细心看不见,稍瘦,但硬朗,镜片后的眼光,很见神采,一看就是书法家才会有的那种身板,筋骨内敛,气脉贯通。
蔡老师家的客厅里,挂着葆荣的一帧大幅书法作品,是工整的楷书,书风瘦劲清丽,秀润而见风力,颇能见出长期临王习柳的功夫。那次见面,他送我一本他的诗集。闲谈中,说起邵燕祥一首悼念伟人的七律和我的步韵和诗,不想他在不久后即将此二诗作成大帧书法贻我,清劲而见气骨,出沉郁。使我异常感动。
前些时,葆荣要把他的书画评论和文艺美学论文裒为一集出版,打电话邀我为序,并寄来部分入选篇目和有关资料。我以杂事应酬太多,很拖了些时日,让他着急,很觉歉疚。好在读完他的文章,看了别人对他的介绍和评论,觉有话要说,恰好这两天有空,也就可以了却这笔文债。
我很佩服葆荣能长期在繁忙的科技研究和管理工作之余,钻研书法,不仅坚持创作,而且进行理论思考,研究书法史上许多疑难的公案,在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并进行认真梳理之后,写出考辨文章,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把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结合起来的方法,是尤为难能可贵的。这种结合的好处是,既不会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鲁莽家、写字匠,也不会成为只有嘴上功夫的“天桥把式”,或鲁迅先生所不屑的空头皮的理论家。
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它既有技艺、技术的层面,更有文化意蕴的层面。从技艺、技术的层面看,没有从“上大人孔乙己”描红开始的长期艰苦的临摹和训练,即所谓“笔成冢、墨成池”,是很难达到熟稔圆练的程度的;从文化意蕴的层面看,书法艺术又反映着书家的主体人格、文化素养、气象胸襟等等,可以说“功夫在书外”。自古书家讲风骨,讲气韵,讲格调和境界,都与主要着眼于文化意蕴层面相关。在葆荣的书法理念和创作实践中,对于上述两个层面的关注,以及对后者的更加侧重,都是相当自觉的。那证明,就是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
书法作为艺术,有着久远的文化历史承传,葆荣对于书法史的研究,是取一种辩证分析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既看到恒久生命力的积极的主流,也不回避由于历史局限而确实存在的负面的东西。所以,在对古代书法研究的论文中,他坚持的原则,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切从实际出发。比如《论〈非草书〉之本义》是一篇论辩文字,意在澄清从古到今认为赵壹“否定草书”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葆荣从细读《非草书》文本出发,把赵的论说,放在当时具体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结合赵壹的全人,进行仔细的分析,得出“赵壹不是笼统的反对草书,而只是反对那种不思其旨反失其节的草书;不是笼统的反对书草之人,只是反对那种‘今之学草书者’和效颦的学书者”的结论,令人心服。
《王羲之与顾恺之》是对晋代一位伟大书家和一位伟大画家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文学研究与艺术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比较,寻绎对象之间的异同,引出规律性的结论来。在风格研究上,为了把握艺术家或艺术流派风格的独特性,常用比较之法。王羲之与顾恺之,虽一个做书,一个做画,但中国书画同源,故还是有可比性的。葆荣的这篇文章,在介绍二人基本情况的前提下,比较了二人的异同,而特别提出王羲之的“意”和顾恺之的“神”,加以发挥,是文章的出彩处。
特别应该一提的是葆荣《关于圣教序》的长篇论文。这篇文章,以丰富的资料,细密的梳理,精审的辨析见长,对唐沙门怀仁的《集王书圣教序》的由来,怀仁法师对《集王书圣教序》的贡献,《集王书圣教序》的历史功绩和历来的评价,都提出了很到位的分析与判断。其中,利用现代科学统计的方法,列表比较了《集王书圣教序》与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的字数分布,尤为可贵。读了这篇文章,即使对《集王书圣教序》毫无了解的人,也会得到明晰的印象。
书中还有一些关于书画艺术的审美特质的论文,如对灵感等问题的思考,也都值得一看。总之,读了葆荣提供给我的这本书画评论集的书稿,感到很高兴,比我原先预想的要好得多。他不仅是书法家,还是评论家和长庆油田乃至石油文联群众书法活动的组织者。我以有他这样一位学弟而自豪,丹青不知老将至,祝您健康长寿,创作更多的作品,写更多的美文。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二日 六砚斋
何西来:著名文学评论家、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顾问、原副所长兼《文学评论》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