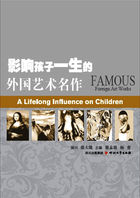在当下背景中,体制改革推进和理想化的创作之间,有几个关乎创作发展的问题特别明显,需要认真思考。第一个为强权论。随着市场主宰的加大,市场化越来越开始完全无视艺术内容的表达而强制取舍,这对于艺术创作形成明显的冲击。越来越多的艺术电影被影院经理简单的一句话(市场判断)排斥掉,这就叫市场化的强权论。第二个为计谋论。我们现在尚不健全的体制,还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体制建设,难免遇到市场和主观意念双重枷锁的左右。当要求电影必须挣钱顺服市场时,从宏观指导到创作机构都异口同声,忽略了创作的差异和市场的分野。完全拿市场和挣钱来要求文化产品的绝对衡量显然不是良策。但有的时候又按政策抉择取舍,以不符合规则来定夺,形成一些时候的双重枷锁,称之为功利性的计谋论,这是体制改革进程中必须正视的矛盾。第三个为人心散论。在为了迁就评奖、市场、政策等诸多因素间,经常可以发现,被现实市场威压之后,创作者有时自主丧失了创作自由意识和独立表达的多样性,有些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甚至预设好几个结尾,针对预审官员或影院经理,艺术创作没有主见的情况称之为人心散论,显然是艺术创作中的危险倾向。第四个是无是非论。随波逐流朝云暮雨的现象在大众文化潮流中日渐明显。创作市场的威压和人心历史矛盾产生了2007、2008年中不少评价的前后颠倒的状况,造就突出的言语评论矛盾。诸如《色·戒》的创作几个波潮的批评逐步上纲上线,而对于《集结号》的认识也差点演变为根本性评价,尤其是从对《集结号》开始对集体牺牲的责难,到对艺术表达悲剧的责难等等,体现了创作面对的环境的复杂性。第五个是新媒体威胁论。无需避讳,电影遇到强劲对手数字媒体的威胁,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传播方式,网络所代表的新兴媒体将极大改变对应的创作和传播,难以预测得失几何,但创作不能不考虑如何应对越来越巨大的网络下载给予电影市场的压力,创作也不能不考虑网络创作给予年轻人欣赏习惯和参与意识的改变。
总之,在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和创作发展关系的探究中,我们需要更为宽阔的思路,既要坚持艺术内容的把守,也不能无视市场体制和环境的某种决定性作用。
华语电影:世纪性文化整合及其当下的现代性抉择
——兼论21世纪初全球化与本土化之抗衡及其必然的历史走势
黄式宪黄式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一怎样看待电影这个“文化舶来品”?
电影是自西方引进的一种文化舶来品(也是现代科技文明的产儿),在中国的“国粹”里是断然找不到它的光与影的;倘若以“皮影”说而为自己的“国粹”增添某种敷粉的“尊严”则显然是很无趣也毫无意义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的“入乡随俗”,在电影“舶”入中国后这一百零几年的历史衍进中,它一层层地被濡染并渗透进了我们华夏文化的民族内涵及其底色,它事实上正日渐被我们华夏民族文化所吸纳、所同化,由此而萌生出东方华夏文化的民族风情及其无可替代的民族精神的风采。
在华语电影百年来的历史长河里,好莱坞电影(从短片到长片)自1914年后大量输入中国,无疑扮演的正是一个文化入侵者的角色,随之也将美国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输入了中国;与此同时,在客观上好莱坞也对我们早期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制作带来了一定的文化启蒙和艺术借鉴,并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形成给予了有益的影响。但是,好莱坞电影产业的主体,从来都是以文化霸权形态将中国作为资本扩张的对象国的。
在中国电影新百年伊始之际,我们与好莱坞博弈的棋局,其严峻性显然并不是可以让人掉以轻心的,甚至可以说,在21世纪初全球性的严峻文化语境里,跨国资本、跨国营销所带来的挑战,往往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电影(或华语电影)与好莱坞既对抗又合作的文化关系的新特征。
全球性的文化新格局,使我们面对着这样一组关键词,即:“履约进程”和“跨界对话”。所谓“履约”,作为正式的WTO成员国,中国必须履行WTO既有的约定和规则,入世后的前五年属于“过渡期”,2006年是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过渡期”结束了,文化分销领域的承诺即将兑现,以好莱坞为主体的跨国资本的大举进入势必带来更隐蔽并更紧迫的挑战。今后几年或再后几年,我们与好莱坞角逐和“博弈”的态势显然并不容乐观。特别是,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业已贯通无阻。而所谓“跨界”,即跨文化、跨国族而与世界对话,再也不可能退回到往年“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了,我们除了立足本土,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推进自身电影的产业化,拓展并提升我们电影的国际竞争力,事实上已经别无任何选择。如何抗衡好莱坞的文化霸权,如何规避全球文化趋同性的危机,保持我们电影产业均衡、和谐、良性和安全的持续性发展,这成了迫在眉睫的一个现实的文化实践课题。
二怎样认知华语电影的“民族性”(或“民族寓言”)?
显而易见,在当下日渐开放的国际大环境里,唯有坚守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及其尊严方能自立于世界电影之林。那么,这种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和实质究竟是什么?——概括地说,它所凝聚、所带动、所实现的,事实上,恰恰是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现代人文性的拓展相对接、相交融,这样一来,无疑地我们也就被历史所注定:唯有锐意推进我们电影产业体制机制、电影产品内容形式以及市场营销传播格局的革故鼎新,以承载并弘扬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并锻铸我们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在这里,笔者所说的“民族性”(或“民族寓言”),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美国文化学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在其被广为引用的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提出的所谓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著名论断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诚然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尽管他是秉持着进步的、对“民族主义”予以某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但是,在他的话语表述中,甚至在他的潜意识中,却并不具有历史审视和美学判断的公信力,并且,他在行文中又比较顽强地、不可避免地带有“白人文化中心主义”的若干印痕。我们与他的显著区别,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1.我们所说的“民族性”,它摆脱了“第一世界文化元中心视点”的羁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狭隘的、被历史定格化了的概念,它具有历史衍进的动态性,既含有自身悠久的、不可更易的人文传统,同时,又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在进行时的概念,它始终是变动不居的,总是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着自身,并且是向现代人文性变革持续地延伸着和拓展着的。
2.我们所说的“民族性”,它并不是排拒现代性的、自闭式的,而是具有开放性的,它以“有容乃大”的胸襟,广泛吸纳并包容了文化现代性的诸多命题(主要是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迪),它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充实着自身的,由此所唤起的乃是我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苏醒。事实上,当今所谓“纯粹的民族性”(即所谓“国粹”),是只能被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当代所有的民族文化无不具有杂交性,这里,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就是将艺术家个体融入自身本土民族文化的主体而获得某种超越与升华。
3.我们所说的“民族性”,它并不是自外于本土的纯然理性的判断(尽管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之论是带有一定文化进步性的),而是含有从民族本土出发的生存意识和感性因素,是被艺术家自身的生命实践和社会阅历所决定的,带有艺术家主体性的思考和美学的濡染与渗透,具有不可被其他民族复制的文化原生性、主体性和尊严性。
显而易见,正是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特别是来自对于全球化潮流中某种文化趋同性危机的清醒认知和抗衡,中国以及亚洲周边众多不同国家具有民族文化主体自觉的电影艺术家,才被激发出一股前所罕见的泛亚洲的文化凝聚力,由此构成了一种东方文化的觉醒,成为推进中国本土民族电影(或华语电影)文化之重构的原驱力,成为推进华语电影审美之维向现代性拓展的原驱力。
三历史的回眸:华语电影的世纪性文化整合
在世界电影的总体历史进程中,华语电影无疑以其独特的东方风情和民族精神构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话语形态,并在艰难而坎坷的世纪行进中,一次次实践着超越地域、超越国族的跨界文化行动,对于建构世界电影全局性的多元文化对话的现代格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艺术贡献。
从全球视野观之,所谓华语电影,不妨借用奥运会以“五环旗”比作五大洲的象喻,指的是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和海外华裔“五环”共存共荣的华语电影作品的总称,积世纪之耕耘华语电影总数达万余部,其中包括国语、粤语、客家语、闽语、潮语以及少量英语等语种。《亚洲周刊》曾于1999年12月主持评选了“二十世纪中文电影一百强”,香港学者丘启枫撰文指出,入选的这一百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世纪全球华人的命运,“不仅呈现时代风貌,也反映不同年代的风尚,诉说华人世界的多元化心曲”丘启枫:《百年的光影永恒的记忆》,香港《亚洲周刊》第13卷第50期,1999年12月。。
跨界而与世界对话,包括在电影文化上的交流,在市场上的竞争与互惠,在实务性制片以及技术层面上的合作等多方面的内容,其间一个核心问题是,华语电影如何坚守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在银幕上塑造出经得住历史/审美双重考验的中国(或华人)艺术形象来。这或许是华人世界一代又一代电影艺术家为之献身、为之劳作不息的一个梦想。
华语电影虽从西方舶来,但早在本世纪初便渐渐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国文化历来有一种强大的同化力量,善于吸纳外来文化之所长,富于“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而不是盲目排他的。著名电影学者罗艺军曾论证说:“电影形式虽然是引进的,但中国电影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必然受到中国传统美学的熏陶和哺育。当电影艺术家创造性地根据电影的本性融入中国美学精粹,就会闪烁出光辉来。”罗艺军:《中国电影诗学断想》,《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从默片早期的《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1922)、《孤儿救祖记》,到默片晚期的《故都春梦》、《春蚕》、《神女》,到《渔光曲》(1934,部分有声),无不以其鲜明的东方民族文化特征和清新的电影诗学特色而令人瞩目,直到当今仍被东西方文化学者所热切关注,屡谈屡新;再从三四十年代“社会写实”文艺片的两度高涨,到八九十年代,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三地从传统突围而出、以鼓荡起一股现代新潮为特色的中、青年导演的崛起,划时期地实现了“二战”后两岸三地电影的文化整合,并促成华语电影以“东方新大陆”的煌煌文化风采,引起国际影坛的刮目相看,如大陆的《黄土地》、《黑炮事件》、《红高粱》、《老井》、《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以及台湾的《悲情城市》、《恐怖分子》、《一一》、《喜宴》和香港的《蝶变》、《投奔怒海》、《英雄本色》、《阮玲玉》等,无不呈现出中国历史/社会风尚的变迁和丰盈的人性美、人情美。集中地说,就是艺术地发掘并重构了历史本真的“原生态”,在整体的文化意涵上重塑了中国/华人的艺术形象,他/她们之所以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全新的历史/审美的感受,显然并不是由于这些形象给了他们一个所谓的“民俗/政治的东方奇观”,一个什么“驯服的‘他者’形象”,而是由华人艺术家从全新的现代视角所重塑的一个真实的、浸润着东方审美独有的底蕴和魅力的“中国/华人形象”,由是乃蔚为一时之盛况,荟萃世纪之绝响,铸造了华语电影历史性的文化荣耀。这种历史性文化荣耀的铸成,其关键点在于,这些作品有力地赋予了“中国”和“中国/华人形象”以本土的文化主体性,体现了华语电影健康发展的主流(至于支流性的问题则另当别论),根本不是如同某位学者主观臆断地所谓是为取悦西方受众(或国际电影节评委)而作出的曲意“臣服”,并向西方提供一个什么被看的“他者”。
四“后《英雄》时代”:大片文化品位的颓落或沉沦
中国电影产业化的真正起步,始于2003年。这是由当下全球化的语境所决定的,一个重要而显著的因素就是所谓的“狼逼门前”(即好莱坞大片的强势登陆),近七八年来我们在与好莱坞的“博弈”中获得了自身本土电影产业的觉醒,自《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神话》、《无极》、《夜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迭创票房佳绩,重振了中国电影产业之雄风。特别在2008年之初,第一部现代战争题材的主流大片《集结号》诞生了,它标志着中国大片为自觉地构建主流文化价值观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集结号》的自主创新在哪里?端在为“牺牲与辉煌”正名,让人们穿透历史,去寻觅一种久违了的精神辉煌的价值。因此,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集结号》为中国战争大片拓展出了一种令人心灵为之震撼的新风骨、新情采。它所呈现于银幕的,是一首充盈着历史悲情的英雄史诗,并将英雄的牺牲导向了精神的庄严和崇高,展示出一种何等悲怆、何等壮丽、何等崇高的美!与此同时,国产电影自2003年起在本土市场上竟连续五年超过了好莱坞大片的票房纪录;同时,我们在国际主流市场上也赢得了骄人的票房业绩,显示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尊严和气势,初步彰显了中国电影与世界对话的产业实力。
著名作家王蒙曾指出:“WTO之后,当全球的文化携资本的凌厉之风来到时,迎接或抵抗都不再具有史诗般的英雄主义情绪,中国文化人需要学习的,只是在资本中快乐地舞蹈。”王蒙:《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主题访谈),《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2日,第9版。
那么,怎样才能学会并做到“在资本中快乐地舞蹈”呢?特别是如若遭遇到以好莱坞为霸权主体的跨国资本的渗透时又当如何应对呢?质而言之,就是不可盲从于资本短视的功利本能,而应当清醒地保持艺术家创作个性的主体性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也即注重文化对资本的引导而不随波逐流;与此同时,文化还需促成资本的滚动与增值,达于文化与资本的双赢。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或者让资本打了水漂,则又能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从现代理性精神的角度来看,文化与资本双赢,这恰恰是一种“文化的悖论”,而我们或许也只能在对这种“悖论”的不断适应与突破中求得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