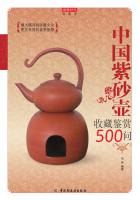九一八改变了国内的政治格局,也彻底粉碎了一些爱国人士的梦想。一大批来自不同艺术领域、有着卓越才华和丰富经验的艺术家被动员或吸引加入了电影这个充满生机的新媒介,其中不少有过留学的经历和受到现代主义艺术的熏陶。左翼电影运动兴起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艺术因素。
左翼艺术家首先是从编剧入手来影响电影创作面貌的。他们的介入,不仅给电影界带来了新的题材,也带来了新颖的叙述风格和艺术观。夏衍正是由此开始他的电影艺术生涯的。此前的夏衍,只有少量文学翻译和戏剧活动等艺术经历,但其艺术观念却与当时的大多数电影从业者有很大的不同。此前他在上海艺术剧社导演的《炭坑夫》似乎就不是一个常规叙事的话剧,而是带有某种实验色彩。有关此剧及其演出的零星遗迹不禁让我们联想到爱森斯坦早期的话剧实验。
左翼电影运动是一场在政治高压下,自由地表达艺术理想的爱国电影运动。在活跃的思想气氛下,电影的探索也表现出极为开阔的思路和灵活的创作手法。30年代活跃的电影人中,夏衍的尝试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一时期,夏衍创作了多部电影剧本,如《春蚕》、《狂流》、《上海24小时》等影片。
夏衍最初的电影剧作在成熟和完整性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但我们从中仍能感受到其构思上的独特方式。《狂流》的核心故事在今天看来很是生硬粗糙的,但是影片是在利用1931年“明星”公司拍摄的长江大水灾纪录片素材基础上构思的。仅此就为我们了解他对电影故事和环境空间的视觉展现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1933年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春蚕》在电影剧作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探索。这是中国的新文学作品第一次被改编成电影。夏衍忠于原文学文本的朴实风格和没有尖锐戏剧冲突的结构方式,从细腻的生活形态中反映时代冲突,从波澜不惊的人物内心世界中折射生活哲理。他并没有采取当时深受观众喜爱的方式进行改编,比如强化戏剧冲突、加强悲剧情绪等方式。夏衍努力按照原作的情节发展方向和人物内心的情感逻辑进行改编,使得改编的影片和原著成为一个统一体。早期的电影观众受到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很少接触如此平实的叙事手法。
虽然《春蚕》的背景音乐对剧情毫无推进作用,但影片的视觉表现仍然可圈可点。影片中有大量室外景,从不同视点和视野上勾勒出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景象,对蚕的刻画又是细致的。“蚕”在此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蚕虫互相的缠绵蠕动、集体爬行,象征着中国人民当时水深火热的状态。影片的整体呈现出真实、细腻、质朴的写实风格,一如剧作本身朴实无华。
《春蚕》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夏衍最早的作品。熟悉夏衍创作的人都能感受到《春蚕》的叙述风格与夏衍后期作品的巨大差异。《春蚕》是一部带有明显的生活流风格的影片。这不仅表现在广受称赞的导演程步高所运用的影像和镜语风格,更是由于影片结构和冲突的设计以及生活细节在叙事中起到的微妙作用等剧作因素与导演处理的和谐统一。影片拍摄时就有对于细节关注太多的议论。影片完成试映时,有朋友曾善意地向夏衍提出影片缺少强烈的戏剧性高潮,建议在老通宝的蚕茧卖不出去时,增加债主讨债的内容。从常规戏剧性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夏衍以尊重原著为理由拒绝了。这件事表面上和我们讨论的现代主义问题无关,但如果我们把他与夏衍的一篇影评放在一起来看时,可能会得到某些新的结论。
夏衍在1934年1月21日《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专栏上以笔名发表了《〈权势与荣誉〉的叙事法及其他》一文,他从这部美国电影史上被称为《公民凯恩》的先声的多视点叙事影片的结构特征入手,说到由于电影在时空表现等方面的特点,真正适于它的可能不是常规线性的戏剧性叙事,而是詹姆斯·乔伊斯式的“‘非年代化的’,以‘理解之流’为函数,凭着故事本身而展开的一种更自由的叙述方法”。将其与夏衍大约同时的作品《春蚕》和《上海24小时》相比,两种风格截然不同,但都对常规叙事做出了某种超越的尝试,我们可能更能感受到夏衍初期创作中所包含的开放的叙事观念和探索精神。
紧接着《春蚕》之后,夏衍创作的《上海24小时》也是中国电影剧作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作品,这部影片是在叙事整体的层次上运用蒙太奇思维的一次尝试。《上海24小时》一改《春蚕》弱化冲突的方式,无论在内容上、人物形象上,还是在声画关系上,处处表现出强烈的矛盾冲突。夏衍独具巧思地用24个小时内发生的故事,描绘了活在社会两端的上海市民的生活场景。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建构出强烈的戏剧冲突,取得了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学习苏联蒙太奇电影观念的一次有效的实践和有力的突破。
《上海24小时》的实验色彩就更加明显了。影片的导演沈西苓早年留学日本,他从影前的戏剧和美术创作都因不乏实验色彩而广受关注。《上海24小时》完成试映时,当时的影坛前辈泰斗郑正秋曾对其有力的艺术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1930年代前期,构成主义通过打散和拼贴等创作方式呈现出的结构性隐喻已经传入中国,并有一些艺术家在装帧艺术等领域进行尝试。而爱森斯坦的蒙太奇探索的构成主义背景也已有所介绍。从现存的剧本和当时人们的讨论和评论来看,这部影片大概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彻底地运用爱森斯坦式的理性蒙太奇结构进行影片的叙事、时空和影像呈现的影片。
30年代是中国电影界全面学习外国电影经验的时期。除了学习欧洲的现代主义思潮、好莱坞的电影产业经验外,也开始学习邻邦苏联的电影经验,尤其是蒙太奇的电影观念。夏衍、郑伯奇等人先后翻译了很多苏联电影人的著作和文章。“软性电影”的倡导者刘呐鸥,与左翼电影人论战的时候,也借鉴先锋派等西方电影理论。这都大大开阔了中国电影人的眼界,丰富了电影人的知识。
在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共存的几年时间里,有声电影的出现无疑刺激了无声电影人的神经,这要求他们营造出更有视觉表现力的画面以及使用更符合无声电影动作表现的叙事方法。当西方国家向中国倾销在当地已无商业价值的无声影片时,这也给了中国电影人最后集中学习无声电影的机会。如《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在成片将近十年后的1928年被拿到中国来放映。另一部著名的表现主义室内剧电影《最后一笑》(即《最卑贱的人》)在中国放映时,田汉等人撰写文章推荐影片,高度评价影片风格化的艺术表现力。无声电影人努力在自己的创作中学习和实践着国外无声电影的经验:时空结构、气氛塑造、蒙太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电影在视觉表现上的不足,渐渐摆脱了舞台化的痕迹,更多地尝试电影化表述的可能性、电影剧本的写作以及建立与观众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等实践。
在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转型期,在现代主义的非写实主义风格追求影响下对于视觉表现力的探索,几乎成为不少影坛新人博人注目的重要手段。1926年孙瑜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拍摄的《渔叉怪侠》等影片,虽然在内容上乏善可陈,但却由于表现主义色彩浓厚的视觉处理而得到了人们一定的关注。袁牧之也是以一个先锋戏剧艺术家的形象进入电影界,他早期的作品带有很强的实验色彩,注重艺术表现力、视觉语言上的探索。“千面人”的美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信奉和追求表现派表演理论的多样化风格。
三个性表达与市场和传统的对话
年轻艺术家们富于个性和先锋主义色彩的艺术表达给3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活力。除了题材和社会关注的新鲜视点之外,更多地表现在更加灵活多样的叙事方式、时空结构,更富表现力的视觉风格和镜语构成,以及视觉隐喻在影片意义表达中的应用等一些方面。这一切让以往不受知识分子看好的中国电影开始赢得他们的关注,这在媒体评价体系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1933年被称为“中国电影年”多少可以看作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媒体评价体系的积极反应。但是对于创作者最希望影响到的普通观众来说,效果似乎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虽然缺少直接的统计数字支撑,但我们仍可从一些讨论影片艺术得失的文字缝隙里,感觉到有人对于一些影片在观赏性方面对大众吸引力不足颇有微词。有些我们也可从后来创作的变化中间感觉到。
此时的中国电影已经经过了十多年市场发展的磨炼,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以张石川为首的“明星”电影公司在早期的本土电影产业格局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张石川和郑正秋所建立的一套基于而又有别于“文明戏”的电影叙事模式,吸引了众多电影观众,也曾引领了几次电影风潮。“联华”电影公司的创立改变着上海电影产业的格局。“明星”公司不同于“联华”,缺少强有力的院线发行放映系统的支撑,更加依赖创作上的创新来防止观众的流失,争取其在行业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此前“明星”在20年代类型更替的狂潮中不断推出新类型以引导潮流,保持了行业中的领先位置。但在艺术上基本保持着郑正秋为代表的经典叙事和影像风格。而“联华”出现之后,竞争使“明星”在题材和艺术上都需要有所创新。这也是九一八后“明星”率先考虑到引进左翼创作者拍摄能够吸引新的历史时期观众的影片的原因之一。左翼影人以编剧的身份进入“明星”公司,为“明星”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挖掘和现实生活更贴近的题材来与观众共鸣。在夏衍早期的十多部电影剧作中,其所蕴涵的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批判意识受到评论界的广泛赞誉,但其艺术特色这方面的价值往往被忽视。
但是他们对于传统叙事经验的超越也同样引起张石川、郑正秋等人的担忧,试图以某种方式进行“纠偏”。
1933年,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脂粉市场》是一部呼唤妇女意识觉醒的影片。影片揭露了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把妇女当作利益交换的商品的风气。它采用线性的叙事手法,将易卜生的社会剧到胡适的《婚姻大事》延续而来的妇女独立等社会性话题收入其中。“脂粉”是一个极为写实的象征,“市场”则直接地揭示出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片名一样,在影片的叙事中,夏衍也努力通过结构和人物命运进行隐喻性的表达。影片通过对生活细腻的刻画、环环相扣的冲突、流畅的节奏,以及明星胡蝶的参演,真实地表现了职业妇女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处处是陷阱的社会现实。该片揭示,女性的转变不过是从黑暗“奴隶市场”变成香艳的“脂粉市场”,其本质是一样的。夏衍在原剧本结尾处描写了主人公离开百货公司,走入街头人群之中的场景。这是颇有寓意的一个结尾,暗指妇女争取解放的根本道路是和争取社会解放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作为导演的张石川删掉了这个结尾,而拍成了主人公独立经营一个小商铺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当时的左翼影评人认为这歪曲了原作的主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原作的批判色彩,而颇有麻痹说教之嫌。夏衍自己也在报上发表了郑重声明。而张石川则更多的是出于自己对于观赏性的理解而做出这一改动的,觉得这样更符合普通观众的期待。
尽管发生过这些不愉快的摩擦,但是早期左翼电影在商业上的不尽如人意,也让左翼影人们感受到尊重观众欣赏习惯的必要性。1937年夏衍和张石川合作的另外一部影片《压岁钱》更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故事通过一块钱的流转,从更广的维度折射社会现实,生动地展现了30年代都市生活,揭示了隐藏在利益背后的人情世故,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混乱和分崩离析的状态。《压岁钱》标志着左翼电影在叙事方面将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与叙述的传奇风格和观赏性等有机结合,开始走向成熟。也让我们看到产业与市场的规则和现实推动着创作者认识到只有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才能将先进的革命思想隐含其中,并对大众真正产生影响。
四视听语言探索与真实观
时代环境和电影动员民众的目的与需求推动着电影的题材和人文关注与生活现实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叙事表达经验。这赋予了影片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特征在更大程度上是在美学意义层面,而非艺术风格追求层面上的。尤其是在视听表现方面,许多艺术家早年现代主义艺术背景下对于艺术语言和风格层面的偏好与追求并没有因接受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而被完全抛弃。反而成为形成30年代电影艺术特色的一种重要的潜在动力。
沈西苓最初与夏衍合作的《女性的呐喊》和《上海24小时》这两部影片中,集中反映了他们试图把苏联电影经验,尤其是蒙太奇的观念全面引入电影创作中的愿望和努力。蒙太奇不仅是一种叙事手段,同时也是表达象征和隐喻的手法。这些可贵的尝试,让沈西苓的作品在使用镜头语言加强表现力上更具才情。在《女性的呐喊》中,他把空间关系直接与人物的现实遭遇结合起来,用狭小的空间暗示人物的非人生活。《上海24小时》更是把蒙太奇运用到整部电影的结构上,用以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
当声音在电影中出现后,对于声音在电影艺术表现中的作用和意义,许多无声电影时代的大师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声音在增加电影现实感方面的优势是否会影响电影艺术表现力的担忧。这使得他们在开始时或者对声音采取了规避态度,或者更加强调声音在艺术风格化表现上的应用可能性。前者如卓别林,后者如雷纳·克莱尔。而爱森斯坦等三位苏联无声电影大师发表的《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声明》则是这种担忧的直接理论表达。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影人。爱森斯坦等人的声明发表仅仅几个月,感觉敏锐的中国影人便翻译并发表了此文。在此后的几场关于电影声音的讨论中,人们都同样表现出对声音在剧作和意义表达方面的表现力方面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