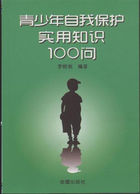在加缪的文学世界里,“人”常常呈现出一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状态。的确,无论是在他所着力塑造的默尔索等人物形象身上,还是在他始终念念不忘的爱琴海上的耀眼阳光之中,我们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顽固而恒久的陌生与疏离。尽管这种基于作家生命底层的判断、这种被命名为“荒诞”的人生感受是加缪的主要思想贡献,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对“荒诞感”的发现远不是加缪的思想终点。实际上,在短暂的写作生涯中,他一直执拗地将文学的本质认定为永远纠正现实的“行动”。如果说这里的“纠正”指的是借沉思生存真相来肯定、赞扬和完善生命的话,那么,这种肯定、赞扬与完善,显然需要一种“转回身说‘不’”的勇气与力量。换言之,加缪以诗学的方式举起的,其实是一面“反抗”的旗帜。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做人”,是《局外人》等一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题。它们以现实为题材、以“我反抗,故我们在”为旗帜,在反思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的基础上,将作家的文学写作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回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而且鲜明地张扬着一种“反抗的诗学”。
一无意义的烈士
不妨先从加缪的小说《局外人》(1942)谈起。在《局外人》中,主人公默尔索的最终命运——被判处死刑——常常令人费解。虽然说任何人的生命之谜都值得破译,但对于这位以“荒诞”名世的青年男子来说,自己的死亡竟然如此煞有介事、如此处心积虑,这就不能不引起特别的追索的兴趣。因为,恰恰在几天前,默尔索刚刚经历了敬老院中母亲的葬礼,目睹了枪声下阿拉伯人的挣扎,现在又要迎接自己与生命的告别。这三桩猝然发生的死亡事件看似偶然,但其潜在的联系却构成一种紧张关系,将人情冷暖与世间百态巧妙地揭示出来。因此,可以认为,这一内在张力也给我们提供了解读作品的另一把钥匙。
实际上,如果单独来看,上述三种死亡都不足为奇。它们或为自然死亡(母亲),或为意外死亡(阿拉伯人),或被法律判决(默尔索)。显然,这三种形态已经大体囊括了生命结束之全部仪式。而且,纯粹从法律意义上说,前二者的死似乎并不必然导致默尔索被判极刑。但是,在这个态度决定一切的时代里,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懵懂杀人居然连开四枪,恰恰构成了默尔索罪名中的全部要害。必须承认,“他之所以被妖魔化而定罪,正是由于他一系列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竟被观念、习俗的体系特别挑选出来,并被精心编织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神话”柳鸣九:《加缪全集·总序》,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3。,所以,在合法化的外衣下,默尔索的出局是难免的。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人的出局不是早已由他自己选定了吗?他不是一直甘于做一个局外人吗?那此处的出局又有什么样的具体含义呢?
加缪代表作《局外人》一版再版
的确,自外于人一直是默尔索的生活常态。无论是工作、交友等日常活动,还是悲伤、快乐等情绪变化,他都表现出与旁人格格不入的表情,口头禅“我怎么都行”就是这种漠然、无所谓的生活态度的恰切反映。然而,“作者并不是要把这个人物视为一个懒洋洋、冷漠孤僻、不近人情、浑浑噩噩、在现代生活中没有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的废物”柳鸣九:《加缪全集·总序》,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页14。,而是慷慨地将他塑造成一个拒绝说谎、光明正大的人,“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页68。实际上,默尔索热爱生活,真实而具体的生活,热爱阳光与大海,他的漠然并非拒绝一切,而是拒绝虚妄的、抽象的生活,力求在真实中找到一己的欢乐。因此,在他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状态下隐藏着另一重断裂:时间的断裂——不顾及昔日也不展望未来,此刻,就是唯一值得把握的价值。进一步说,时间的断裂其实暗示出生命经脉的断裂。社会与个人、抽象与具体、矫饰与真实的冲突在荒诞中堂皇登场。被判处极刑,自然宣告了默尔索的落败,却也在另一维度,让我们透过主人公的眼睛获得几分彻悟:生存的尴尬与无奈从来没有外在于人,它就是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加缪成全了一个别样的默尔索:一个“无意义的烈士”。
有人或许会问,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居然被冠以“烈士”称号,这难道不是一个荒诞的玩笑吗?的确,伴随着“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种古典式美学风格的随风而逝,现代艺术的激变似乎已成定局,高大、雄健的艺术形象早已英雄不再,灰色、晦暗与模糊转眼间成了生活与艺术的主色调。然而,作为荒诞之思的一个典型,主人公默尔索的寂然而亡却违逆了诸多生活逻辑,在不可思议中完成。因此,这桩充满了悖论的事件就尤其耐人寻味。实际上,默尔索对死亡的漠然首先暗示了对生活的反抗。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这里的反抗呈现出形而上学的姿态,是主动的意识选择。所以,“‘抗议’以及‘没有明日路途的牺牲’,这便是荒谬英雄们的抽彩券。这些英雄们知道,人,就是‘自己的终极点’。他们还知道,正如圣泰克絮佩利所述,只存在着‘一种奢侈,人的关系的奢侈’”德·布瓦岱弗尔:《今日法国作家》,页40。。正是由于人感觉到世界的陌生与疏离,所以,“关系”才变得如此“奢侈”。必须承认,存在主义所着力描述的人的逃离与寻找都与“人的关系”有关。众所周知,存在主义的关键词是“荒诞”,而且我们大体上也可以认同“这世界的钝厚与陌异,便是荒谬”德·布瓦岱弗尔:《今日法国作家》,页39。。那么,这里值得追问的关键就成了:在面对荒诞时,哲人作家们究竟采用了怎样迥异的态度?
一位法国文学研究者指出:“面对不抱希望、不信上帝的人们,马尔罗推荐的是行动中孕育而出的‘阳刚之气的兄弟情谊’,萨特推荐的是唯一见证之真实性,加缪推荐的,则是一种‘荒谬的神圣’之中对反抗的超越。”德·布瓦岱弗尔:《今日法国作家》,页15。因此,在这本1986年出版的研究论著中,他给予了加缪慷慨而发人深省的赞扬:“如果说《局外人》在问世四十多年后仍为我们时代最高成就的著作之一的话,那么原因便是,它以一种无可比拟的白描手法表现了人类在荒谬面前的耻辱。”德·布瓦岱弗尔:《今日法国作家》,页42。从审美效果上来看,默尔索之死的荒诞性无可讳言,故事本身给人的“正面震撼”也似乎无人能够逃避。但在我看来,这里显示的荒诞可以从人对死亡的本能焦虑这个角度来考察。
无可否认,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是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可逃避的焦虑,所有抹杀其存在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死亡,本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意识,是人对死亡事实的观念与想象,是有限的此在感受到的心灵中无可逃避的威胁。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威胁人的本体上的自我肯定的,不仅有死亡的绝对威胁,还有命运的相对威胁。只不过,由于个体生存的偶在性,命运显得随机而充满变数,而在死亡面前人则无可选择。由此,对死亡的焦虑就成了最具普遍性的现象与结果。人是被抛的存在。不仅在他被抛出存在的最后时刻,而且在其存在的每一时刻,死亡都站在身后。这里所谓的“被抛”具有双重的涵义。一方面,人的生存状态是偶然的结合,整个环绕我们的因果关系的网罟纯粹是随意的结合;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时无刻不被这张网罟所决定并在最后一刻为它所抛弃。所以,对死亡的焦虑就成了无所不在的生存之幕。在这个前提下,如何克服或者缓解这种焦虑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寻找灵魂的现代人该怎样坦然去死?
针对这个问题,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利希尖锐地提出了“勇气”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勇气”就是不顾(in spite of)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的自我肯定。这一界定主要是受斯宾诺莎关于勇气看法的影响。实际上,自我肯定的信条是斯宾诺莎思想中的核心,其根本特征表现在这样一个命题中:“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质。”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106。对他而言,自我肯定就是参与到神的自我肯定之中。“个体事物(人当然也在内)借以保持其存在的力量就是神或自然的力量,不是就此力量是无限的而言,而是就此力量可以通过人的现实本质而得到说明而言。”斯宾诺莎:《伦理学》,页173。蒂利希继承这个命题,并在此基础上着力强调了斯多亚派哲人的精神品格。
公元前4世纪创立于雅典的斯多亚学派,主张淡泊自守的人生观,不以苦乐为意。因此,与柏拉图主张的“坚毅”、斯宾诺莎倡导的“自我肯定”,以及尼采高扬的“权力意志”相区别,斯多亚派对死亡表现出惊人的坦然与从容,这种勇气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苏格拉底之死。可以说,临终的苏格拉底所具有的勇气是理性—民主式的,而不是英雄—贵族式的。“苏格拉底之死对整个古代社会既是一个事实又是一个象征。它昭示了面对命运与死亡时人的处境。它昭示了一种勇气,这种勇气能对生命加以肯定,因为它能对死亡加以肯定。这个事件给勇气的传统意义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在苏格拉底那里,过去的英武勇气变成了一种理性的和普遍的东西。勇气的民主观念被创造出来用以反对勇气的贵族观念。”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9。死亡,说到底,是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从容赴死的勇气就称不上有对生命的热爱与真诚。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用鸩酒验证了理性—民主的凛然不可侵犯,但这一行为的意义又远远超越对理性—民主的维护。它实际上昭示了一个人生存的深度,烛照了人性的光辉,提升了人类的品位。因此,斯多亚派的精神既非无神论的又非有神论的,存在,是它的力量之源。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斯多亚派鲜明地将“自杀”作为确立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正如保罗·蒂利希所指出的,“斯多亚派所标榜的自杀,并不是推荐给那些为人生所征服的人的,而是推荐给那些征服了人生,既能生又能死,并能在生死之间作自由抉择的人的。自杀作为一种逃避,作为一种受制于恐惧的东西,是与斯多亚派的存在的勇气相抵触的”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页10。。对死亡的坦然接受,已经是一种有勇气的姿态,更何况积极主动地赴死!斯多亚派的动人之处正在这里:旷达,说到底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是穿梭于生死两界时表现出的大悲悯。如果死亡是命定到来的节日,那么,坦然去死的秘诀就在于“勇气”——一种不顾一切的自我肯定的精神。在这个分析背景下,让我们回到默尔索问题。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不能说默尔索没有勇气。但是,现代人默尔索的勇气却是迥异于古典的斯多亚派的,后者所谓的“旷达”与“悲悯”在这里早已荡然无存,余下的唯有冷漠与陌生。世界与自我之间的裂缝居然如此巨大,默尔索实在无法作出认同。因此,母亲死后他没有哭,也没有见最后一面,与玛丽交欢后被问及爱还是不爱时,他也不置可否。在通常的观念中,母亲是和割舍不断的亲情联系在一起的,与异性发生关系也最好冠以爱的名义。这一切都太正常了,太合乎常规了,因而当有一个人跳出来,对这一切表现出自己的漠视时,社会感受到威胁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就是说,默尔索的冷淡与缄默断绝了有效的交流,暗示着与众不同的反叛,但与强大的社会法则相比,他个人的力量显得十分软弱,他的特立独行的生存方式也终将被排除出局。
但是,面无表情、摸摸索索的默尔索却让人觉得熟悉而亲切,能够作为一个文学典型经久不衰,原因何在呢?加缪曾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成一句话:“在我们的世界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就是说对于社会常规而言,默尔索代表着一种真正的威胁。他最为恐怖之处,不是他犯罪或作恶的倾向,而是他对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希望、信念和理想的漠不关心。
在我看来,漠然中的真实就是默尔索的价值所在。他是社会的“局外人”,却是一个本能地保持并尊重与生俱来的自然力量的人,拒绝装扮成周围的人装扮的样子,他依照一种与社会功利毫不相关的价值优美从容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没有留下遗憾。因此,默尔索是一个真正的烈士,一个为荒诞殉葬的“烈士”。他被以正义与公理的名义处以死刑,而他身上反而蕴藏着一般人缺乏的忠实于内心感觉的品德。我们当然可以认为默尔索是荒诞的,因为他不曾为母亲之死流泪;而默尔索却会认为其实整个世界是荒诞的,因为大家都在说谎,“说出的东西多于存在的东西,说出的东西多于自己感觉到的东西”。默尔索是幸福的,他的幸福在于“对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他热爱自己的生命,拒绝掩盖真实的假面,对生活有一种真实的,而非装腔作势的、矫揉造作的激情,加缪在为美国版的《局外人》写的序言中写道:“他远非麻木,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因此,默尔索的勇气虽然缺乏古典的英雄气概,却依然不失其光彩。在这个意义上,局外人的问题,本质上是自由问题,也就是说,他探询的是,在世界与自我的紧张中,如何找到灵魂的自由和生命的力量。
实际上,“当康德把上帝的存在推拒到经验理性之外的世界,阻断了唯理思想家设定的人的理智与上帝的智慧的关联,荒诞就成了人之为人的首要条件。因此,特别从康德以来,理性的人愈来愈感到需要为自己的欠缺辩护”刘小枫:《拯救与逍遥》,页362。。加缪塑造默尔索形象,正是试图站在现代人立场上“为自己的欠缺辩护”。雅斯贝尔斯对时代意识的如下断言显然得到了加缪的赞同:“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页1。接下来的问题是,该怎么办?显然,对默尔索来说,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是要战胜社会的虚伪、宗教的虚幻,在真实中生活。对这一真理的领悟使默尔索重新体验到快乐,他是自然之子,也只能在自然中得到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