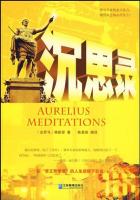但如果要探问构成这部巨著的无穷意义的原因,我们还得回到作家丰富与驳杂的身份上来。作为一个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一发表就受到了当时俄国著名评论家别林斯基的盛赞——别林斯基毫不犹豫地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掌握了“艺术的奥秘”,是“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在以后的岁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一连串作品兑现了这一善意而慷慨的预言。同时,作为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痴迷于哲学难题——回答和解决哲学问题——他不止一次在书信中以及借他的人物之口说出:必须先解决重要的思想问题。他的作品里也的确充满了各种堪称思想家的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梅什金公爵、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他们拥有和维护着一系列各自独立而又相互矛盾的哲理观点。但无论是小说家还是哲学家,这两个身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全面指称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的无可替代在于他几乎完美地将这两者熔在了一体,即力图以文学的形式写作哲学,以思辨的笔触创作小说。
茨威格曾深刻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一种伟大传统的断根人,是真正的俄国人,是过渡人。他们心里是开始的混乱状态,还背负着克制和没有把握的重压。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哪个问题得到了回答,也没有一条道路平整了出来。”茨威格:《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页106。这一点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几个主人公——尤其是伊万身上得到了极富意义的体现。伊万的思想形象与他的弟弟阿廖沙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一个宗教象征,阿廖沙,这位“城郊修道院里刚满20岁的见习修士”,具有宗教直觉,不但是兄弟们中唯独不和任何人对立的人,而且切实地将感受到的宗教精神贯彻进自己的日常行为。但必须指出的是,小说里的阿廖沙实际上只是一个“爱的化身”,一个象征性的精神符号,他的“行动”仅仅类似于东正教中“圣母”的悲悯而垂怜的目光,缺乏作为人的动感特征。因此,在这部巨著里,阿廖沙的形象还有着无可讳言的单薄之处。至于伊万,则显然复杂得多。
从话语的力度来看,伊万是一个雄辩的典型。他强大的说服才华的直接后果——借他的异母兄弟斯梅尔佳科夫之手完成了弑父行径——就是一个例证。再如,在小说末尾,即庭审弑父案即将开始之前,伊万与魔鬼(伊万的另一个自我)进行的那场滑稽而可怕的交谈,也都显示出他确实具有超强的“言说”能力。对伊万而言,理性中的“自明法则”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他对上帝的质疑与分析也自然隐含着对理性的信任:
亲爱的,我认定,既然我连这个道理都弄不懂,我哪里懂得有关上帝的事呢。因此我只好老老实实承认,我毫无能力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我的头脑是欧几里得式的世俗的头脑,因此我哪能解决来自非人间的问题呢。好阿廖沙,因此我也劝你永远别想这类问题,尤其是关于上帝的问题:有没有上帝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不是仅有三维空间概念的凡夫俗子的头脑所能解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页324。
伊万甚至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假如有上帝,假如他真的创造了大地,那他也是按照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创造的,而他的头脑也与人类相同,仅拥有三维空间的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页323。这个大胆的结论源于他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他向阿廖沙倾诉道,令他无法与上帝取得和解的主要原因是关于孩子们的受难问题。伊万提醒阿廖沙,孩子和大人完全不同,大人“偷吃了禁果,懂得了善与恶,变得‘跟上帝一样’”,“但孩子们什么也没吃,因此暂时还无任何罪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页327。然而这个世界上却有人做着伤害和折磨孩子的荒唐事,而基督教宣称“在世界的终点,在永恒的太和到来之时,将会产生和出现某种至为宝贵的东西,它足以抚慰所有的心灵,消弭所用的愤懑,弥补人们的一切恶行和他们所流的全部鲜血,足以使我们不仅可以原谅,而且可以为人们所发生的一切辩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页324。,也就是说残害孩子的凶手也终将被宽恕。伊万从自己肉眼的观察出发根本拒绝这一个所谓的永恒幸福,他宣称:
我根本拒绝接受那种所谓太和,这样的太和还抵不上仅仅一个孩子的眼泪。……你用什么,用什么来补偿这些眼泪呢?难道这补偿得了吗?莫非他们得到了报应就算了吗?……我不愿意人间出现太和,由于我爱人类我不愿意。我宁可固守在我那未得到补偿的痛苦中,固守在我那未曾消弭的愤怒中。要获得太和的代价太高了,我根本买不起这门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页338—339。
无疑,伊万在这里对超验上帝的反驳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千古难题,神正论显然无法回应所有的现实苦难与人的精神困境。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反思上帝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借理性的名义为所欲为。伊万没有这么浅薄,他的真诚基于一种对生命的执著追问。伊万虽有名言“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但这实际上并非他践行的生活原则。相反,他无时无刻不震惊于这一逻辑主义结论的可怕,从而彷徨无所之。正如作家本人曾指出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是深刻的,这不是当代的无神论者,他们的无信仰只说明世界观的狭隘和才智的平庸呆板”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页387。。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的无神论者”的迂执、刻板与缺乏人性从斯梅尔佳科夫的形象中得到了体现,而伊万的头脑远非那么简单。从俄罗斯文学的史迹来看,伊万是与“多余人”系列形象有内在的精神联系的。无论是普希金的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当代英雄》)、赫尔岑的别里托夫(《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罗亭》),还是托尔斯泰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战争与和平》)、列文(《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都以其不懈的精神探索姿态和迷人的思想深度闪耀于世界文学长廊之中。同样,基于这种“家族相似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伊万,这位被称为“彼得堡时代的漂泊者”的人物,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探索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在我看来,伊万精神困境的根源在于混淆了“理性”与“理性主义”这两个概念。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明确指出:“令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上的果实,是来自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44—45。为了获得这种囊括一切的知识,必须把思考作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包括各种逻辑形式:归纳、演绎、分析、论证,以及计划、解释、判断、评估等等。这种知识的基础和知识本身以及取得它的手段通常都被称为理性。而对理性全然的信任,也就是那种将理性当作衡量一切存在的真伪标准与意义标准的态度就被称为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确立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却遗忘了基督教义理所教会我们的“谦卑”的艺术,忽略了“上帝”形象的多重面相。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万最终走向疯狂的生命结局不仅昭示出这一点,而且也暗示了作家痛苦思考之后的价值选择。
三个体自由及其困境
应该承认,重新拥有本真的生命状态、获得内在的精神信念是作家的终极关切。无论是对于加缪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点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两位作家都对上帝问题有过自己的思考。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西方思想的发展历程上,上帝的多层面的形象实际上是逐渐形成的。第一个层面是圣经中的上帝。这是一个以人的形象亲近人、爱人、引领人走向理想国的至善者,他为人类的利益四处奔走呼告。第二个层面是作为最高实体的上帝,形而上学的上帝,至高的存在,第一推动因。这个层面的上帝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作为最高实体的上帝,以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和奥古斯丁的看法为代表,托马斯认为上帝是自然规律的超验根据和终极目的;其次是作为宇宙普遍法则的上帝,以笛卡儿的看法为代表。笛卡儿虽然不同意神是万物的推动因,但基于对上帝的虔诚仍然把“上帝”的意志解释为自然规律本身;最后是历史世界中的上帝,以黑格尔的看法为代表,在黑格尔这里,绝对理性即是上帝,“上帝”与世界历史同一。可见,“上帝”一词的内涵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面目全非。
透过历史的尘埃,“上帝”一次次地承载着他人的议论、阐述与评价。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伊万的问题恰恰在于没能区分清楚这个符号背后的不同涵义。换句话说,话语的混乱导致了思想的混乱——伊万以理性思辨的方式驱逐了形而上学的上帝,不幸却连《圣经》的上帝一起驱逐了。对此,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无法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