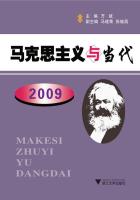以一个“忠”字来保护自己,在那个时代实为最有效的手段。冒死上书以勇为忠,丁忧出山以孝为忠,功成而退以惧为忠。以曾国藩的功绩地位和当时的情势,换了第二个人恐怕早已身首异处了。
曾氏原是一位清闲的京官,官至侍郎,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他可能会永远做一个文官,并可能有大量著述留给后世,成为清朝后期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理学家。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改变了他的人生。1852年秋,他回湖南湘乡的老家吊母丧。1853年1月21日,接到咸丰帝谕旨,要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这道寄谕打破了曾国藩宁静的生活,从此走上了“以杀人为业”的带兵打仗的征途。与太平天国的战斗初期基本上是败多胜少,曾氏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是“屡败屡战”。“屡败屡战”不同于“屡战屡败”,前者虽是屡败,但仍屡战,可表明斗志之坚强,意志之顽强;后者则未免令人读之泄气,纯为无能的表现。这期间曾氏因兵败,痛心疾首,两次投水自尽,又有一次欲仿效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之先例,策马赴敌而死,均被同僚救起或劝止。从这几次动真格的自杀举动中,曾氏的忠心可见一斑!不仅曾氏自己忠于君王,他也以此影响部属,在全军范围内,所重“惟忠而已”。当然他部下的忠心,具体到实际问题上,则是士兵忠于哨长,哨长忠于营官,营官忠于统领,统领忠于大帅。上级对下级不越级指挥,而兵勇和将领只听命于他们的顶头上司,只忠于他们的“第一个”上级。这种情形为清廷在19世纪中叶以后军权旁落,渐归督抚埋下了祸根,更为民国时期军阀蜂起,连年混战埋下了祸根。但这在当时,仍然彻底地改变了原来清军主力——绿营所存在的“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的弊病,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斗力。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害。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有书记载说,曾国藩平素莫名其妙地最怕鸡毛,偏又爱吃鸡肉。
当时,紧急公文,信封口都粘有鸡毛,俗有“鸡毛令箭”之称,曾国藩一生,见了这种文书,总是不敢亲自开拆。曾国藩死前的一年(同治十年,1871年)到上海阅兵,阅兵台上供张齐备,侍卫先来检查,瞥见曾国藩的座位后面有鸡毛帚子,大骇,立刻吩咐取去藏过,阅兵仪式才如常举行。就是这样一个连鸡毛都怕的人,却能冒死犯颜直谏,不失时机地说出那些常人所不敢说的话,确是令人佩服。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亢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有清一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等同。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来的诚,是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
没有这样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