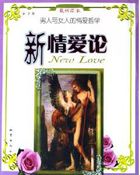世人各有其性,各有其长,但不一定人人皆能用,也不一定人人皆不可用。所以用人之道与取人之术常是至为关键的。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掌控这两方面的一等智者,他眼光锐利,观察仔细,常能找到为自己谋大事,成大事的强人。
“阅读精要”
识人、取人、用人是曾国藩的特长,很多发生在他身上的相关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他善于通过取人、用人,把别人的能力化为己用。曾国藩取人、用人不拘一格,使这些人才各适其位、各尽其力,曾国藩也正是借此成就了自己的“中兴”伟业。人才的重要性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域都一再被强调,作为一代政治、军事英杰的曾国藩更是把它放在决定事情成败的首位。在练兵之初,他既没权又缺钱,硬是靠一批忠勇能干的人才训练成为一支善战之师。
(1)四处求取人才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将颓败的官场风气与人才问题联系起来,指出:“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面语无归宿。”他说:“有此四者,习俗相传,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其势如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席卷东南。对此,曾国藩无比感慨地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时即使得到,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或遭遇挫折、或离职而去、或抑郁而死。而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权重,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呼吁封建地主阶级重视人才问题。他一再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有此认识,就足以证明他的眼光之高。曾国藩求贤若渴,他向友人描述自己在咸丰三年(1853年)时的心情说:“我曾经说过要谋求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人才,几个月以来,我在梦里祈求他们的到来,烧香祈求他们的到来,没有片刻敢有所忘怀。”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事业”大有发展,人才尤为亟需。他给友人写信说:“国藩当疲惫之余,忽膺艰巨之任,大惧陨越,贻友朋羞。惟广求名将,以御寇氛;广求循吏,以苏民困。得一人则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则地方渐受十分百分之福。”同治四年(1865年),他走上攻捻前线,榜列《剿捻告示四条》,其中一条便是“询访英贤”。他指出:“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才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于城心腹之用。”他号召:“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酌察录用;即不收用者,亦必优给途费。”曾国藩求才,可说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料理官车,摘电备查”,或“圈点京报”,获取信息。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他还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认为求才应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及其余”。因此,他多次致书李恒、李瀚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诸弟,论述得人之道,要求他们随处留心,“博采广询”,“兼进并收”。他还嘱咐弟弟要“求人自辅,时时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后两弟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长处短处一一告知阿兄”。
(2)争取选到合适的人才
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他对曾国荃说:“弟常以求才为急,但无才之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与之共事。”当时,亲戚朋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惟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于预见国运的人,看到该国贤良俊杰在位,就知道它一定会兴盛起来,看到办事拖拉,冗员比比皆是,就明白它将要被取代。善于预见军队的人也是这样。他对方存之说:“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庸人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他说李元度“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既广求人才,又不博收杂进,分辨真伪,考察贤劣,这就决定于对选择人才的标准的认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人的德行。他在笔记《才德》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接着他强调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基于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质)”。他指出:“以其质而更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他声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他劝诫绅士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故他特别强调禁大言而务实。在确定选择的标准时,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表示:“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什么是“官气、乡气”?他解释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比较起来,曾国藩更厌恶那些爱摆官架子、应酬圆通,却奄奄无气、从不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因此,他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即“筋力健整、能吃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关于为官“四到”,曾国藩本人有个解释:“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心叮咛是也。”这里当然仅是举例以说明。能真正做到“四到”的人,必须是“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他们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中克服某些弱点,渐成大器。总之,曾国藩选人、用人的标准主要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行操守践履到实处。
(3)用人应德才兼备
当然,曾国藩不是不注重才识,相反,他是很注重才识的。他劝勉曾国荃说:因“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二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振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在选用人才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但是经过多年的曲曲折折,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番感慨:在用人这一点上,实为万事的根本。德才二项要取其一已属很难。而要二者兼备,则极为少见。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1871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4)始终把发现网住人才放在首位
发现和罗致人才,只是解决人才问题的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人才。曾国藩的原则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用人上的“广”与“慎”,是互为条件,互相影响的。广则人才多,人才多则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广而不慎,必会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慎则使用得当,使用得当则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慎而不广,必会人才匮乏,或窒息人才,同样是事业的大患。薛福成说他“在籍办员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并说李世忠、陈国瑞在湘军将领中以“桀贪骜诈”闻名,曾国藩对他们仍予以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曾国藩说:“求人之道,必须像白圭经营买卖那样,像鹰猎取食物那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白圭,战国时周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如同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买卖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推荐,有的为该员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的“未发迹”之时,甚至在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在办团练时,他时谍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曾国藩困顿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以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奄奄无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作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做准备。曾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想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等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愿投胡林翼处而不愿跟他做事时,立即改弦更张,翻然悔过,与之展开一场广揽人才的竞争。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蚨,即青蚨,是类似于虫的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李竹浯推荐的。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很有人才匮乏凋弊之说法,实则岩搜谷采,楚材晋用,而故山反为之一空。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在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宣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因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炼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