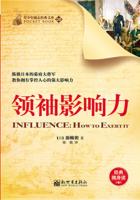和平时代的人们,做事情的敢与不敢,主要体现在有没有承担风险的勇气以及抗拒风险的能力。换句话说,敢不敢承担大的风险,往往这种敢并不直接威胁身家性命。而战争时代的敢则不一样了,他直接面对的是生死的抉择。曾国藩就是在关键时刻具备这种“敢”的人。
1854年4月27日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沿湘江北上,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顺流疾进,刚至中午,湘军水师和步骑都到了靖港镇外。
步骑过了浮桥,曾国藩即下了进攻的号令。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湘军初战受挫,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后退。李续宾、王錱等人想督军迎战,谁也不听指挥。一片喊杀声震山荡水,“活捉曾国藩”的吼声更让中计的曾国藩心惊胆战。然而,他心知不能一败再败,必须誓死抵抗。面对溃逃如潮的湘军,他怒火中烧,令护卫把将军旗插在江边,自己执剑立于旗下,高声断喝:“过旗者斩!”
溃兵涌来,曾国藩大吼一声,挥剑砍翻一个,余者呆立瞬刻,绕过军旗,继续狂奔。后面的败兵如排山倒海,曾国藩一把长剑再也不知刺向何人了!
这时,太平军大队冲入湘军队伍中,一片砍杀之声,湘军完全失败了。卫兵一把拉过曾国藩,护入座船,仓皇向长沙败逃。
曾国藩呆坐舱内,五内俱焚。衡州出师后,与太平军交锋,两仗两败,落了个狼奔豕突的结局,自己惨淡经营,苦练了将近一年的湘军,竟是如此无用。他想这样下去,原先的豪言壮语将全部落空。再回长沙,官绅们的冷眼将不堪入目。何况,这次是否能逃得回长沙,也很难说。耳畔,响起一片败兵的嚎叫,一片“活捉曾妖头”的怒吼!他左思右想,决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讨其辱。这时,幕僚陈士杰、李元度看到曾国藩神情有异,命令章寿麟驾一舢板,随护座船左右。
岂料,座船随员稍未注意,曾国藩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跃入江心。“曾大人跳水了!”章寿麟一面大叫,一面从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国藩,扶进船舱中。大家七手八脚为他换衣、推腹,好在他并未呛水,尚无大碍。大家一路解劝,狼狈退回长沙。
曾国藩的勇敢与倔强,后来在他兵困祁门时也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的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这是何等的勇敢与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军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四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
在艰危的形势下,曾国藩敢于“誓死如归”。别人不怕的他怕别人都怕的,他却不怕,这往往是一种大智大勇。
人生的戏,不同于舞台的戏。舞台的戏,演错了可以重演,不会有什么生命之虞。而人生的戏,在表演生与死的“艺术”时,则很可能弄假成真,因而更需要表演者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大智大勇。人生许多峰回路转的佳境,都是靠这一“表演”艺术再现的。因此,更多的时候就看芸芸众生敢不敢在这一舞台上一试身手。
曾国藩认为,在透视成功者时,一般人往往难以顾虑到事物仍在发展变化中的因素,对成功者更难识别是少年早发还是大器晚成。他说,具备早成天赋及聪慧的人会很快崭露头角,处理事务游刃有余;但是那些大器晚成者,往往持重,愿意通过艰苦努力获得成功。对后一种人更不可以掉以轻心。效刘备患难与共,“死在一堆何如?”
处于困难的时候,如何凝固人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成功术。曾国藩在这方面可谓很有招术,以致当时人认为他也很崇尚权术。
曾国藩困顿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有程尚斋等几个人,奄奄无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这时,李秀成带太平军大队人马破了羊栈岭,进克黟县,距曾国藩总指挥部的祁门大营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当时,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防兵,驻扎休宁的张运兰更是岌岌可危。曾国藩只好急调鲍超驰援祁门。曾国藩此番处于绝境,自料难逃一死,连遗嘱也写好了。祁门大营的幕僚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曾国藩见人心已散,不可强留,乃心生一计。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作答,悄悄把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作准备。一日曾国藩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惜李秀成在休宁柏庄岭与鲍超、张运兰大战失利,随即匆匆撤兵南下,经屯溪、婺源转入浙江,让曾国藩白拣了一条命。在此期间,曾国藩表面上谈笑风生,神态自若,内心则极为恐惧。据说,李秀成退兵之后,鲍超率亲兵一队前往祁门大营拜见曾国藩。鲍超下马,正打算行礼,曾国藩快步上前,与鲍超相拥抱,并说:“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言已泪下,“不复能自持矣”。可见这次祁门被围,在精神上对曾国藩打击之重。
李秀成虽然走了,但太平军仍有大批人马留在皖南,尤其在占领徽州以后,太平军随时都有可能进攻祁门。所以,曾国藩下令鲍超留驻渔亭,张运兰驻扎黟县,以加强祁门大营的防卫力量。但是,由于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对比上湘军又处于劣势,因而曾国藩仍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马三路再次向祁门发动进攻。东路破德清、婺源直趋祁门,西路破建德、鄱阳转攻景德镇,北路入洋栈岭进逼黟县。曾国藩四面楚歌,再次陷于惊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说:“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曾国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饷,徽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浮梁、乐平、景德镇一线成为祁门大营惟一的对外通道,一旦被太平军攻占,就会文报不通,粮饷断绝,立刻就会陷入困境。此次太平军进攻祁门的诸路人马中,西路军人数最多,大约不下二万人,主将为太平军的骁将黄文金,成为对湘军的最大威胁。因而,曾国藩急调鲍超赶赴景德镇救援。可惜黄文金与鲍超、左宗棠军激战负伤,率军退回皖南,使曾国藩得以很快恢复粮道,度过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