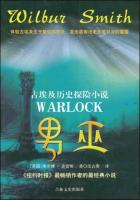我的笔一写到往日的这个姓名,我的心就想到往日的爱情。我仍旧把她写作劳娜·费尔利。想到她的时候,我不能用她丈夫的姓;谈到她的时候,我也不能用她丈夫的姓。
我这是在重叙往事,所以我无须另做解释。我既然仍有毅力和勇气写,那么现在就让我继续写下去吧。
一到第二天早晨,我第一件渴望要做的事就是去见我的母亲和妹妹。我离家许多月来,她们一直没法获得我的音信,现在知道了我的归来,她们一定惊喜交加,我觉得有必要让她们对此有个思想准备。于是,我一清早就发了封信到汉普斯特德村舍;一小时后我自己也跟着出发了。
经过团聚时的一阵激动,逐渐恢复了往常那种安静的气氛,这时我从母亲的表情中知道她心底里隐藏着一件十分烦恼的事。她亲切地看着我时,焦虑的眼神中不仅流露出慈爱,还含有悲哀;她亲切地、缓缓地紧握住我的手时,我从她那温柔的手上觉出了她的怜惜之情。我们之间一向是毫无隐瞒的。她知道我一生的希望遭到毁灭——她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了她。这时我想要故作镇静地问她:可曾收到哈尔科姆小姐给我的信吗?有什么关于她妹妹的消息吗?这些话已经到了唇边,然而,一看到母亲那副神情,我再也没勇气哪怕是很婉转地向她提出问题。我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你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谈吧?”
我对面坐着的妹妹,这时突然站起身,也不解释一句,就离开了屋子。
我母亲在沙发上向我挨近一些,双臂搂住我的脖子。亲热的手臂开始颤抖,泪水很快地从那诚挚、慈祥的脸上流淌下来。
“沃尔特!亲爱的!我为你心里难受。”她压低了声音说,“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要记住,现在我还活着呀!”
我一头倒在她怀里。她在以上几句话中,已经道出一切。
……
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三天早晨——十月十六日早晨。
头几天里,我一直和她们待在村舍里;她们见我回来都很快乐,我竭力不要使她们也像我一样感到痛苦。我要尽一切力量在打击下重新振作,要看破一切,接受我的命运,要把我的巨大悲哀在心中化为柔情,而不是变成失望。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泪水怎么也不能医好我痛楚的眼睛,我妹妹的同情和我母亲的慈爱怎么也不能给我带来安慰。
就在那第三天的早晨,我向她们倾吐了心底的话。早在我母亲告诉我她死讯的那天我就急于想说的话,现在终于脱口而出。
“让我独个儿出去几天吧,”我说,“让我再去看看第一次遇见她的那个地方,让我跪在她安息的那个坟墓旁边为她祈祷吧:那样,我心里也许可以好受一些。”
我登上旅程——我去看劳娜·费尔利的坟。
那是一个静谧的秋日下午,我在冷落的车站下了车,独自徒步沿着那条熟悉的公路走去。从稀薄的白云中夕阳发出微弱的光芒;空中温暖而岑寂,倏忽将尽的季节给荒凉宁静的乡间笼罩上了一层愁郁的气氛。
我走到了荒原上;我又重登上小丘顶;我沿着小径向前望:远处是花园里那些熟悉的树木,清晰地延伸过去的半圆形车道,利默里奇庄园的白色高墙。种种奇遇与变化,过去许多个月的流浪生活与惊险经历:在我脑海中一切逐渐暗淡了。仿佛昨天我还走在这片芳香宜人的土地上!我幻想中看到她来迎接我,那顶小草帽在阳光下遮着她的脸,一身朴素的衣服在风中飘动,手里拿着那本里面夹满了图画的写生簿。
哦,死神,你带来了痛苦!哦,坟墓,你取得了胜利!
我向一旁转过身去;下边谷地里是那所凄凉的灰色教堂,我曾在那里的那条走廊等候白衣女人。那些小丘环绕着静悄悄的墓地,那条清凉的小溪汩汩流过石床。那儿,是上面竖立着漂亮的白云石十字架的坟——现在坟底下埋的是母女俩。
我向那座坟走近。我又越过低矮的石头墙阶,踏上那片神圣的土地,脱下了帽子。那是神圣的,因为它埋藏着温柔与善良;那是神圣的,因为它引起了我的崇敬与悲哀。
在竖立着十字架的座基前我站定,我看见它靠近我的一面上新錾的碑文——那些刻画分明、冷酷无情的黑字概括了她的一生。我试图读那碑文,我读到“纪念劳娜——”。那双柔和的蓝眼睛泪水模糊,头部疲乏地低垂着,她在那几句天真的道别话里央求我离开她:哦,要是最后的回忆能比这愉快一些,那该有多好啊;我曾经带着这回忆离开了她,我又带着这回忆来到了她的坟上!
我试图再次读那碑文。我看见最后面是她去世的日期;而那前面云石上刻着几行字,其中有一个人的姓,那姓搅乱了我对她的怀念。我绕到坟的另一边,那上面没有文字可看——没有世间的邪恶把她和我的精神分隔开。
我在坟前跪下。我放下双手,头枕在宽阔的白石上,闭起了疲倦的眼睛,不去看四周的尘土,不去看上空的天光。我要让她回到我身旁。哦,亲爱的!亲爱的!现在我的心灵可以和你交谈了!又像那天一样,咱们彼此道别——又像那天一样,我握着你那可爱的手——又像那天一样,我的眼睛最后一次看着你。亲爱的!亲爱的!
……
时光流逝;寂静像浓重的夜色般笼罩着一切。
经过片刻奇妙的宁静,最初听到一阵轻微的窸窣声,仿佛微风飘过坟地上的小草。我听见窸窣声向我缓缓移近,后来觉得那声音改变了——变得像是向前迈进的脚步声——最后脚步声静息了。
我抬起头来看。
夕阳即将西沉。浮云已经飘散,小丘上映出柔和的斜照。死亡的幽谷中,白日将尽时是那么阴冷、明净、寂寥。
在我前面远处的坟地里,在阴冷明净的残辉中,我看见两个女人并排站着。她们正在朝坟墓这面看,向我这面看。
那是两个女人。
她们向前走近几步,又停了下来。她们蒙着面纱,我看不见她们的脸。她们止住脚步,其中一个揭起她的面纱。在寂寞的斜阳中,我看见了玛丽安·哈尔科姆的一张脸。
那张脸改变了,似乎已经经历了多少岁月!一双露出疯狂的大眼睛,带着奇怪的恐惧紧盯着我。那脸憔悴消瘦得可怜。它上面好像刻画着痛苦、恐惧与悲哀。
我从坟前向她走过去一步。她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她身旁那个蒙着面纱的女人气息微弱地喊了一声。我止住步。这时我已神魂飘荡,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控制了我的全身。
蒙着面纱的女人离开她的伙伴,慢慢地朝我走来。玛丽安·哈尔科姆独自留在原地,她开始说话了。那声音我仍旧记得——那声音没有改变,像那恐怖的眼睛和消瘦的脸一样没有改变。
“我这是在梦里呀!我这是在梦里呀!”可怕的静寂中,我听见她悄悄说出了这么两句,接着她就跪倒在地,向上空举起紧握着的双手,“天父呀!让他坚强吧。天父呀!在他需要的时刻,帮助他吧。”
另一个女人继续向前走;缓缓地,默默地向前走。我盯着她——盯着她,从那时起只顾盯着她。
为我祈祷的人的声音开始颤抖,逐渐低沉,但接着又突然升高,她恐怖地叫唤,拼命地叫我避开。
但是,那蒙着面纱的女人已经控制了我的全身与灵魂。她在坟的另一边停下了。她和我面对面站着,当中隔着那块墓碑。她靠近了座基另一面上的碑文。她的衣服触到了那些黑色字体。
叫喊的声音更近了,而且越来越激动地提高了。“遮住你的脸!别去朝她看!哦,上帝救救他吧——!”
那女人揭开了她的面纱。
“纪念劳娜·格莱德夫人——”
劳娜·格莱德夫人这时正站在碑文旁边,正站在坟头上瞧着我。
[故事的第二个时期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