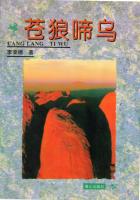劳娜的神情慌张,已经使我感到惊讶,再加上我仍为梦里刚看到的景象感到凄惶,所以,她一说出那名字,我对突然获悉的事简直是经受不住了。我呆在那里,一言不发紧张地瞪着她。
劳娜一心想着那件事以致竟没注意到她的答话给我带来的影响。“我看见安妮·凯瑟里克!我和安妮·凯瑟里克谈话了!”她又说了一遍,好像我没听清她的话似的,“哦,我有许多事要告诉你,玛丽安!去吧——咱们在这儿会被人撞见的——赶紧到我屋子里去。”
劳娜急忙忙地说完这些话,拉住我的手,搀着我穿过书房,走到底层特别为她设置的那间库顶里边的屋子。除了她的贴身女仆,谁也不会突然来这里找我们,她先把我推进房间,然后锁上房门,拉上里边的印花布窗帘。
一时间,我仍不能摆脱那种奇怪的麻木感觉。但是我越来越相信,并且已经深深感觉到,一些错综复杂的事情,一些早已威胁着劳娜和我的事情,现在已经突然紧紧地围困住了我们俩。我的感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甚至不能够在意识中模糊地加以体会。“安妮·凯瑟里克!”我悄声自言自语,不知所措地重复说,“安妮·凯瑟里克!”
劳娜把我拉到房间当中靠得最近的那张长椅上。她说:“你瞧!瞧这儿!”说到这里,她指了指她的胸口。
我这时才看见,劳娜的那只遗失了的胸针又端端正正地别在那里了。我亲眼看见了胸针,后来又亲手接触到了它,那种真实感仿佛使我混乱的思想又开始稳定了,并且使我的情绪镇静下来。
我能向劳娜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儿找到了你的胸针”。我在这样的重要关头竟提出了一个如此无关紧要的问题。
“是安妮·凯瑟里克,她找到的。”
“在哪里?”
“哦,我该从哪里说起呢,在船库里的地上——我该怎样对你说呢?安妮·凯瑟里克和我讲话的时候显得那样古怪——她看上去身体那样不舒服——她后来又那样突然地离开了我!”
劳娜因纷乱的回忆而激动着,她得声音也随着提高了。在这家里,我日日夜夜都被疑惧困扰着,所以这时立刻向她发出警告,像刚才一看到胸针就立刻向她提出问题一样。
我说道:“窗子开着,它对着园子里的路。轻轻地说。从头说起吧,劳娜。把你和那女人遇见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吧。”
“要先关上窗子吗?”
不用关,但是,要轻点儿说,要记住,在你丈夫家里谈安妮·凯瑟里克很危险。你先在哪儿看见的她?
“在船库里,玛丽安。你知道,我沿着那条小路穿过种植场,出去找我的胸针,一路上留心望着地下。就那样,经过很长时间,我到了船库;一走进那屋子我就跪到地上去找。我正背对着进口寻找的时候,就听见身后一个陌生的声音轻轻地呼唤:‘费尔利小姐。’”
“费尔利小姐!”
“可不是,叫的是我从前的称呼——我以为那个熟悉可爱的称呼永远和我分开了。我跳了起来,并不是害怕,而是感到十分惊奇,因为那声音非常亲切柔和,它不可能使任何人感到害怕。瞧向那儿,一个女人正站在门口瞧着我,我完全不记得曾经见过那张脸。”
“那女人是怎样打扮的?”
“她身上穿了一件整洁漂亮的白衣服,上边披了一条陈旧的深色条纹的围巾。她戴的那顶褐色无边的草帽和她那条围巾显得一样陈旧。我看到她身上的衣服和其他的打扮很不相称,就感到很奇怪,她知道我注意到了这点。‘别去瞧我的帽子和围巾,’她气喘吁吁,急促地说,‘只要有白色衣服穿,对于打扮我都可以不计较。尽情看我身上的衣服吧——我不会为它感到不好意思的。’这话说得多么奇怪,你说对吗?还没等我向她解释,她已经伸出了一只手,我看见我的胸针就在她手里托着。我十分高兴和感激,走过去,离她很近,向她表示谢意。‘既然这样感谢我,您可以答应我一件小事吗?’她问道。‘当然可以,无论什么事,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可以答应你。’我回答说。‘我把您的胸针找到了,那么,就让我给您别上吧。’我真没料到她提出的竟会是这样一个请求,玛丽安,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异常急切,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不自觉后退了一两步。‘咳!’她说,‘您母亲就会让我为她别上这只胸针的。’她提到我母亲时,口气和神情中有着那么一种谴责的意味,这使我对自己的猜疑感到羞愧。我握住她托着胸针的手,轻轻地抬起它放在我的胸口。‘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您认识我母亲吗?我以前见过您吗?’我说。她正在忙着为我别胸针的一双手停下来,紧紧抵住了我的胸口。她说:‘您不记得,在利默里奇村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您母亲在去学校的那条小路上走,一面一个有两个小姑娘伴着她吗?打那时候起,我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高兴去想,只记得这一件事。您是那两个小姑娘当中的一个,而我就是其中的另一个。那时候聪明漂亮的费尔利小姐和呆板可怜的安妮·凯瑟里克可比现在要更亲近的啊!’——”
“安妮·凯瑟里克向你报了姓名,劳娜,你记得她吗?”
“记得的,我记得你在利默里奇庄园曾向我问起过安妮·凯瑟里克,你还说大伙从前都说她长得像我。”
“这件事你是怎么想起来的,劳娜?”
“是安妮·凯瑟里克使我想起的。她靠近了我,我朝她看的时候,突然想到我和她长得很像!她的脸苍白而瘦削,显得疲倦,但是我看上去吃了一惊,就好像我生过一场大病,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一样。这一发现,不知道什么是缘故,使我十分震惊,有一会儿工夫我对她完全说不出话来。”
“你不说话,她看起来是不是像动气了?”
“恐怕她是动气了。‘您的脸不像您母亲,心也不像她。’安妮·凯瑟里克说,‘您母亲的那张脸是黑糁糁的,您母亲的那颗心,费尔利小姐,是天使的心。’我说:‘真的,我对您怀着一片好意,但是可能我不会恰当地把它表现出来。为什么您管我叫费尔利小姐呀?’‘因为我喜爱姓费尔利的人,憎恨姓格莱德的人。’说到这里,她突然愤怒得像发了狂。在这以前,我根本没看到她有疯癫的迹象,可是这时候,在她眼光中我仿佛看出了疯癫。‘我还以为您不知道我已经结了婚呢。’我说,我想起了她在利默里奇村写给我的那封荒唐的信,同时试图使她安静下来。她沉痛地叹了口气,从我身边走开了。‘我不知道您已经结了婚?我到这儿来,就是因为您结了婚。’她重复了一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在去阴间会见您母亲之前给您想一个补救的办法。’她身子逐渐往后退,最后退到了船库外面,接着就四下里注视和留心听了一会儿。等到再转身向我说话时,她不是走进来,而是站在原来的地方,眼睛向里边瞧着我,手叉在两边的门框上。‘您昨儿晚上在湖边看见我了吗?您在树林里听见我在后面跟着吗?我整整几天都在等着您,想要单独和您谈一下——这一次我丢下了我唯一的朋友,让那朋友为我担心害怕——我冒着险,不顾再被关进疯人院——一切都是为了您,费尔利小姐,一切都是为了您呀。’她说道。她的话使我感到惊慌,但是她说话时有一种口气使我想从心底里可怜她。我相信我的怜悯是真诚的,因为我胆子大起来,叫这可怜的人到船库里去坐在我的身边。”
“她这样做了吗?”
“没有。她摇了摇头,说必须继续站在那儿望风,当心有外人突然到来。她一直守在门口,手叉在两边的门框上,一会儿突然向里边探进来向我说几句话,一会儿又突然向后退回去四面张望。‘昨儿天黑前我到这儿来了,’她说,‘听见您和那位同您一道来的小姐谈话。我听见您向她谈到您丈夫的事。我听见您说没法使他相信您,没法使他不提起那件事。啊!我听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了,因为,在听的时候,我的良心向我说明了一切。我为什么让您嫁给他了呢!咳,都是因为我害怕——瞧我那疯狂的、可怜的、该死的恐惧心理啊!——’她用那条旧围巾捂住了脸,在围巾里边哭边嘟哝着。她会不会伤心绝望得失去了理智,不能控制自己,最后连我也没法应对她呢!我害怕起来了。我说:‘请冷静点儿,告诉我,您当初又怎么可能去阻止我结婚呢!’她揭开蒙在脸上的围巾,茫然地瞪着我。‘我当时应该有足够的勇气留在利默里奇村里,我根本不该被他要去那里的消息给吓走。’她回答,‘我应该先警告您,设法挽救您的,那样不会像现在这样木已成舟了。为什么我只有给您写那封信的勇气呢?为什么我的动机是为了您好,但结果反而害了您呢?那都是因为我害怕呀!我那疯狂的、可怜的、该死的恐惧心理啊!’她重复这句话,又用她那条旧围巾的一头捂住了脸。她那副样子真的可怕呀,她那些话真可怕呀!”
“她一再谈到害怕,劳娜,你肯定要问她怕什么吧?”
“我问了。”
“她又是怎样回答的呢?”
“‘假如曾经有人把您关进疯人院,将来还有可能再把您关进去,您是不是会害怕那个人?’她反过来问我。‘那现在您还害怕吗?如果现在还害怕,您肯定不会来这儿了吧?’我说。‘不害怕了,’她说,‘我现在不害怕了。’我问她为什么不害怕。‘您猜不出什么缘故吗?’她突然向船库里探进身子说。我摇摇头。‘瞧瞧我是一副什么样儿,’她接着说。我告诉她,看到她满脸病容,神情十分忧郁,我感到很难受。这时她第一次露出笑容。‘满脸病容,’她重复了一句,‘您知道我现在为什么不害怕他了吗。我都快死了。您相信我要在天堂里和您母亲会见了吗?如果我见了她,她会宽恕我吗?’我十分震惊,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回答她。‘我老是在思考这件事,’她继续说,‘躲开您丈夫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都在思考。思考到最后,我只好来到这儿了——我要设法补救——我要尽力消除我以前造成的一切危害。’我再三恳求她向我说明这些话的意思,她仍旧那样茫然地瞪着我。‘我能消除那些危害吗?’她主意不定地自言自语着,‘您是可以得到朋友帮助的。所以,如果您掌握了他的秘密,他就会害怕您,就不敢像对待我这样来对待您。她既然害怕您和您的朋友,那么,为了保全自己,他就不得不好好地对待您。他如果好好地待您,如果我能说这是由于我的功劳——’我急切地想往下听,可是刚说到这儿,她突然停下了。”
“你催她继续往下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