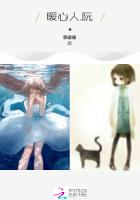如果劳娜糊里糊涂地签了字,而所订立的借据具有什么性质,她个人又会承担什么责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俩都远远缺乏应有的知识与经验。我个人深信,这份文件不可告人的内容,肯定涉及到一笔十分卑鄙恶劣、极尽欺诈之能事的交易。我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因为珀西瓦尔爵士拒绝给人观看或向人解释那份文件,他之所以拒绝,很可能只是由于性子倔强,脾气骄横。我之所以怀疑他不诚实,是因为他到了黑水园府邸后,在言语和态度上发生了变化,而看到这一变化,我就深信他在利默里奇庄园受考验的整个时期里都在弄虚作假。
他那样体贴入微,那样礼貌周到,很好地迎合了吉尔摩先生的老式观念,此外,他对劳娜那样谦恭,对我那样诚恳,对费尔利先生那样温和:这一切都是一个卑鄙、狡诈、冷酷的人所耍的手段,他一朝靠玩弄欺骗达到目的,就撕去了他的伪装,那一天在书房里公然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我不必去谈这一发现使我为劳娜感到多么悲伤,因为这不是我能用任何语言来表达的。我现在谈到这件事,只是要说明我为什么做出决定:除非她先了解文件的内容,否则不论后果如何都不能让她签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准备好一个理由来反对明天的签字,它要在法律基础上使珀西瓦尔爵士无法坚持己见,并使他怀疑我们两个女人是和他同样熟悉商业上的契约和法律的。经过了一番考虑,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我决定写信给我们可以找到的、确信他会为我们细心策划的唯一的忠诚的人。那就是吉尔摩先生的合伙人基尔先生;自从我们那位老朋友因为身体不好退出了事务所,离开了伦敦,现在那事务所就由基尔先生主持。我向劳娜解释:吉尔摩先生曾经亲自向我推荐,说可以绝对相信他的合伙人诚实、精细、完全熟悉她的一切情况;劳娜也完全同意找这个人来帮助我们,于是我立即坐下来写信给他。
我在给基尔先生的信中,尽量把信写得很短,不让它在那些多余的谦辞和无谓的细节上纠缠。在信中,我首先据实说明了我们的处境,然后请他回复信指导,我的信写得简单明白,他不可能误会和错解。我刚要在信封上写好地址,劳娜发现了我只顾忙着写信而完全没注意到的一个难题。
“咱们怎么能及时收到复信呢?”她问,“你的信要明天早晨才能寄到伦敦,邮局要第二天早晨才能把复信送到这里呀。”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克服这一困难,那就是复信必须由律师事务所派一名专差送给我们。我把这一要求写在附言里,请送信的专差乘十一点钟的早车,午后一点二十分抵达我们村里的车站,这样最迟两点钟以前可以到黑水园府邸。并且让他直接来找我,不要回答其他任何人问题,让他把信递到我手里,不能交给其他任何人。
“万一珀西瓦尔爵士明天两点钟之前回来,最好的办法是:你带着你的书或者活计,整个早晨都到外边庭园里,在专差没把那封信送到之前,你别进屋子。”我对劳娜说,“我整个早晨都在这儿等着他,以防发生什么意外或者差错。按照这个办法,我希望也相信咱们不会遇到什么意外的事。这会儿咱们到楼下客厅里去吧。如果两个人关着门在这儿待得太久,那会引起人家怀疑的。”
“怀疑?”她重复了一句,“这会儿珀西瓦尔爵士又不在家,咱们会引起谁的怀疑呀?你的意思是指伯爵吗?”
“也许是的,劳娜。”
“你现在也开始像我一样讨厌他了,玛丽安。”
“不,不是讨厌他。讨厌多少含有轻视的成分,但是我在伯爵身上看不出有什么可以轻视的地方。”
“你总不会害怕他吧?”
“也许我害怕他——有点儿害怕他。”
“他今天出面干涉,给咱们帮了忙,你反而害怕他!”
“是呀。他那样出面干涉,要比珀西瓦尔爵士大发雷霆更加可怕。记住我在书房里对你说的。劳娜,无论如何你别和伯爵做冤家!”我们下了楼。
劳娜走进客厅,我手里拿着信穿过门厅,准备把信投进我对面墙上挂的邮袋。厅门敞开,我走过门口时,看见福斯科伯爵和他妻子正站在外边台阶上谈话,脸朝着我这面。
伯爵夫人匆匆忙忙走进门厅,问我可有空和她单独谈几分钟话。看到这样一个人对我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我把信投进了邮袋,回答说我很乐意奉陪。她勾住我的胳膊,显得异常亲昵,但不是把我领进一间空屋子,而是把我带到外边围着大鱼池子的那圈草地上。我们在台阶上走过伯爵身旁时,他鞠躬微笑,接着立即走进屋子,随手带上厅门,但并未完全把它关拢。
伯爵夫人陪着我缓缓地围着鱼池散步。我以为她要告诉我什么异常秘密的话,但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她所谓要私下里和我谈话,只不过是礼貌很周到地对书房里发生的事向我表示同情。她丈夫已经把全部经过,以及珀西瓦尔爵士对我谈话时的傲慢态度一起告诉了她。她听了这些话十分震惊,并为我和劳娜感到难过,所以现在已经下定一个决心,伯爵已经同意她这一决定,现在她希望我也同意——如果再发生这类的事,她就要离开府邸,对珀西瓦尔爵士的蛮横无理表示抗议。
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像福斯科夫人这样一向异常沉默的妇女,怎么会采取这一行动,尤其是那天早晨,我们在船库里交谈时,双方唇枪舌剑地交换了那些尖锐的话。然而,一个长辈这样亲切有礼地来找我谈话,我完全有责任亲切有礼地回答她。因此,我也用她那种口气答话。等我们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我就打算回到屋子里。
然而使我感到无比惊奇的是,福斯科夫人好像决心不放我走,她还决心要继续谈下去。以前她一向是妇女中最为沉默的,可是现在滔滔不绝地用一些陈旧的废话来折磨我:谈到婚后生活,谈到珀西瓦尔爵士和劳娜,谈到她自己如何幸福,谈到已故的费尔利先生在她承受遗产一事上如何对待她,还谈到许多其他的事,让我围着鱼池子兜了半个多小时,使我感到十分厌烦。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觉察出这一点,但是后来她突然住了口,像开始时的举动一样,朝正屋门望了望,一下了又恢复了冷冰冰的神气,还不等我找脱身的借口,她已自动地撒开了我的手臂。
我一推开门走进门厅,就突然发现自己又面对着伯爵。他正把一封信投进邮袋。他投了信,扣好邮袋,问福斯科夫人这会儿在哪里。我告诉了他,他立即朝厅门口走出去找他妻子,他和我说话时显得无精打采,我转过身去看他的背影,猜想他会不会是有病,或者情绪不好。
为什么我下一步会直接走到邮袋跟前,取出我的信,又向它看了看,隐约地感到一种疑虑;为什么我第二次看了信后立刻想到,为了更安全起见,需要把它重封一次:这一切都是神秘的,那道理也许太深奥,也许很浅近,但我是无法知道的。大家知道,女人做事往往出于一时的冲动和直觉,连她们自己也无法解释,我只能设想:正是这种直觉促使我采取了这一无法理解的行动。
不管这样做究竟受了什么影响,反正我回到自己房间里,准备重新封这信。我认为幸亏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这样做了。我本来是像平时那样封的信:先弄湿涂了胶的封皮,然后把它向下面纸上按牢,可是这会儿用手指揭它时,虽然已经整整过了三刻钟,但那信封并未粘紧,并不需要撕,一下子就被我揭开了。也许,我没把它封牢吧?也许,胶质有什么毛病吧?
要不然就是——不!我一想到第三种可能,就感到一阵恶心。我真不愿意去想那件本身已经十分明显的事。我对明天的事态发展几乎感到恐怖——一切要看我是否能够小心谨慎,是否能够克制自己。有两件需要当心的事,它们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的。我必须留心律师事务所的专差什么时候给我送来回信;我必须在外表上注意对伯爵保持友好。
6月17日——晚餐时我们又聚在一起,福斯科伯爵又像平时那样显得兴致勃勃。他竭力逗我们乐,仿佛一心要我们忘掉那天午后书房里发生的事。他很生动地描绘他历次旅行中惊险的经历,以及在海外遇到的那些要人的趣事,他从欧洲各地的一些男女当中举例说明各国社会风俗习惯奇怪的差异,可笑地叙述他年轻时一些天真和愚笨的事,说他如何影响了一个二等意大利城镇里的时装,如何模仿法国小说为意大利的一份二流报纸写一些低劣的爱情故事:他一串串的话说得娓娓动听,很能直接和巧妙地迎合我们的兴趣与好奇心,劳娜和我听得出了神,而且,说来似乎很矛盾,我们也开始像福斯科夫人那样十分钦佩他。女人能抗拒男人的声望,男人的爱情,男人的金钱,男人的仪表,然而她们没法抗拒男人的一张嘴,只要那男人懂得怎样和她们谈话。
晚饭后,伯爵给我们留下的良好印象仍很鲜明,但他却悄悄地退到书房里看书去了。
劳娜要到外面去散一会儿步,欣赏漫长的黄昏垂尽时的景色。出于礼貌,我们当然邀福斯科夫人同去,但这一次她显然已经被吩咐过,所以婉言谢绝了我们。“伯爵也许还需要更多烟卷儿,除了我,”她用道歉的口气说,“谁也不能做得让他满意。”她说这话时,冷峻的蓝眼睛里几乎透出温暖——能令她的主人在吸烟中得到安慰,看来她对这份差事真感到骄傲啊!
于是我和劳娜两人走出去散步。
那是一个空气闷热、浓雾满天的黄昏。四周给人一种零落衰败之感,园子里的花朵已经萎谢,地上焦干,没有露水。我们从静静的树梢上望过去,西面天空呈现出一片苍白和淡黄,太阳在迷雾中朦胧下沉。随着黑夜的来临,看来要有一场雨——就要降落了。
“咱们向哪一面去呢?”我问道。
“向湖那一面去吧,玛丽安,如果你高兴的话。”她回答。
“你好像非常喜欢那片凄凉的湖水,劳娜。”
“不,不是喜欢那片湖水,是喜欢它附近的景色。在这么一大片地方,只有那些沙地、石南、枞树会使我想起利默里奇村。但是,如果你高兴的话,咱们随便朝另一面去也可以。”
“在黑水园,我没有一处爱去的地方,亲爱的。我觉得哪儿都是一样。就让咱们往湖那面走吧——到了空阔的地方,也许比这儿凉快一些。”
我们静悄悄地穿过树荫密布的种植场。黄昏时空气闷塞得令人难受,所以一走到船库,我们都急于到里面去坐下休息一会儿。
白茫茫的雾低悬在湖水上空。对岸是一带浓密的褐色树木,排列在浓雾之上,好像一片低矮的丛树飘浮在半空中。沙地从我们的坐处层层下降,神秘地消失在浓雾的深处。四周寂静得可怕,听不到树叶的簌簌声,听不到林中的鸟啼声,也听不到隐秘的湖水浅处水禽的聒噪声。今天晚上,连青蛙的呱呱声都停止了。
“这儿十分荒凉阴森,”劳娜沉静地说,“但是在这儿咱们可以比在别的地方更安静。”她一面说,一面心事重重地用凝滞的眼光瞅着浓雾中沙地以外的荒凉远景。我看出,她只顾想心事,并未觉察出这时已深深刻在我脑海中的寂寥的印象。
“我曾经答应告诉你我婚后生活的真实情况,玛丽安,免得你再猜测,”她开始说,“这是我第一次瞒着你,亲爱的,现在我决定不再瞒你了。我以前之所以不说出来,那是为了你,部分也是为了我自己。一个女人把自己整个一生都赠给了他,而他恰巧就是所有人当中最不重视这一赠品的人,而现在你要这女人坦白地说出这一切,这对她是很难堪的。无论你待我多么好,对我多么忠实,但是,除非你也结了婚,玛丽安,更重要的是,除非你婚后过得幸福,否则你是不能深切地理解我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她。只好拉住她的手,眼睛含着无限深情紧瞅着她。
“以前,”她接下去说,“我常常听到你取笑自己的所谓‘穷’!你常常闹着玩儿,祝贺我阔绰!哦,玛丽安,别再取笑我啦。为了你的穷感谢上帝吧——穷让你做了自己的主人,使你不致像我这样命苦。”
一个年轻的妻子竟然说出了这样悲哀的话!我悲哀的是她冷静而坦率地说出了真实的话。单是我们一起在黑水园府邸度过的短短几天,已经足以向我说明,向任何人说明,她丈夫娶她为的是什么。
“听到我怎样很快就开始失望、感到痛苦,或者甚至知道了更详细的情形,”她说,你也不必为此难过。单让我自己记得这些事也就够了。只要告诉你,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怎样向他表白心情,再用不着向你详细说明一切,你就可以知道他一向是怎样对待我的了。那一天在罗马,我们一起骑马出去,参观了塞茜莉亚·梅特娜的坟。天气爽朗可爱,庄严的古迹看上去很美,我想到古代有一个丈夫由于爱而兴建了这样一座坟纪念他的妻子,一时我对我的丈夫也更充满了柔情。‘你也会为我盖这样一座坟吗,珀西瓦尔?’我问他。‘咱们结婚前,你说十分爱我,可是,打那时候起——’我再也说不下去了。玛丽安!他连看都不朝我看一眼哪!我心想,还是别让他看见了我含着一包眼泪,于是拉下了面纱。我还以为他没注意到,可是他注意到了。他说:‘走吧。’接着,一面扶我上马一面自个儿笑着。他上了马,我们一起离开了,他又大笑起来。‘如果我给你盖一座坟,’他说,‘那可得花你自己的钱呀。我不知道,塞茜莉亚·梅特娜是不是有一大笔财产,花的是不是她自己的钱。’我没回答——我正在面纱里哭,怎么能回答他呢?
咳,你们这些脸色苍白的女人都是多愁善感的,他说,你需要什么呀?需要听几句奉承和好听的话吗?还好,我今天早晨兴致还不错。我认为奉承和好听的话都已经说了。男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对我们说的那些冷酷的话多么深刻地印在我们记忆里,多么沉痛地伤害了我们的心灵啊。我真想哭上一场,但是他那轻蔑的态度使我收干了眼泪,横下了一条心。
打那时候起,玛丽安,我再也不禁止自己去想念沃尔特·哈特赖特了。我回忆我们俩私下恋爱的那些幸福的日子,从中给自己找一些安慰。除了这样,我还能找什么安慰呢?如果当时咱们在一起,你会在一旁指导我的。我知道那样是错误的,亲爱的,但是告诉我,难道我那样的一个小小错误就没有可以被原谅的理由吗?
我不得不把脸避开了她。“你别问我!你受的这种苦我受过吗?”我说,“我有什么资格来做出判断呢?”
“我总是想念他,珀西瓦尔晚上自己和朋友去看歌剧,丢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想念他。”她继续说,放低了声音,跟我更挨近点儿,“我总是想象:如果上帝肯赐给我贫穷,如果我做了他的妻子,那我又是怎样一副情景。我总是想象,他出外挣钱养家,我穿着整洁的廉价衣服在家里等他,——我在家里为他做家务,而因为必须为他做家务,就更加爱他——我看见他很疲劳地回到家里,就帮他摘下帽子脱了大衣,玛丽安,晚饭时我就用我为他学着烧的小菜儿款待他。哦!我希望他永远不会也像我想念他梦见他那样想念我梦见我!永远不会感到孤单忧郁。”
她说到这些伤感的话时,声音里又透出那已经消失的柔情,脸上又映现出已经消失的美丽。她的眼光又那样带着爱怜注视着我们前面那片衰败、凄凉、不祥的景象,仿佛在朦胧阴沉的天空中看到了坎伯兰那些令人感到亲切的小丘。
“哦,劳娜,别再去谈沃尔特啦,”我说,这时我总算勉强克制住自己,“现在就别去谈他,别惹得咱们这样痛苦啦!”
她站起身,亲切地看了看我。
“我宁愿永远别再提到他,”她回答,“也不愿让你有片刻感到难过。”
“这是为了你好呀,我这样说,是为你着想呀。”我辩解,“如果你丈夫听见你这样说——”
“如果他真听见我这样说,他也不会感到意外。”她这样奇怪地回答时,在沉着与冷漠中显得无所谓。她那种异样的态度,几乎和回答的话同样使我感到惊奇。
“他不会感到意外!劳娜!”我重复她的话,“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可把我吓坏了!”
“这是实话,”她说,“这就是我今天要趁咱们在你房间里谈心的时候说给你听的。我在利默里奇已经向他坦白了一切,玛丽安,不过只隐瞒了一件事,你说那是可以隐瞒的。我就是没把那姓名告诉他,可是被他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