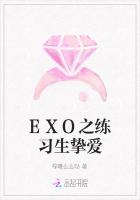第二天,她几乎什么都没有干下去,老是在看表,老在想他这时应当下车了,这时应当找住的地方了,这时应当到办公楼了。
一直到吃晚饭,他也没有跟她联系。她计划好两人一起吃饭,可跟他无法联系上,那时还没有手机。中午饭就没吃,晚饭再不吃她就走不动路了,她可不想在他面前没有精神,这么一想,就到食堂要了一荤一素两盘菜,一口气吃了个干干净净。
晚上大院里放电影,她害怕他找不着她,就一直坐在办公室等着他。
十点,他来了,她以为他会穿着帅气的军官服,他应当知道她喜欢他穿军装的样子,可他却穿着一身西装。人情绪不高,蔫头耷脑的。
怎么了?
带的稿子全毙了。
你这么在意上稿呀?
当然了,单位对这事看得很重,专门来送稿,上不了稿怎么回去交代?
别发愁,让我们共同想办法。对了,你吃了吗?
吃了。
住在哪?
地下室。
地……地下室?
离报社近,我回去了,刚跟单位的报道员打电话了,又商量了个稿子,回去写。
我跟你一起去。
地下室真不是人住的,房子小得刚够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墙上潮湿发霉,天花板上也渗进了一圈圈水迹。
怎么能住这么个地方?台灯也没有。
能有个住的地方就不错了。
你看我刚写了个消息,你是大报编辑,帮我看看。
柳宛如皱着眉头,拿纸巾擦了擦桌面和椅子,然后坐下来,看起稿子来。这个导语不行,现在要紧跟宣传的形势。
身后传来疲惫的声音,那你就大胆改,只要能发表,怎么改,你说了算。明天一上班还要交给编辑呢。
柳宛如一字一句地帮着改起来,说,改完了,你看看?回头一看,张钢已经倒在床上睡着了。
明天就要交给编辑,基层的新闻工作者真难。柳宛如蹑手蹑脚地坐下,想了想,揉揉眼睛,认真地抄起稿子来。十一点半了,稿子抄完,她回头坐到床前,仔细打量着他,他瘦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不过一头乌黑的头发还是那么好看。她真想摸摸那黑发,还有那放在胸前的一双大手,又怕吵醒他,就站起来拉开被子,才发现被子是潮的,床单是脏的。她摇了摇头,悄悄拉灭了灯,走出门去。
第二天一大早她提着早点到地下室,他还在睡着。她在外面等了一小时,才敲门。他吃得很香,看到她抄好的稿子,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上班后,你先送稿子。我也再给你介绍几个编辑,还有你不要住地下室了,我已经跟我一个同事说好了,他回家了,你住他那。
张钢呆呆地望着她,说,你对我真好,可我对不起你。
胡说什么呀,我俩什么关系?还这么客气。
我昨天就想告诉你来着,一直开不了口。你不用对我那么好,真的,我已经结婚了,我们没有未来。
人都是要结婚的。柳宛如嘴上平静,心里一下子凉到冰点:他结婚了?结婚了?
你这么想,我也就没有这么顾虑了。
咱们还是朋友对不?你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
你还真的帮我?
当然。
柳宛如不是圣人,虽然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帮他,毕竟他们曾经是恋人,可是一想到他已经是别人的丈夫,这帮忙的心情就不同于昨天那般痴情,打了折扣。
我怎么能这样?我怎么能这样?我爱过他,现在还爱着他,他在北京没有亲人,我就是他的亲人呀。柳宛如自责着,决定跟他一起去找自己认识的一位首长让他在报社实习,一方面系统地学习学习,再认识些编辑,多发些稿子。他们上到公交车上,柳宛如不时凝望着他,忽然感觉结婚后的他的确不对劲了,他的身上已经有了别的女人的气息,不再像过去那样让自己迷恋。我怎么了,别这样想。她强迫自己不能狭隘地处理她曾经美好的初恋。
这时上来一个少妇,站在了张钢的前面。张钢两只手左右开弓地握着扶手,远远看去,好像拥那女人在怀中,这让站在张钢身后的柳宛如极其不舒服。她叫了一声张钢,她希望他能转身,跟自己对面站着,也许随着车的摇晃,她还能忆起他们曾经温馨的浪漫。他毕竟是人家的丈夫了,她不能再跟他拥抱亲吻,可是总可以在这偶然碰撞中再回忆一下。不知是张钢怕转身让周围的乘客不满,还是其他,反正他回答,不用了,你不是说快到了嘛。
柳宛如又望了望那女人,女人的长发刚好抵着张钢宽广的胸怀,她忽然极其难受,忽然决定张钢的忙不帮了。虽然到首长家里,她也给首长讲了要多帮张钢,可是在张钢出门后,她给首长说,当着他的面,我是没办法,我跟他没有多少关系。
回来时,张钢很是高兴,提议两人到公园去,柳宛如借口有事,回宿舍了。两天里,再也没有去看张钢。
张钢的事当然没办成,三天后,他就回部队了。柳宛如强忍着难受,到车站去送他。她心想我做到了仁至义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