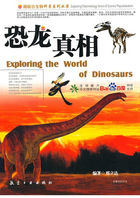诗歌,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而英雄史诗与叙事长诗,就更为丰富。在回族文学史上,也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光彩夺目的优秀民间叙事诗,如著名的《马五哥与尕豆妹》《吆骡子》《歌唱英雄白彦虎》等。然而,与民间文学相比,回族作家创作的叙事诗则比较鲜见。解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扶摇直上,各种题材、体裁的回族文学作品频频问世,回族文学新人不断涌现,叙事诗的创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回族诗人杨少青创作的“花儿”叙事诗,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例。
“花儿”是流传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并为回族人民深深喜爱的一种民歌形式。杨少青生活、工作在回族聚集的宁夏南部山区,对民族文化艺术传统有着深厚的感情。几年来,他在艺术道路上努力攀登,不但创作了大量“花儿”体的抒情短诗,而且写出了《回族英雄马和福》(连载于《回族文学》丛刊总第员、2期)、《姆旦与秀兰》(载《新月》1982年第员期)、《阿依舍》(连载于《银南文苑》1982年第员、2期)三部“花儿”叙事诗。这些“花儿”叙事诗,以其饱满的形象、鲜明的风格和新颖的形式,为回族文艺百花园增添了新的光彩。
“花儿”是以抒情见长的。它短小精干,格律谨严,多用来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纯真美好的爱情。而叙事诗,则是一种以诗的形式来刻画人物、描述故事的文学体裁。别林斯基就曾指出:叙事诗的特点是“要求创造个性和特有的戏剧安排”。杨少青的“花儿”叙事诗,则是“花儿”与叙事诗自然而和谐的结合体。它以“花儿”为基本形式,融抒情与叙事为一体,在不破坏“花儿”原有风格、格律的情况下,根据作品内容的需要适当延长了它的篇幅,增强并提高了它的叙事性及表现力,成功地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回族人物的典型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回族人民的斗争生活。
读完这三部作品,它们的主人公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歌唱英雄马和福》中的马和福、《姆旦与秀兰》中的姆旦、秀兰,还是《阿依舍》中的阿依舍、萨里哈、李满拉,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作品植根于民族生活的肥沃土壤,善于挖掘民族地区特有的矛盾和斗争,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性格,因而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阿依舍》通过主人公阿依舍、萨里哈同恶势力、旧礼教的殊死斗争,表现了回族青年为追求理想的爱情生活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姆旦与秀兰》则在新旧两种思想的交锋中,塑造出秀兰这个普通然而体现着新的时代思想的社会主义回族新人的形象。《歌唱英雄马和福》主要塑造的是回族革命烈士、中华苏维埃陕甘宁豫海县回族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的形象。这部作品真实反映出马和福由一个逃难的“穷河州”,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光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发展过程,生动地刻画出马和福那豪爽、刚直、嫉恶如仇、机智果敢的性格特征。如第一部“热依斯的口唤”一节中,管家热依斯狐假虎威,硬逼着马和福连夜给他打个日本柜。马和福如期交来后,只见那地柜“螃蟹腿儿乌龟背,毒蛇头翘在个天上;缠头恶魔在背上卧,母夜叉立在身旁”,热依斯不禁勃然大怒:“胆大的奴才想造反,敢给我热依斯画像?”然而,“和福闻言笑一场:‘热依斯错怪我四匠,我打的地柜有名堂,胜过那日本的式样。画蛇(哈)添足为青龙,热依斯骑在个背上;二太太随爷享清福,早日(哈)升进个天堂’。”他凭着自己的大胆和智慧,把这个狗奴才痛快淋漓地戏弄了一场。这里虽然带有夸张的成分,但通过这个精心设置的典型事件,马和福那机智、勇敢,甚至还带有某种程度“狡黠”的性格,就鲜明而立体地呈现出来了。
三部作品在塑造人物时,不仅注意了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还能够把人物的个性特征与民族的共性特征结合起来予以表现,因而就使他们具有了更强烈的典型性。如《姆旦与秀兰》中,父亲姆旦在自然灾害面前鬼迷心窍,放弃农副业生产,想跟人搞投机倒把,以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女儿秀兰得悉后,耐心地劝诫爹爹道:“通天梯子接云霞,进天堂靠的四化;你不守本分犯王法,脸抹黑对得起谁家?”当父亲不听女儿的规劝,一条道走到黑,结果反倒蚀了老本,债主盈门,恨不得上吊时,“双扇扇门儿单扇扇开,鲜花儿一朵飘进来”,秀兰姑娘走进屋内,掏出自己上山干活挣来的2000元钱,情真意切地对父亲说:“半年的辛苦踏青山,百斤发菜汗水换”“只要爹爹心意回,女儿的辛劳没白费。”终于感化并挽救了失足的父亲。由于历史的原因及传统的影响,回族妇女的性格一般都比较含蓄、内向,因而,秀兰在对父亲的错误做法进行斗争时,就采用了这种以实际行动说服、感化的方法。这样,在秀兰的身上,我们就不仅看到了回族姑娘温柔、体贴的美好心灵,而且看到了回族青年坚忍、倔强的性格特征。
《阿依舍》中对阿依舍、萨里哈、李满拉的描写在这方面尤为成功。阿依舍与萨里哈是两个有着强烈反抗性格的回族青年,共同的命运及思想感情,使他俩倾心相爱。但是,恶霸地主“北山狼”却垂涎于阿依舍的美貌,想娶她做偏房;阿依舍的父亲李满拉虽不忍自己心爱的女儿落入虎口,但也不愿把她嫁给萨里哈。面对这重重阻挠和突然降临的灾难,他俩并未退缩,而是坚定地唱出:
儿的主意女儿拿,
不拿时由不得自家;
任你剖心扒肝花,
不死了还这个做法!
你我的面前三道关,
一道比一道艰难;
宁叫他皇上的江山乱,
决不叫俺俩的情断。
这岂止表达的是二人在爱情方面的坚定信念,也是回族人民传统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气质的激发,是宁折不弯、无所畏惧的民族性格的流露。
李满拉这个人物,也是十分典型的。在李满拉的身上,真实地表现出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心理状态及多样的性格侧面。一方面,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本分老实,能隐忍的时候尽量隐忍;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刚烈的汉子,具有回族人民敢于反抗,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因而,他既对“北山狼”的蛮横行径坚决反抗,表示:“人心没底蛇吞象,恶狼休想再逞狂,有花决不插粪堆上!”宁愿拼出身家性命,也决不屈服于“北山狼”的淫威;同时又顽固反对阿依舍与萨里哈恋爱,认为:“鬼精子丫头不识羞,浪门子维下了朋友?败坏了门风丧廉耻,依玛尼活活儿跑丢!”这反映了那个时代上年纪的回族老人的典型心理。由于这个人物的设置,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更深入的开拓。它说明,压制这两位回族青年的还有传统的习惯势力,有像枷锁一样套在回族人民头上的旧的观念。所以,当阿依舍发出:“王法教规是埋人的坟,把女子压在个底层;个家的终身旁人定,一辈子活人是难心”的呼喊时,我们不但看到了作品有别于其他爱情题材作品的闪光之处,而且还看到了作品中主人公性格的新的升华!
恩格斯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典型,永远是社会性的。三部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但注意了他们的代表性,而且同时注重并表现了“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因而使其具有了比较深刻的社会内容。
如《歌唱英雄马和福》在塑造马和福的英雄形象时,对促使他们成长的周围环境的描绘上也是典型的。作品这样描写当时的社会:
苛捐杂税(是)如牛毛,
闹兵荒壮丁(哈)乱抽;
富户(哈)豪门油满肠,
穷阿哥皮包着骨头。
形象而真实地揭示了那个时代回族社会生活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当时回族地区苦难的生活现实,不但给我们提供了马和福性格发展中令人信服的生活依据,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
《阿依舍》讲的虽然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在阶级社会里,爱情问题不是孤立、静止地存在着,它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阿依舍》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如作品中写阿依舍是:“苦菜花开黄一片,苦根儿难嚼难咽;苦姐儿出在桃花岭,苦泪儿把人的心淹。”写萨里哈是:“黄连的树上落阳雀,苦命鸟吃果哩;桃花岭来了萨里哈,穷汉娃受孽障哩。”而写“北山狼”则是:“团总金衔挂肩上,大寺学董镇九坊,官衙土匪都联上。”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是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是吃人的黑暗社会埋葬了这两个青年的纯洁爱情,扼杀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这样,由于作品把典型形象置于典型环境之中,在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中刻画人物形象,所以就使这些人物具有了比较深刻的社会内容与典型意义。
无论是作为叙事诗,还是作为抒情诗,抒情都是它们的显著特征。别林斯基曾指出:“感情是抒情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杨少青的三部“花儿”叙事诗在运用“花儿”的基本形式叙事状物,塑造民族典型性格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了“花儿”长于抒情的特性。作者满怀对本民族的一片赤诚,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于笔下,因而使这三部叙事诗都有着强烈的抒情色彩。
作者的激情,似乎已在自己的胸腔内凝聚了很久很久,所以,往往在作品的一开头,便阻遏不住地迸发出来。如《阿依舍》:
棒打鸳鸯雨浇莲,
合欢树怕分两半,
有情人单怕无情棍,
活生生遭罪含冤。
哎哟——
东雅于上良多磨难,
冰河里血泪滚翻……
通过渗透着强烈感情色彩的诗句,把我们引到一个深沉、忧伤的艺术境界之中,似乎是在倾听歌手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唱出一支悲伤的歌。尤其是“哎哟——”这个具有典型民歌风味的呼唤性衬词,它虽然没有确定的含义,但却表达了一种忧伤而绵远的情思。这情思脱离了那无力表达它的文字,变成了音乐的声音,仿佛是作者沉重的叹息,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
诗人的丰富感情,也流露在他所描写的具体物象上。在三部“花儿”叙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典型环境的刻画上,还是在客观景物的描写上,都渗透着作者浓烈的感情色彩。如《歌唱英雄马和福》中叙述豫海回族自治政府成立的一段描写:
五彩云托住九重天,
吉祥鸟
银嗓门放了个宽展;
十锦旗笑迎东风卷,
金鼓儿
擂动了同心的山川。
动人的口弦水朗朗弹,
干花儿
漫醉了喜庆的少年;
不是圣纪、古尔邦,
清真寺
抹一层节日的浓艳。
别林斯基说:“纯抒情的作品看来仿佛是一幅画,但主要之点实则不在画,而在于由那幅画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感情。”这段“花儿”确实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作,它不仅使我们如身临其境般看到了回族地区特有的风俗画面,感受到了浓厚的民族与地方风味,而且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这一欢乐的环境之中,感受到热烈的喜庆情绪。甚至连无生命的锣鼓、锦旗等客观物象,都抒发了诗人欢欣若狂的主观情感,反映了他称颂这一在中国回族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盛大节日的鲜明态度。
诗人火热的激情,集中体现在自己塑造的回族正面人物形象身上。马和福、阿依舍、萨里哈、索秀兰身上,都寄寓着诗人深厚的感情和热烈的赞颂。他没有过于琐碎地描写他们的外貌,而是集中篇幅,大笔泼洒,抒写了他们的内心思想和感情,热烈地讴歌了他们的心灵美和行为美。如在《歌唱英雄马和福》中,当英雄不幸落难,宁死不屈,被敌人押上刑场时,作品以大段抒情讴歌了英雄的冲天浩气,表达了乡亲们的无限思念,从而使作品的主题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再如《阿依舍》中,当外有“北山狼”威逼,内有李满拉责罚,矛盾冲突发展到白热化的时候,作品并没有把篇幅用在惊险情节的渲染上,而是紧紧围绕着诗歌抒情性的特点,把大段篇幅用在了阿依舍与萨里哈二人内心感情的抒发上,这样就鲜明地突出了二人藐视一切封建王法、勇于反抗黑暗势力、大胆追求幸福生活的叛逆性格。在作品末尾二人殉情而死时,诗中写道:
北风卷起六月雪,
化做克番身上裹,
石崖遮体坟一座,
天昏地暗夹雷火,
青松低头唱挽歌,
泪雨泛起万顷波……
这是宏大的悲剧气氛的渲染,这是诗人沸腾感情的迸发!作品通过夸张的描写与奇特的联想,通过自然景物的活化铺陈,造成了一种撼人心灵的悲剧效果,深切地反映了诗人对追求幸福、追求理想的回族青年的无比同情,对昧凶残、专横暴虐的封建反动势力的无比愤恨!
为了使“花儿”更好地叙事状物,塑造民族典型性格,抒发民族的炽热感情,这三部“花儿”叙事诗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与艰苦的探索,从而在民族文学体裁的发展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传统“花儿”,大多是一首三句或四句,至多不超过六句的“散花”,虽有个别的“整花”,如《三国》《西游》《杨家将》《花唱十二月》之类,但形式单调,内容陈旧。杨少青的“花儿”叙事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革新,表现了民族生活的新内容和新面貌,因而受到了人民的欢迎。
首先,三部“花儿”叙事诗都广泛而灵活地用了各种派别“花儿”的形式为自己的内容服务。如“花儿”中存在着河湟与洮岷两大流派。河湟“花儿”常见的形式是头尾齐式(一首四句,分两段)、折断腰式(一首五句或六句,分两段);洮岷“花儿”常见的形式是单套子(一首三句,句句押韵)、双套子(一首四句至六句,不分段)。这些样式作为抒情的小令自有其独到的优点,但作为叙事诗来说,则容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假如作者囿于一种样式,便会产生单调、乏味之感。是,杨少青把它们统统接受过来,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在三部“花儿”叙事诗中,我们就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作品既有河湟“花儿”的样式,又有洮岷“花儿”的样式,这样不但使作品变得活泼、生动,而且还进一步丰富了“花儿”的表现力。三部“花儿”叙事诗不仅打破了流派的局限,广泛地吸收、利用了“花儿”的各种形式,而且按照作品中内容的要求,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恰到好处的发挥了它们的所长,产生了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别林斯基说:“有这样一种抒情诗作品,其中诗和音乐的界限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花儿”可以说是这样一类的作品,它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它的不同的调式,往往反映着不同的节奏特点。一般来说,河湟“花儿”音调悠扬,节奏舒缓;洮岷“花儿”音调激昂,节奏急促。杨少青根据它们的这种特点,在作品中交替使用。如在《阿依舍》中,当赞美主人公的美好形象,抒发他们心中的美好情感时,作品往往采用河湟“花儿”的头尾齐式或折断腰式;当描写激烈的冲突或主人公紧张的情态时,往往采用洮氓“花儿”的单套子式。这种调式的不时替换,语言节奏缓、促相间的有规律的起伏,不但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音乐色彩,而且更好地表达了其中的思想内容。
在语言艺术上,这三部“花儿”叙事诗也是很有特点的。作者努力学习民间文学艺术的优秀遗产,继承并发扬了“花儿饶比兴”的良好传统,广泛运用了夸张、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使其作品的语言形象生动、色彩绚丽,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例如在《阿依舍》中,阿依舍听见“北山狼”逼婚的消息,忙去找萨里哈商量,可是,找到他后,她却:
暸着阿哥害羞了,
粉腮儿泛起个红了;
盖头儿贴在脸上了,
泪珠儿串成个线了。
运用凝练、传神的语言,把初恋的回族少女见到心爱的情人又羞又急、又娇又嗔的生动情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再如,作品描写萨里哈:
一殁老子二殁娘,
苦水里跌绊子哩;
十五上学成尕石匠,
泪河里栽跟头哩。
从群众的口语中提炼出夸张、生动、形象的语言,不仅有力地表现出了萨里哈的贫苦,而且富于地方色彩。三部作品除了吸收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生动形象的口语外,还有选择地采用了一些波斯、阿拉伯语汇的译音,如前面所引用的“东雅”“克番”等,因为这在回族群众中,并不是什么异国情调,也不是猎奇造作,而是普遍流行使用、反映特定民族生活内容、渗透强烈民族情感的语言,许多优美的想象、充沛的情感、特定的生活内涵,正是通过它们表现出来的。对此,我们应该予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三部“花儿”叙事诗在语言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善于从回族传统民歌中汲取营养。作者对传统“花儿”抱着既认真学习的态度,又不拘泥于它们的原样,亦步亦趋进行生硬的模仿,所以,写出来的诗句既保持了“花儿”特有的风貌,又不是它们简单的翻版。如《阿依舍》中:
想哥想得难入梦,
暗数天上的星星;
我两个不是一娘生,
离开时咋这么扯心。
熟悉“花儿”的人一看就知道它是借用了下面一首民间“花儿”:
天上的星宿(么)对星星,
并蒂莲开花(哈)同根,
我和阿哥不是一娘生,
离开(者)咋这么扯心。
后者虽不乏优美、贴切的比兴,但情与景之间缺乏内在联系。而前者由于把天上的景物与人物此时内心的具体感情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并通过以数星星来入梦的生动情节映衬女主人公因思恋而产生的失眠,就使诗中静止的画面动了起来,使我们不仅从中看到了人物的外部动作,而且窥见了她的内心感情,从而成为符合叙事诗要求的一个情景交融的动人场面。
总之,杨少青的“花儿”叙事诗创作是成功的,他在艺术上的探索值得肯定。当然,这些作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们甚至在一些方面比较幼稚。然而,“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关键是要扶助它发育成长。这就使我们在对杨少青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希望文化艺术有关部门,一切热心于民族文艺事业的同志,伸出自己的双手,尽自己的努力,为回族文艺的更快发展,为回族文学新人的茁壮成长,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载《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