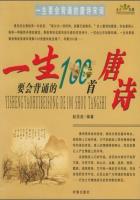关于什么是节奏,前人多有解释,朱光潜在《诗论》中设《诗与乐——节奏》专章予以论述。概而言之,“节奏是宇宙中自然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则。节奏产生于同异相承续,相错综,相呼应。……艺术返照自然,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具体到诗,其节奏受到3种影响。诗是文字的艺术,而文字的声音与音乐有关联,而意义则是音乐所没有的。诗的节奏,在声音的层面上,受发音器官的制约,必须有所承续,错综,呼应;在意义的层面上,又受词义、词的组合的影响,不能不以停顿、间隔来区分;再则,诗又是感情的抒发,情感的起伏、往复也能够影响声音随之而变化,从而对节奏造成影响。
在诗里,最小的节奏单位是顿,即朗诵(默诵亦然)中产生的自然的必须的或长或短的停顿,类乎音乐的节拍。
说话的时候,通常是一个句子完结时才作停顿;而诗用于吟诵,就得放慢速度,在诗行中就要作若干次比较短暂的停顿,于是作为最小节奏单位的“顿”就应运而生。对顿的研究是从古诗引入新诗的。由于在古诗中顿的划分是格式化或形式化的,如五言句就是三顿: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从时值讲,有说成二顿半的);七言句就是四顿: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亦说三顿半)。有时这样的划分会与语义发生龃龉:“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按照语义是应该这样划分的: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但是这样读起来就与散文近似了。这就说明,诗与散文的区别,很显著的一个要点是,诗具有形式化了的节奏,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新诗的分顿却复杂得多。五四时期,把“顿”称为“音节”比较普遍,但是因为与语言学里的“音节”(汉字一个字读出来就是一个音节)混淆,后来就不再采用它。经过研究和实践,如今基本一致的意见是,格律体新诗中,宜以二字顿和三字顿为主。三字顿可以包含两个词。如“一粒子/生成个/富庶的/家园”。四字、五字的结构一般可以分解为二顿,如“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带虚词的四字结构可以采取形式化手段使之消解为二字顿。在这个问题上,胡乔木与卞之琳的探讨是很有成效的。如“顾不上/对落叶/的容光/鉴赏”,就把“的”字后靠,避免了比较冗长、致使节奏感受到影响的四字顿。这种处理实际上在古诗里可以找到依据:“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黄河/之水/天上/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都是这样诵读吗?闻一多对于自己的《死水》的节奏很满意,曾经以之为例,说明顿的划分: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明确了顿的划分,顺理成章就该说到组顿为行的问题了。
“行”是大于顿的节奏单位,一个诗行由若干个顿组合而成。一般2-5顿一行比较常用,一顿行是个别的现象;六顿的诗行也不多用;六顿以上的诗行一般应该避免,因为比较拖沓,节奏就不鲜明了。下面各举几个例子:
那/一夜雨
从巴山
落到/眼前
right——刘年《巴山夜雨》
包含了一字顿、二字顿、三字顿,以及独顿行、二顿行;
三顿行、四顿行、五顿行各举一例:
喜欢舞/枫林的/秋叶
喜欢追/云空的/鹤翼
right——宋煜姝《风》
多少年,你如同/小舟/一叶
始终/漂泊在/我的/思念里
right——陶菲《别离》
城市/化山冈/阻断/树的/生路
饕餮者/炊烟/熏炙/树的/枯骨
right——王端诚《哀树魂》
如前所述,新诗的跨行现象比较常见。跨行可以化解长句,增强节奏感。如: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right——郭沫若《维纳斯》
新诗中,顿的划分以语意为基础。写作格律体新诗,在使用跨行手法时,为了凑齐每行的顿数,或者押韵,有可能生硬地割裂语意,破坏和谐。这种弊端,甚至名家也难以避免。骆寒超在《20世纪新诗综论》中就对卞之琳的《飞越台湾上空》提出了批评:
是岛!我们/的岛!还想望
见一下/应该是/熟谂的/人群,
指出为了保持每行四顿和押上交韵,竟把“望见”一词活生生割断。这种因律害意的做法,不可取。
在建行这个范畴,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是不能忽略的。
一是林庚先生发现的“半逗律”。他是从古诗诗句的结构规律得到启发的。古诗的诗句与语法意义上的句大多一致,如同一句话分主语、谓语两部分一样,诗句往往可以划分为上下两部分:五言是上二下三,如“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而七言则是上四下三,如“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是倒装句)在格律体新诗里,尤其是九言四顿和十言四顿的诗行,半逗率的运用比较广泛。因为容易得到协调的效果,便于使用排比、对仗的修辞,所以值得重视。试举戴望舒《烦忧》的第一节(下节是“回文”)为例说明:
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假如有人/问你的名字
我不敢说出/我的烦忧
应该注意的是,新诗的这种上下的划分,并不一定依照上主下谓的语法关系,这四行诗若按半逗率划开,就连一行也不是主/谓式。还有,可以采用上五下四和上四下五两种方式。
不过,应该明确,半逗律只是建行的一条规律,而不是金科玉律,不具普适性。
二是诗行以单音词收尾还是以双音词收尾的问题。何其芳留意到现代语言中双音词居多的这一明显变化,指出了以单音词收尾的古诗和民歌在反映现代生活时所受到的局限,主张为了与口语一致,应该尽量少用单音词收尾,以避免整篇节奏的失调。卞之琳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发现:一首诗里,若是双音词收尾的诗行占优势,全诗就是倾诉性的朗诵调;而单音词收尾的诗行占优势,就成为歌咏性的吟诵调。这两种节奏式都具有音乐性,也都不脱离民族风格。诗行收尾方式不仅关系到节奏,而且关系到全篇的总体风格。何、卞二位对此的研究是对于格律体形式理论的重大贡献。
格律体新诗是合顿为行,又组行成节,然后联节成篇的。
节与节之间用空行隔开。每节的行数和每首诗的节数都无须统一规定,完全视需要而设。这就是闻一多指明的和近体诗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为诗人们的创造力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诗节在格律体新诗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组节的样式和节与节的对应关系就决定了诗的体式。其变化无穷无尽,使格律体新诗能够随诗人的意愿,根据表达的需要任意创造,体现了它的无限可操作性,亦即其体式的无限可能性。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详论。
第四节 格律体新诗的三大类型
经过90年的实践与研究、总结,格律体新诗的三大类型已经凸现。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这一可见可知可感的诗坛新生事物,已经是客观的存在,不容轻易抹杀了。
把已有的格律体新诗进行科学的分类,是在新旧世纪之交,对于格律体新诗这一研究主体认识的深化与细化,这一升华与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具体描述三大类型的“姿容”之前,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绘制这个“蓝图”的历程吧。
闻一多把格律分为两个方面:属于视觉的是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属于听觉的有格式,音尺,平仄,韵脚,而格式是基础,是前提。新诗的格式是相体裁衣,是层出不穷的。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比如典型的十字行是两个三字顿和两个二字顿组成的,典型的九字行是三个二字顿和一个三字顿组成的。
何其芳继承了闻氏的这一理论,又有所改造,提出了“均顿”说。这与闻一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并不要求每行字数相等,而只是要求顿数相等,字数允许参差。他认为,这个加上有规律的押韵,就是格律体新诗的必要充分条件。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何其芳理论中谈到民歌的局限性,竟遭到一场围攻。此后新诗格律问题被打入冷宫,视为禁区,人们噤若寒蝉,这一理论当然谈不上发展。直到80年代,格律体新诗理论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已有创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格律体新诗自身的类别和体式框架逐步有了明确的认识。可以说,这就开创了自闻一多、何其芳之后,格律体新诗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走在最前面的当数邹绛先生。他是一位诗人,也是翻译家。1984年,他编选了《中国现代格律诗选》,重庆出版社于次年8月出版。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本这样的选集。邹绛的书前长序《浅谈现代格律诗及其发展》是格律体新诗理论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此文扼要总结了格律体新诗发展的历史,梳理了已有的基础理论,还将这一诗体与中国古代诗歌、外国格律诗,以至自由诗作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更有创新意义的,则是他的编选体例。他按照当时自己给格律体新诗划分的类别来编排作品,并在序言中加以说明。而稍后出版的另一本同类选本中,作品仍然按诗人组合。
邹绛是这样分类的:其一、每行顿数整齐,字数整齐或不整齐者;其二、顿数个别出“格”者;其三、一节之内,每行顿数并不整齐,但每节完全或基本对称者;其四、以一、三两种形式为基础而有所发展变化者;(以上均要求有规律地押韵)其五、符合上述4类条件的无韵诗。遗憾的是,他没有为这几种类型的格律体新诗命名。
对于格律体新诗进行分类,予以命名,而且大同小异、不约而同的是万龙生、程文和孙则鸣。万龙生在上引《回顾、现状与展望》中,就把每行顿数相等的称为“整齐式”,把节与节对称、相应行顿数相等的称为“对称式”,而以上述两种基本形式为基础,综合组织节奏式、段式、韵式而形成的各种变化无穷的体式称为“变体”。1997年,他在《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见《诗路之思》)中,把后者改称“综合式”,并提出可以培育若干种“固定体式”(留待第六节详论)。后来,他在编选《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作家出版社,1999年出版)时,就完全按照这样的体例编排,成为一个先例。程文几十年从事格律体新诗研究,与程雪峰著有《汉语新诗格律学》(香港雅园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对牵涉到的各个方面问题都有全面的论述。他把上述前两大类分别叫做“整齐式”和“参差式”。在随后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格律诗大观》中,他也是把入选作品按照这样的分类排列的。而孙则鸣是一位活跃于网络的格律体新诗研究者,2005年12月才把自己经过多次打磨的长篇论文《汉语新诗格律概论》载入《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他分别把上述3种体式称为“整齐对称式”、“参差对称式”和“综合对称式”。
因为他认为对称原则对格律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整齐式也是一种对称的形态,只不过其对称的特点被整齐所掩盖罢了),所以都冠以“对称”二字。但是,为了称说的方便,可以分别简称整齐式、参差式和综合式。
本书综合几家的意见,把格律体新诗分为整齐式、参差式和复合式。
这种分类,不仅符合格律体新诗的实际状况,而且追根溯源,也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态吻合。如果说诗基本上是整齐式,那么词、曲基本上就是参差式。二者交相辉映,形成一部伟大的诗史,构成一座充盈的宝库。
下面就对格律体新诗的三种体式加以论述:
一、整齐式
一般有两种情况,即邹绛划分的一、二类:每行顿数和字数都相等,或者顿数相等,而字数允许参差不齐。赞成前者的以闻一多为代表,赞成后者的以何其芳为代表。程文力主前者,并称之为“完全限步说”,孙则鸣认为二者皆可。不妨说,这两种情况可以算整齐式的宽、严二体,可以任由诗人在创作中自便,而不必置可否。其走向尚待实践来确认。
要指出的是,“齐言体”要建立在“等顿”的基础上。所谓硬切的“豆腐干”就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朱湘算新月派里节奏调理得好的一位诗人,他的《石门集》中许多十四行诗都是11字诗行,看起来很整齐,但是大多是四、五顿间杂,并不协调。就是在闻一多的作品里,也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骆寒超在《20世纪中国新诗综论》里就引用了他的《春光》一诗的8行为例,进行音顿划分,结果有6行是四顿,而五顿和六顿各有一行。虽然看起来整整齐齐,都是12字一行,实际上节奏并没有做到整齐。
受古诗的影响,“齐言”一直是有些意欲创格的诗人的梦想。于是在七言的基础上延伸为九言就顺理成章成为首选的方案。九言诗行,按半逗律或者上五下四,或者上四下五,每行必然安排3个二字顿、一个三字顿,写起来的确比较顺当,所以喜欢使用的诗人不少。对九言体兴趣最大的前有林庚,后有黄淮,各有佳作传世。闻捷和袁鹰合写的访问巴基斯坦的诗集《花环》,几乎全部是9行四顿体的短诗,轻灵优美,相当成功。
比较常用的是七言体,其次就要数十言了。按照半逗律分割,可以有上五下五、上六下四、上四下六3种方式,个别情况下,还可以是上三下七的分割。当然二字顿和三字顿的安排就更加灵活多样了。比如第一种方式就可以是32/32,23/23,23/32,32/23四种。且看林庚的名作《北平情歌》,这是一首“五五式”的成熟十言诗:
冰凝在/朝阳//玻璃/窗子前
冻红的/柿子//像蜜/一样甜
街上有/疏林//和冻红/的脸
冬天的/柿子//卖最贱/的钱
对于三、四行的末顿做了如前所述的形式化处理,即把助词“的”后靠了。可以试试,这样念并不别扭。
整齐式的格律体新诗,可以从每行一顿到六顿,上了七顿节奏感就会大大减弱,所以除非特殊需要,不宜轻易采用。
二、参差(对称)式
参差式就千变万化,不可穷尽了。这是邹绛划分的第三类。
只要想一想宋词中上下阕对称的词牌,就可以知道参差式格律体新诗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模样。二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青年诗人何房子是写自由诗的,却师从邹绛研究过格律体新诗,创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基准诗节。所谓基准诗节,就是一首参差式格律体新诗中,其他诗节在节式、韵式上都必须“亦步亦趋”地复制、“克隆”的诗节。它通常是诗的第一节,是诗人灵感的产物,是诗人情绪律动的记录。闻一多曾对朱湘的《采莲曲》赞不绝口,称其具有内容与格式、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试看其一、二节:
小船呀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娇娆。
日落,
微波,
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
右撑,
莲舟上荡起歌声。
菡萏呀半开,
蜂蝶呀不许轻来,
绿水呀相伴,
清静呀不染尘埃。
溪涧,
采莲,
水珠滑走过荷钱。
拍紧,
拍轻,
桨声应答着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