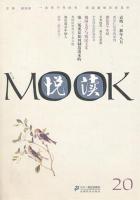垂柳大多生长在村外的空地上,它们垂下的枝条长可及地,遮挡住了树干,也遮住了土路之外的风景。每当有风吹过,柳条一齐摇摆,步子军阵般一致,沙沙的响声是叶片在相互碰撞挤压,它们大踏步向前走着,把土路远远甩在了身后,有时候是土路在自行倒退,渔村的外围身影闪动,那是柳树和土路在发生摩擦,渔村被包围在垂柳疾走的身影之中。看到这齐整的队伍,总会让人肃然起敬,每个过路的人走到这里停下来,手搭凉棚望着柳树的阵列,心里都会发出一声轻轻的感叹。
七月里,卖鱼的小贩们总是喜欢树底下的阴凉,在这里摆开摊子。午后的时光稠密,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空隙照下来,满地金光闪闪,照在臂膀上灼得微微生疼,初夏的太阳不饶人,好在树荫下还有凉风,把灼痛稍稍减轻了些,柳条筐摆在地上,满筐的鱼流泻着银光,真如白铁锻造的一般。一个穿红褂的女人经过摊前,几步跨了过去,她转头望见了鱼,又折了回来。她蹲在地上挑拣,每条鱼都用纤纤玉指捏了一遍,最后终于挑中了三条梭鱼,小贩心里不快但又不敢吱声,只盼她快点挑完。好不容易盼到了,小贩转过身吐吐舌头,恰好被我看见。他顺手在旁边揪了两根柳条,看似随意,实则瞬间发力,来势凶猛,柳树的一个枝丫跟着摇晃起来,落下不少树叶,叶片旋转着落地,他胳膊挥出,驱赶着树叶,没有一片落进鱼筐里,这时柳条稳稳地垂在他手里了,只见他左手拎着柳梢朝上,右手往下一捋,叶子纷纷落地,叶柄的脆响连成一片,顷刻间绿汁喷溅,涂满了手掌,他也毫不在意,手里只剩下光溜溜的柳条,黄褐色的弓形不住抖颤着,他拈起柳条的根部,这里有一处略近于球形的疙瘩,本是连接主干之处,现在却成了利器,直穿过了鱼鳃,又从鱼嘴中穿出,如此往复,把三条梭鱼系在了一处,鱼嘴指着天,鱼尾垂地。女人提着鱼走了,她提鱼的姿势极为懒散,两根手指勾在柳环上,任凭鱼来回摇摆,柳环也不断变换着形状,时而是圆,时而紧绷成一根直线,她带走鱼的同时,把柳条也带走了,满街浓荫还在晃动着,好像在追赶她。柳树如果不是生在半岛,难和海里的梭鱼遇见,甚至捆在一起。就这样,柳树和梭鱼成了死敌,柳条不知穿过了多少鱼的鳃,光滑的枝条结成的绳扣,轻轻缠绕在主妇们的手指上,鱼在底下晃荡着,成为渔村一景。鱼和柳的尴尬关系保持了许多年,沉甸甸的柳条扣在手指上,主妇们想着心里的午饭,心情大为舒畅,她们已经习惯了柳条的柔韧与滑腻,用完的柳条扔在灶台下,锅盖流下的蒸汽恰恰滴在柳条上,直到打扫锅灶时,才发现柳条居然还绿着,有的地方发出了新叶,有的埋在煤灰里,居然生出了细根。小贩们用的柳条筐又何尝不是呢,盛着鱼的筐子多数也是柳条编织的,为了防止渗水,柳条筐里铺了一层油纸。它们总是湿漉漉的,在海水的浸泡下,居然也保持着绿色,那是今年新编制的柳筐,我路过地摊边,忽然想到,筐上那些柳条还是活着的,与飘在它头顶的柳树相对无语。
柳絮起时,古镇上空飞起漫天白烟,人们出门时经常被柳絮迷了眼,有人干脆就戴上墨镜和口罩。柳絮最盛时,人们的衣服也沾满了白絮,尤其是穿黑毛衣的女人,最让她们恼火的就是柳絮,雪白的柳絮落在身上绽开了一朵朵白花,拍打几下,柳絮却又碎成无数小块,丝丝缕缕缠绕在衣服上,和衣服的纤维搅在一起,除了一根根仔细择下来之外,别无办法,许多夜晚,女人们坐在炕上,手里拿着钢针,一根根挑着柳絮,每挑出一根就掷进身边的一小碗水里,迫使它们不能乱飞。一晚上的时间,碗里的水变成了黏稠的白粥,女人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倒在炕上睡着了。
柳絮落地时互相缠绕,变成大团的白球,在地下打着旋。各家各户房上晾晒的鱼也落满了柳絮,柳絮落在鱼鳞上,这时鱼刚摆在房上,还没有干透,等鱼半干时,柳絮已经在鱼身上粘牢了,人们想了很多办法都拿除不掉,若要用刀刮,势必会毁坏鱼身,那样就卖不上好价钱了,如果柳絮放在上面不动,照样卖不上好价钱。不久之后,人们带着斧子锯子,走出各自的家门,把一排柳树伐掉了。叮叮当当的伐木声中,柳絮还在飞着,它们随风而起,轻松跃上房坡,附着在干鱼上,干鱼变成了毛茸茸的怪物,许多干鱼因此变成了不合格的残次品,整筐掀进了臭水沟里。那个下午柳絮照样飞着,随着几声巨响,柳树硕大的树冠纷纷坠地,鱼和柳在这一场争斗中同归于尽。几天后,小贩又把摊子摆好,一抬头发现密集的柳树林不见了,就连树桩也没留下一个,原来树桩都被村民刨回家做凳子了,地上的深坑还没来得及填平,大多数坑里还积了水,坑底还有几个脚印,显然是走夜路的人掉下去又爬上来,这使土路周围陷入一片泥泞。
小贩慌了手脚,平时习惯了用柳条穿鱼,现在拿什么来穿呢?他跟一位老人请教,老人告诉他,这片柳树林长了几十年,如今被伐尽,要找到同样的柳树林并不容易,需要走很长的路,于是他收起摊子上路了,去寻找柳树。我们最终失去了他的消息,他和柳树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是那样彻底,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