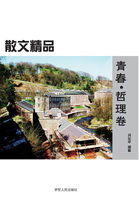头一遭走在那上面,比坐船稳当不了多少。
灰白的窄条子土路,左右是张着大嘴的养虾池,从土路到水面,还有一人多深,土路边缘残缺不全,像一把陈年的菜刀,锯齿斑斑,那是藏在食物里的骨质甚或细碎石粒的轮廓。走了几步,我就开始摇晃,路两侧是陡峭的土壁,池面宽阔的水域上水声大作,抽水机的粗管子正往池里灌着海水,池中心冒起一堆白沫,荡出了半圆的巨浪,层层叠叠压向对岸。仿佛受到它的牵引,我站立不稳,慌乱中把土路踩掉一块,二叔从后边抓住我的衣服,一大块土坷垃盘旋而下,在虾池里绽开一朵浑浊的花。
池间小路的尽头,是二叔新盖的小屋,新打的泥墙坯是翻滚的波浪,我们站在不远处,饶有兴致地观望了多时,体内居然也有了些波浪的动静了。
推开铁门,迎面一铺炕,旁边连着一个简易灶,灶台上还有半瓶白酒。看到酒,我心里踏实很多,到底是二叔的屋。
二叔一早就出门去了。我一觉醒来,旁边的二叔已经不见了,我伸过脚去,被窝还是热的。他应该是喂虾食去了。探身朝窗上一看,他正顺着条小路,向土屋走来。他一手拎着网兜,一手攥着酒瓶子的细脖儿。锃新的一瓶酒,金箔纸的标签在朝阳下放着奇异的光,光点忽然变成圆转的金线,二叔把瓶子抡起来了。有太阳的早晨,走在自家的虾池上,二叔嗓子发痒,忽然弓背作势欲唱。我大气不敢出,单等着听他的好戏文,他喉结滚了几下,到嗓子边的唱段又给压了下去——本地的柳腔戏,多是哭哭啼啼的悲声,跟眼下的好天气根本不搭调。
接下来,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改变了我们后来的生活,它让我们变得烦躁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二叔的酒瓶脱手了。
起先,他还没有注意到,也许是手上汗涔涔,瓶子打滑了,他还在作势挥舞,忽觉手里发空,这时瓶子已经落到一半,他刚看到,已经救不迭了。池间路之下的峭壁上有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把瓶子削成了两半。这时的二叔网兜也脱手了,里面的小鱼小虾沾到水,开始探头缩脑,试探着从松动的袋口钻出来,游进虾池里。
我三下两下穿好衣服出了屋,二叔蹲在那里,往池里看,土路沿儿让他抠掉一大块,豁口处裸露着深色的内瓤。
——别看了,二叔,咱再买瓶。
——再买,就不是这瓶的味了。
二叔起身,在小路上狠踹了一脚,路面的土掉了一大块,紧接着,虾池里响起土块落水的声音。
后来的几天,二叔每每走到路中央,总忘不了跺一脚,土路几乎被截断了。父亲来和二叔换班时,一鼓劲跳了过来,气得说不出话。二婶和母亲来送饭,总也不敢过这条路。父亲铲来土补过几次,豁口总也培不住,后加的土像扔进了无底洞。
终于,二叔在一次大醉之后彻底忘记了那天早上的事情。他醉后醒来,搬个方凳坐在窗台前,安静地吃掉了半罐虾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他曾经的愤懑强加给了我们,他的怒气消散之后,只留下一言不发的豁口土路,还有经过土路中央时跳来跳去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