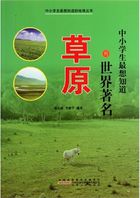胡小桃一直想美美地睡个囫囵觉。
在西三路上,肯定还没有第二个像胡小桃这样起得早的人。胡小桃抡着扫把,从西三路的铁路地道口将大街扫到城外的渭河桥头时,天还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倒完垃圾,回家做熟早饭叫醒上高中的儿子,胡小桃蹬着卖菜的三轮车出摊时,左邻右舍的邻居们才刚刚揉着惺忪的眼睛,从被窝里爬起来。
丈夫去世时,胡小桃还不满四十五岁。丈夫是在工厂的一次锅炉爆炸事故中死的,当时,厂里人慌极了,不知道这个从外地赶来的哭肿了眼睛的女人,到底要向厂里要多少?后来,厂里人问胡小桃,安葬费抚恤金要多少?胡小桃当时“哇”一声就哭了,抽抽噎噎说,娃他爸人都死了,多少钱能换回我丈夫?!厂里人悬着的一颗心算是放下了,处理完丈夫的后事,厂里决定让胡小桃的儿子顶替父亲进工厂上班。丈夫的工友七嘴八舌对胡小桃说,进吧,进吧,你往后的生活也算是有个着落。但胡小桃却犹豫了。儿子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就这样初中没毕业就进了工厂当工人,儿子不是可惜了?最终,胡小桃进厂当了临时工,只是把儿子从老家的山区转进城里来读书。
几年后,工厂倒闭,厂里要给工人发放安置费,胡小桃因为不是正式职工,厂里多发一年工资就算将她打发了。熟人纷纷给胡小桃出主意:到厂里哭去闹去,十万八万向狗日的要去,孩子他爸可是为厂子死的!胡小桃见个生人说句话都脸红,这样的泼她肯定耍不出,最终,胡小桃领了厂里发的工资,就默默回了家。
从前在老家山里,胡小桃是吃惯了苦的,工厂倒闭后,城里那些吃力流汗的累活儿,还没有她没干过的。胡小桃在建筑工地上打过小工,在纺织厂做过挡车工,去餐馆扫过地刷过碗,甚至在一家化工厂的防腐队,她做过几个月防腐工。后来,靠一位老乡帮忙,胡小桃承包下工厂门前西三路上的卫生,白天她在菜市场上摆摊卖菜,天快明时清扫西三路上的卫生。一眨眼,胡小桃进城已六七年了,但她像刚来城里时一样,黑黑的,瘦瘦小小的,整个人像一张被人拉成满月状的弓,天天绷得紧紧的。
时常有人嘻嘻哈哈半是赞叹半是噌怨说:胡小桃啊胡小桃,我算服你了,你咋天天绷得这么紧?!听别人这样说时,胡小桃常常脸一红,头比往常低得更深了。
不是她绷得紧,是胡小桃有她自己的打算:儿子眼看已读高三了,马上就要上大学,可大学不是说想上就能上的,上大学得花钱,她得把儿子上大学的钱一分钱一毛钱一块钱地攒下来。胡小桃在银行里有一个存折,胡小桃每个月雷打不动要往存折上偷偷存500块钱,那可是儿子将来上大学的靠山啊!
但弓,说松就“嘎巴”一声松了。
胡小桃是一天在菜市场卖菜时昏倒的。在医院里醒过来时,医生来到病床前问,你的家属来了吗,让他跟我过去一趟。胡小桃嗫嚅说,我没有家属,娃他爸去世七八年了,我只有一个儿子下个月就要高考。医生望一眼胡小桃,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你的病情况很严重,重度贫血,还有别的诊状,我们建议你马上住院检查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胡小桃一下感觉整个世界顷刻间像是在她眼前突突突跳起来,儿子下个月就要高考了,可千万不能让儿子知道呵!是的,她银行里存着三万多块钱,要是她看病花光了钱,儿子上大学岂不是成了泡影?!最终,胡小桃给医生一声招呼都没打,就结了账回家了。
医生说的没错,胡小桃连她自己都感觉出她肯定真的是有病,一定还病得不轻。有好多回,胡小桃扶着扫把站在街上,往常宽阔笔直的西三路就像一条行驶在浪尖的木船,不停在她脚下左右摇晃起来,胡小桃真想就这样倒下去,闭上眼睛美美地睡上一觉,可上眼皮一挨着下眼皮,眼前一下浮出儿子一张圆圆的脸,她倒下了,儿子咋办呢?胡小桃在心里一遍遍自己对自己说:胡小桃,你不能倒!胡小桃,你真的不能倒下啊!胡小桃用手背狠狠拍拍自己湿漉漉的额头,身下脚步踉跄了几下,胡小桃最终真的就稳稳站住了。胡小桃扶着墙壁回到家,儿子一见就哭出了声。儿子心疼地对胡小桃说,妈你这几天歇歇吧,我考完试就打工养活你。胡小桃用手摸摸儿子的头,对儿子疲惫地笑笑说,妈没事,你安心准备考试吧。
儿子高考那天早晨,胡小桃破例为儿子煮了5颗鸡蛋打来一斤牛奶,望着餐桌前狼吞虎咽的儿子,胡小桃叮咛儿子说,用心去考吧,妈在看着你。
儿子考完最后一场试回到家,胡小桃正半躺在床上。儿子走到胡小桃身边,胡小桃问儿子,试考得好吗?儿子羞涩地笑笑,说,还行,也许说比较理想。胡小桃颤抖着手从身下掏出一个存折,然后告诉儿子密码。胡小桃接着对儿子说,上了大学可别忘了爸和妈。儿子流着泪用力点了点头。看见儿子点头,胡小桃的嘴角涌出了一抹浅浅的笑痕,不久,笑痕像水面上微风吹开的涟漪,很快就消失了。
胡小桃闭上了眼睛。
胡小桃终于可以美美地从一个个天黑睡到一个个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