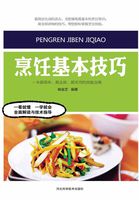益阳在秦以前的历史,先秦史籍缺乏明确记载。
远古天下分九州时,荆州在南方。从《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的描述推知,地处洞庭之野的益阳隶辖于荆州。
相传上古部落时期,北方以黄帝和炎帝为首领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与中原东部的九黎部落首领蚩尤大战于涿鹿,蚩尤战败后溃逃大江之南,在洞庭湖平原及江南丘陵一带,发展并形成三苗、百濮和扬粤等诸民族。著名学者刘范弟认为,蚩尤、善卷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领袖人物。目前考古支持商周时期益阳族属分布大致是:东北部为土著古越人,西北部为零星侵入的巴人,西南部为濮人。
益阳在西周晚期乃至战国早期以前,越人一直是这里的土著居民。文献和考古证实,越人断发文身、袒乳短裙。他们习于舟楫,特别擅长制作独木舟,捕鱼摸虾,过着最简单的原始渔耕生活。1996年,在资阳区李昌港乡麻绒塘大溪遗址,出土了一种高圈足盘,其上刻画有成捆的稻草、饱满的谷穗、成行的大雁以及形似渔网的网格和扣链图案。这是6000多年前的器物,早期先民渔猎耕作生活以艺术与美的形式悄然呈现,不禁让人茅塞顿开。此外,在洞庭湖湿地的浅水湖湾,有着大片的莲藕生长,摘莲子、挖莲藕也是越人生活的一部分。1989年,考古人员在赫山区泞湖裴家山遗址一处小灰坑中,无意中清理出数十粒炭化了的古莲子。当尘封的生命被揭开的那一刻,人们在惊叹之余,无不从内心深处构想着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自然图景。
夏商前后,益阳土著越人在制造石器生产工具和陶器生活用具等手工业技术方面都相当成熟。西部丘陵的邓石桥石湖遗址、北部平原的李昌港周家山和新桥河等大批龙山文化至商周遗址,分别出土了各类石器、陶器、贝壳及翼形青铜箭镞和青铜斧等兵器。“特别是各种多翼形青铜箭镞,极为薄巧锋利,显示了高超而精湛的冶铜制造技术。”从单一游牧渔猎中分离出了农业、纺织业和其他产业,完成了定居。这些古代蚩尤的后代“几乎遍及全县各处丘陵溪谷、湖沼台地”。那么,这些滨水而栖的越人究竟如何择址而居?史书记载,北方华夏民族在黄土高原开凿有发达的洞穴,而生活在益阳的越人却学会了构木结屋,其巢居之所往往择址于高台,大多地势平坦,视野开阔。1988年,资阳区新桥河镇五四村发掘的商代遗址,其中一座房子,几乎在每个柱穴中都填有大块的鹅卵石。专家据此推断,这种干栏式建筑在潮湿多雨的洞庭湖周边,在当时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关于越人的生活习俗,还可以从一些出土墓葬及器物中略加窥视。桃江腰子仑到石牛江一带分布着上百座古越墓,考古发掘表明,越人男性随葬兵器,女性多随葬纺轮,男女都随葬一种用于破篾编织竹席的铜削,有专家定义为篾刀。陪葬的竹席早已腐烂成泥,只留下铜削这种用途十分广泛的小型工具。从出土的兵器看,古越人确实英勇无畏,岁月没有覆盖这些青铜短剑的锋芒,只需轻轻一划,利刃就能划开厚厚一叠纸张。而从赫山区羊舞岭商周遗址发掘的样式各异的陶器,特别是带扉棱纹、水波纹和绳纹的印纹硬陶,同样能看到古代益阳境内的越人富于地域特色的审美情趣。
商朝是青铜时代。当时或已纳入益阳版图的宁乡,曾存在一个青铜方国,发掘出了名震华夏的如四羊方尊之类的国宝,被誉为“中国南方青铜器之都”。而益阳,却只有零零星星的青铜器现身。虽然数量不多,但规格并不低。20世纪30年代,与宁乡交界的益阳安化东山出土了一件绝世青铜酒器——虎食人卣。奇特的造型,入神的刻画,把一只饿虎掳人的惊险场景表现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具有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商代大铜铙,是益阳城市周边出土的又一精美青铜器。2000年7月28日,益阳赫山区千家洲出土的这个高75厘米、重达90公斤的大铜铙,器形规格排全国第三。铜铙上布满由夔龙组成的饕餮纹,线条抽象,造型狰狞,寓意神秘。它既是一种乐器,鼓舞士气,指挥军队进退,也是一种礼器,祭祀苍天后土之间的神灵万物。当然,考古同时显示,商王朝强劲的脚步似乎被某种神秘力量阻隔在长江北岸,洞庭之南依然为土著文化所主导,其文化基石一直未能被撼动。
随着西周楚人的兴起,楚文化开始了长达千年左右的历史进程。楚人在不断问鼎中原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长江以南的广阔疆域。湘北一带地近楚都纪南城,是楚人入湘直抵南岭的必经之路。“至迟在春秋晚期,楚国已对湘北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这里修筑不少城邑。”如汨罗的罗城,为东周遗址,桃源采菱城,相传为楚平王出巡所筑,慈利白公城,相传为春秋战国之交楚白公所筑。湘北东周遗址还有石门古城堤城、临澧古城堤城、平江安定古城、岳阳麋子国城,皆为楚人所筑。毫不夸张地说,环顾四周,益阳基本被这些楚国古城所包围。令人庆幸的是,楚人在益阳资江南岸留下了一处名叫铁铺岭的战国故城遗址。虽然夯土城堤缺失,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址略有区隔,但城址规制完备,建筑规模不小,除视作城址以外,别无其他合理的解释。1985年,在距铁铺岭不远的陆贾山发掘了几十座东周古墓,出土一批包括青铜缶、青铜簠在内的青铜礼器,其精良的造型、精美的纹饰,令人叹为观止。早在1977年,邻近的赫山庙更是出土了一柄“越王州勾”剑,剑身两面都装饰着黑色的菱形几何纹,光泽耀眼,精美异常。剑柄端的铭文以鸟虫篆作书,赫然醒目。此类礼器和兵器的相继亮相,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铁铺岭这个楚人军政治所的想象空间。
相关研究表明,在益阳安化一带,约当春秋晚期,楚人进入本地开发资源,战国时期,极可能是楚巴争夺之地,战国晚期,由于秦人的进入,楚文化渐趋消失。楚文化活动时间不长,干扰大,楚文化未充分发展,遗存也不甚丰富。
在益阳出土的东周青铜器大多是兵器,这不仅是楚人尚武的体现,也是征战历史的沉淀。1993年发掘的资江北部平原的李昌港爱屋湾东周遗址,是个面积抵得上近3个足球场的地方,被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包围,里面密布的水井,为大量人口生活提供了可靠依据。这些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引了水就是一条拱卫城池的护城河,足以抵挡小股车马的进犯。而且,此处临近河道、古驿道,扼守控制四面交通,地势平坦,视野空旷,是绝好的屯兵之地。专家们相信这是迄今为止,在益阳发现的一处十分重要的军事驻地。
在与爱屋湾遗址遥遥相对的资水南岸,黄泥湖的仙峰山也有惊人的发现。这个超大型东周墓葬群,近千座古墓的量级让专家们大跌眼镜。考古发掘的结果是,墓坑粗糙,生土成堆,葬具凌乱,显得下葬草率、匆忙;未见盗痕,已挖掘的700余座中,近1/3的墓葬却空无一物;剑、矛、戈和匕首所占比例大,铜镜、琉璃和玉器之类用具和装饰品罕见。但是,就在这样的墓葬中,却惊奇地找到数枚青铜印,印面各为“楚”和“令”两字的一半。这不是普通的青铜印章,而是用于调兵遣将的兵符,是军队将领组织攻防的命令。专家们相信,黄泥湖遗址是一支勇猛善战的楚国军队战败后最终的归宿之地。有人甚至大胆地想象:两千多年前的日出或日落,一群群悲戚的楚人,正抬着漆绘彩棺,一路旌幡飘展,巫乐齐鸣,从爱屋湾驻地出发,涉江来葬。这样的场景,让人欷歔不已。
剑、戈、矛、匕首和箭镞是益阳楚墓的几种主要兵器。从数量而言,剑的比例最大,占青铜兵器795件的近两成,达139件,戈、矛次之,各为116件和112件,匕首最少,只有区区3件。剑是楚人的最爱,但属于有身份的一群,既体现尚武精神,又显示武士的高贵。剑、戈和矛是冲刺兵器,体现了进攻意识,与土著越人长于狙击、勇猛顽强有关,也与益阳多山林、河湖交错、山岭逶迤的复杂地貌有所联系。灵活、轻便的戈、矛和剑不需要大部队的展开,适应于近距离的搏杀作战。益阳出土的匕首少,说明军队数量众多,无须防止突袭;箭镞不多,可推知楚军实行以攻代守、以进为退的战术。从兵器运用,人们不难发现,当时益阳战事频仍、战斗连续、战损严重,几乎形成“全民皆兵”的局面。
益阳出土的戈和戟中最美、最珍贵的,当属武王戈、错金铭文戈、雕降戈和楚王戟。戈能徒手使用,也可用于车战。不过,在益阳,很难构想楚军战车碾压后大地卷起滚滚尘烟的画面。
崇巫尚鬼是楚人的习俗,祭祀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益阳几十处墓地中,发掘了1800余座春秋至战国的楚墓。统计和分析表明,陶鬲、高领绳纹圜底罐、长颈壶是益阳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据文物考古专家潘茂辉对墓主身份的判读,他认为,个别能够“造祭器”的,应该是从楚都来的,一般陪葬铜鼎、铜簋;大部分是“无田禄者”不设“祭器”的下士和庶民阶层,随葬品为日用器具;至于拥有盂、陶鬲、罐和豆组合的,当是楚系血统人员。
征伐和战争以外的楚人,同样忠实于现实生活,并充满无比奇丽的想象。与商周青铜器狰狞、恐怖和古奥的风格不同,楚人把生活器具用于祭祀和宴乐,用沉稳端庄的造型、繁复纤细的图案纹饰表达对艺术的唯美追求。2006年,益阳李昌港与新桥河搭界的新桥山战国遗址发现一面五山镜,直径19厘米,底纹为繁缛的花叶纹,主纹为五个倒卧的山字,镜面无锈,映像清晰动人,给人以美轮美奂之感。经检索,此五山镜全国仅出土过五面,称之为稀世珍宝乃名副其实。另外,楚人还留下像双龙玉璧、琉璃璧、琉璃珠、玛瑙珠等珠宝玉石。特别是赫山庙出土的连座凤鸟木雕和凤形镇墓兽,均取材于楚人所崇拜的凤图腾,其中连座凤鸟木雕不仅造型精美巧妙,而且寓意吉祥美好,颇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