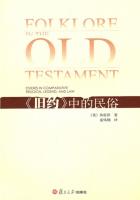在外面跑了一圈,1994年4月14日,赵朴初回到北京,因旅途疲劳,当晚发高烧,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医院。医生连夜给赵朴初打点滴输液。他没有料到,这次住院,一住就是一年多,还差一点儿出了大事。
理疗师潘淑中对赵朴初说:“29年前,您住香山疗养院时,我在疗养院工作。”
算起来,那是1966年夏天。潘医师的话,将赵朴初带到一个特殊的时代。怅忆前尘,赵朴初说:“那时,在西山很闲,整天听大树上夏蝉嘶叫。不久,红卫兵贴大字报,勒令我们滚下山,把我们赶走了。”
潘淑中说:“你们走后,香山疗养院也停了。”
赵朴初摇头说:“那是个不讲理的时代。”
4月19日下午,赵朴初带病到广济寺,出席“恭送佛牙舍利巡礼缅甸法会”,并在法会上讲话。他的烧还没有退尽,每天仍在打点滴输液。
三天后,赵朴初烧全部退尽,医生停止打点滴输液,改口服药。赵朴初站在量体重的盘子上量体重,降低到56公斤了。
这时,夫人陈邦织带来侄子从安庆寄来的新茶。
见到新茶,赵朴初十分高兴,说:“快泡一杯,我要尝尝新。”
8月25日,王忠信从远方寄来红布鞋一双,祝福赵朴初米寿。去年,庭野日敬开祖88岁米寿,赵朴初还为他祝寿呢!今年自己虚年88岁了。这双红布鞋千针万线,那么老远的寄来,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赵朴初对夫人说:“穿这双红帮粉底的鞋,怎么舍得在外面走啊?”今年,朴老已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医院了,他想月内总该出去,因为身体基本上康复了。
陈邦织笑着说:“哪个叫你穿上出门?大红大福,添个吉利。”
高兴头上,赵朴初赋词《朱履曲》:
千针万线情怀。千山万水飞来。怎舍得红帮粉底踏青苔?
数竿窗外绿,万卷架间排。倒不如跷起脚儿躺着瞧着好生自在。
《朱履曲》就是红鞋曲啊!既然红布鞋舍不得穿,就不如躺在床上跷起脚,多看几眼。
词近于游戏,赵朴初却十分高兴,一双红布鞋,出了一个好题目,添了一首好词令!
虽住在医院,赵朴初“外出会客办事”依旧很多,单单9月份,他就会见了日本真言宗各派总大本山会第十一次访华团;会见台湾佛学家印顺法师;会见西藏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等。此外,为朋友题诗、写贺词等文字债务,也耗去他不少精力。
朴老想出院,但医生不同意。他在医院里看书、写字、批阅文件,也不空闲,但比在外间好一些,有时还是要外出会客办事。他自觉体力渐渐恢复,年令大了,有现在这样的精力也就算较健康的老人了。
11月5日,赵朴初88虚岁的生日。生日期间,祝寿者太多,赵朴初在给刘沂的信中,附寄小曲道:
连日人来拱手忙,祝朴老,寿而康。年虽八十八,意气尚轩昂。丘山重,万牛回首,骆驼背上,再添百吨也无妨。
刘沂和陈国生女儿陈淮淮等是好朋友,“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南小栓的常客。最近,刘沂寄来骆驼画片贺寿,赵朴初吟诗中巧妙地将“牛”(偕南方音刘)和骆驼嵌了进去。
李瑞环指示要全力急救
1994年12月中旬,病中的赵朴初想起哑姐的墓还在水边,担心起来。如不尽早迁葬,将来时间长了,就可能被水浸没。四年前,自己回家乡重新迁葬了父亲的墓,在迎江寺为母亲设了莲位,并在寺前镇设立了纪念母亲的“拜石”奖学金,唯独遗憾的是来不及为哑姐迁墓了。
哑姐1945年年初去世,已经半个世纪了。在所有的弟弟妹妹中,赵朴初自思,都尽了一些力,独没有给哑姐做什么。而在所有的姐妹兄弟中,哑姐是最辛苦的,死的也很痛苦。上次回家乡,赵朴初特地去拜了哑姐的坟。那次回去,三个侄子(女)也一起去祭祀了四姑的坟墓。这也是自1947年母亲去世后,在安庆的家人第一次去太湖扫哑姐的墓,以致在这以前,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坟在哪里。假若自己不去扫墓,恐怕这个墓就成为无主坟了。
去年夏天,听说太湖花凉亭水库涨水,赵朴初就担心四姐的坟墓。1958年,太湖修建花亭湖水库,淹没了赵家的状元府,也将哑姐本来在山上的坟边。这是当年家人在选择墓地时,没有想到逮水库引起的。现在,稍一涨水,哑姐的坟就浸到水里去了。寺前镇状元府旧址几个石墩子,浸在水里被湖水不断拍击的情形,常常浮现在赵朴初的眼前。他很想把哑姐的坟移到半山上,离开湖远一点,深埋下去,在上面种一棵松树或者几棵松树,不筑坟包,这样可以为农村节约土地。在树下立一块小碑,将原来的碑深埋下去。碑文则由自己来写,哑姐有知,这也该是她所希望的。
12月14日,赵朴初给侄女婿黄立言夫妇写信,说:“这件事,我想托立言去办。可不可以?”
12月20日早晨,赵朴初从梦中醒来,按几十年的习惯,念一遍“般若经”。护士进门送药,见赵朴初微闭双目,嘴似有所动,说:“愿您早早康复出院。”朴老听了,心花怒开。
护士走后,赵朴初拉开窗帘,旭日高照,雪地映衬着烁眼的光芒,令他眯起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好天气”。赵朴初高兴地舒张手臂,仰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除了按时念“心经”,坚持做一套保健按摩,赵朴初每天揉腹部任脉的穴位300次,经常梳头发等。他喜欢看苏东坡诗集,苏东坡的养生术之一,就是日梳头发千遍。晚上睡觉前,赵朴初习惯一边看书,一边洗脚。因为刚洗了脚,睡意顿消,往往上床倚枕,还要翻一会儿《山谷诗集》。
赵朴初原打算春节前出院回家过年,不料年底又感冒发高烧,不能出院了。表弟陈邦炎从上海来看他,正逢自己吃中药,赵朴初感慨地说:“若不是毛主席主张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与旧诗词,此二者今天就难以为继了。”赵朴初吃的药中,有中成药松仁露,此药润肠清肺养心。
1995年1月10日,腊月初十,赵朴初忽然昏厥数小时,经医院抢救脱险。
这是赵朴初第一次出现心脏停止跳动的现象。“一瞑空诸相,乾坤断见闻。寂光嗟浅涉,开眼渺难寻。”醒后,赵朴初追忆昏迷时的感觉,真有灵魂出窍,悠悠荡荡的感觉,始有此诗。抢救脱险之初,赵朴初眼前幻相一片,仿佛大地怒吼。迷糊中,卧床似乎已经竖起,要踵立行走的样子。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闻报后,迅速赶到医院。听了大夫关于朴老的病情汇报,李瑞环神色凝重地说:“全力急救,不可迟缓。”他紧握赵朴初的手,叮嘱朴老:“既来之则安之。”
赵朴初的病房摆满了各种抢救设备,特护24小时值班。白衣大夫都是全国第一流的心脏病医生,治疗过许多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赵朴初内心感到了他们的仁慈和温暖。脱离危险后,妻子陈邦织安排了晚辈杨百琦、陈文灿和保姆林阿的女儿姨林华等三四人,轮流到医院陪护。她们服侍朴老穿衣、喂饭,对待耄耋之龄的朴老,如同对待童稚一样。“昼夜勤陪护,无儿胜有儿。”朴老在小诗中记载了心中的欣慰。
赵朴初病危的消息,惊动了香港佛教界。
1月28日,宏勋法师代表他们,专程来北京医院探望。近期,陈邦织和医生拒绝客人探访,以绝对保证赵朴初恢复健康。但宏勋法师早上专程到北京,当天乘飞机返回香港,又是香港的客人,情况特殊。因此,陈邦织安排法师进屋和朴老见面。之前嘱他尽量少讲话。
静静地坐在床边,见朴老脸颊瘦削,纹路加深,宏勋法师一阵难过。他握着朴老的手,语重心长,只讲一些养生之道,如少食多餐等。
“谢谢!谢谢!”赵朴初不觉眼泪潸澜,为感念四方高僧大德的厚意,自己也该努力护持,发挥余热啊!
除夕之夜,陈邦织在医院陪赵朴初过年。朴老仍然弱不禁风,好在烧已退。大病后,赵朴初体重减轻了4公斤,只有48公斤了。他信心百倍地对妻子说:“不要紧,我还要看看香港回归呢!”
2月,赵朴初的身体逐渐恢复了些,但下旬因患感冒,引起发烧,他在省级佛教协会工作座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只好请秘书代读。2月28日,赵朴初带病出席了这次大会的闭幕式,并作了发言,提出佛教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组织”一样,也有个“三自”,即自知、自反、自强。
评陈独秀墓“定论终难到盖棺”
1995年4月1日,赵朴初在医院给立言、太平写信说:“你三姑母已回上海,来信说平安。她老人家今年92岁了,去年来北京,跌了一跤,骨折了,幸医治得法,现能起尘,拿拐仗走几步路。眼睛白内障也刮除了,能看见了。她的儿女雇了一位大姐照顾她。”信中,伯伯附寄了“三大”(三大姑)的地址,希望侄女写信去问候。
赵鸣初去年到北京,不料走路跌倒,导致腿骨折。赵朴初伯父赵恩长,生了两个女儿——赵荣绮、赵荣綵,排行老大、老二,赵鸣初的谱名叫赵荣绶,排行老三,写信时,她习惯署名“三大”。小时候,赵朴初和大伯的孩子住在一起,因此,喊自己的胞姐姐喊三姊,喊哑姊四姊。
接到伯父的信,赵锡和夫妇给在上海的三姑赵鸣初写信问安。赵鸣初回信说:“我九十之年很好。跨进九十一就麻烦了!眼睛白内障,且在室内摔跤骨折,现眼已复明,骨折因年纪太大,算能恢复了,只能拄两根拐棍,在室内活动。常能阅读,此心充满着感谢,否则真难度此长日啊!”
收到姑妈的信,太平夫妇寄了家乡的茶叶给她老人家。
接到立言侄婿和太平侄女的新茶,赵鸣初十分高兴。自己的运气好,被他们猜着喜欢喝茶了。从邮局取回来,赵鸣初马上泡了一茶杯!好香,喝了一口,味道很好!年轻时,大概50来岁时,下午和晚上不敢喝茶,喝了茶睡不着觉。现在人老了,年轻时的毛病反而没有了,因为不操心了,喝茶一样睡得好,这就随便了,想喝就喝。侄女一下送这么多故乡的荣,真高兴啊!
赵鸣初想,弟媳妇今年该82岁了,自己应该没记错。不知她的眼睛可还好。贺孟珍和弟弟1913年同年出生,所以,赵鸣初记得她的年龄。
现在,每天早上,赵鸣初一醒就念一遍观世音经文,十遍《心经》。是弟弟朴初在北京送给自己的,已经念熟了,能背。她想教太平的母亲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二字,念成“拿莫”,就是“敬礼”的意思。每天念这七个字,就是供奉观世音菩萨。菩萨的慈悲的光彩会照着她的。
小时候的事,赵鸣初还记得不少。她在给太平夫妇的信中写道:“你们今年多大岁数?太平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生日是否冬月(十一月)初三?”姑妈记忆真不错,太平出生于1937年冬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但眼前的事,姑妈转背就忘了。
4月30日,一位刚从安庆归来的朋友到医院看望赵朴初。谈到安庆,他说:“我曾去陈独秀墓,墓前有一鲜花圈,系缎带题‘浩气长存’四字,无献者之名。”客人的声音很大,朴老的耳聋越来越厉害了。
赵朴初说:“陈独秀在狱中曾书联云:‘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他确是‘浩气长存’的人。后汉徐孺子吊郭林宗母忧,置生芻一束于庐前而去,不道姓名。”
客人走后,赵朴初吟诗《陈独秀墓》:
途穷不改寸衷丹,定论终难到盖棺。
照世心光无愧作,破关虹气处艰难。
直呼益显行高狷,遗著犹能激肺肝。
一束生芻千古泪,谁叹何处不须参。
写毕,赵朴初怕人看不懂“直呼益显行高狷”句,自注道:
余五年前返故乡,访陈独秀墓,墓碑姓名下无“同志”或“先生”之称。顷有友人往安庆归,言曾访陈墓,墓前有一鲜花圈,系缎带题“浩气长存”四字,无献者之名。陈在狱中书联云:“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后汉徐孺子吊郭林宗母忧,置生芻一束于庐前而去,不道姓名。
出关入世愿无事
1995年夏天,天气逐渐暖和。
赵朴初住了一年多医院,心里很着急,对陈邦织说:“很想回家住住。”医院再好,也没有家的感觉啊!
陈邦织劝他:“不要回家了,看见家里乱,你肯定要发脾气的。”
赵朴初说:“保证不发脾气。”
医生见赵朴初的病情比较稳定,也同意他回家住住。
5月15日晨,赵朴初出院了。他自去年4月14日夜入院,至今,住院时间恰好一年又一月。赵朴初平生住医院,这次时间最长。在朴老眼里,病房是他修练的“净名室”,出医院是“出关”,回到南小栓是“入世”。
回到南小栓胡同号,赵朴初顿感亲切。他坐在靠椅上,满心欢喜,吟诗曰:
一年一月净名室,不僧不俗方便关。
出关入世愿无事,少病少恼心长安。
“不僧不俗”,是指居士的生活,也指虽然住院,仍然很忙,不能躲避尘世的打扰。但不管怎么说,在医院里,相对要安静多了。他把出院回家看成入世,重新回到现实的世界。
夏日的一天,袁鹰和朋友商量,请谁来为《忆夏公》写书名适合?1995年2月,夏衍去世了,文艺界的一些朋友打算出一本纪念集。
袁鹰说:“最理想的人是赵朴初老人写了。”
朋友说:“老人家一直在医院养病,不见客,能行吗?”
袁鹰说:“我写封信试试看。”袁鹰也没有把握赵朴初一定能写,但心里想,赵朴初和夏公私交很深,只要自己身体许可,是乐意写的。
接到袁鹰的信时,赵朴初已经出院了。为夏衍的书写字,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了。6月19日,朴老题了书签,并给袁鹰写了回信:
袁鹰同志:
久不晤聚,想起居安吉。奉大函,遵嘱题书签,附上,不知可用否。弟病住医院年余,曾与夏公病室为邻,斯人常往,良可伤痛。回忆公有名言:愿听逆耳之言,不作违心之论。固是夫子之道,若以此分论两人,在上者如果愿听逆耳之言,则可望在下者不作违心之论,所谓违心者,违反事实,违反民心,可畏也。然否?请赐教正。顺颂
夏安
赵朴初
六月十九日
夏衍晚年曾对袁鹰说:“处在像我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多听些逆耳之言还是可以做到的,但要不做违心之论,不做违心之事,有时候就比较难。人在旋涡中,对上对下,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形势使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在五十年代连续的政治运动、思想批判中,我都说过违心的话,写过违心的文章。”
“回忆公有名言”,说明夏衍晚年在医院,和病友赵朴初也谈过“愿听逆耳之言,不作违心之论”的话。
声明达赖无权认定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1995年5月17日,赵朴初听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言人关于达赖认定班禅灵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广播后,作为班禅灵童寻访总顾问,对于达赖在国外擅自宣布某个小孩是十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表示十分震惊和愤慨。
七年前,即1989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以第十世班禅大师为首的转世灵童寻访班子,赵朴初和帕巴拉·格列朗杰为总顾问,按宗教仪轨、如法如仪地进行诵经祈祷、朝湖观影、秘密寻访、验证遴选等一系列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二天,赵朴初发表谈话说:
达赖喇嘛竟然不顾一切宣布西藏另一名儿童为“班禅转世灵童”,这是在政治上搞分裂活动,是非法的、无效的。就宗教方面来讲,也是违背宗喀巴大师嘱托和格鲁巴三味耶戒的教理的。佛教界人士都知道,佛菩萨转世,包括西藏活佛转世,目的都是行菩萨愿,救人救世的。活佛和菩萨都是发愿为本,行愿为宗,一世不成,转世再来,所以叫作乘愿再来,即再来继续行愿也!
班禅和达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而格鲁派寺庙普遍供奉的“师徒三尊”中却只有班禅而无达赖。按藏传佛教化身转世的说法,班禅是无量光佛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可见班禅略高于达赖,不存在达赖凌驾于班禅之上,可以由达赖来认定班禅问题的。
达赖喇嘛搬出“师徒关系”也说不过去,以往十世班禅中只有三世曾拜达赖为师,而十四世达赖中却有八世拜班禅为师(未含师从一世班禅学经多年的一世达赖)。师徒关系并不是自始至终都有的,只是随缘而起、时断时续的,并非宗教仪轨。更何况第十世班禅和第十四世达赖根本就没有师徒关系。
通过以上史实,赵朴初的结论是:“达赖喇嘛在寻访认定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根本没有发言权,没有指导权,更没有认定权。”
5月22日,第一届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旨在通过构建三国佛教的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三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维护东亚稳定,维护世界和平。
赵朴初在大会上致词说:
三国佛教徒和三国人民自古以来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三国山水相连,文化习俗同源,宗教信仰也一脉相承。许多纽带把三国密切联结在一起,在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给它一个名字:“黄金纽带。”这条纽带史自有来。回溯历史,佛教在中韩日三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可以说,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
这次中日韩三国佛教会议,是朴老黄金纽带思想的具体落实。因此,尽管他刚刚出院,仍然做了主题报告。
北京的天气不好,近来,连日阴雨一个多星期。空气潮湿,气压低,加上为筹备纪念抗战胜利50年活动,赵朴初写文章、开会、接待来访,身体很疲劳,有点烦躁。
8月12日、13日,在陈文尧秘书的陪同下,赵朴初到西山休息了两天。
“西山难得到,两日作闲人。”山中清泉声声,松柏沿途送香,四围苍翠深深。不知名的野花芦苇在微风中摇动身躯,欢迎着客人的到来。朴老一时换了角色,忘却了纷纭尘世的干扰,清心爽目。他柱仗缓缓而行,脚踏山间石径,边行边吟。累时,朴老就近坐在石凳上,微闭双目,舌抵上颔,双手迎天,深吸新鲜空气,数着鼻息。四周寂寞,唯有一阵阵山鸟鸣啼,闯入朴老的意念中来。
西山有现代化的娱乐—设备歌舞厅,光彩缤纷,华灯眩目。大家请朴老点歌,赵朴初说:“我点《黄河颂》,大家喜欢吗?”大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不仅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爱国歌曲,也是抗战时朴老在星期聚餐会上唱过的歌曲。
下山后,赵朴初又忙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