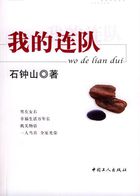不知道为什么,从网站上搜索到的狗肉馆电话全都打不通,有的没人接,有的是空号,有的说是打错了。另外,朋友W给我几个药检中心的电话,我都打了一个遍,对方或说没有对私的检测业务,或说客户不能提供药物的标准的话,没法进去检测。我也不懂所谓的医学上的“标准”是啥东西,看来这些方式,都是不可行的,想从中得到什么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因为工作上没什么事情了,于是我提前下班去了工厂。去之前我顺便去超市买了一捆火腿肠、一包花生零食和一把香蕉。到了工厂,先把火腿肠分别喂了三条狗,然后将一把香蕉送给了食堂里负责喂二黑的那个胖师傅,最后我带着那包花生去找了锅炉房的那个老师傅。不知道为什么他见我来显得有点尴尬,这是对于他的表情的一个直觉。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小床上。这张作为临时休息的床,已经被煤烟熏得黑漆漆,不过,他坐着的地方用几张旧的挂历纸垫上了。他见我进来,坐了起来,依然用那副招牌式的似笑非笑的表情看了我一眼,然后淡淡地寒暄一句:
“哦,你来了。”
“嗯,今天没什么事情,就早点下了班过来了。”我走到床头边的一张脏兮兮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其实不是我不怕脏,只是对于找到一条狗或者与老头拉近距离感来说,这种承受力太微不足道了。
“像你们这个工作多好啊!”
“没什么好的呀,不就是上班下班嘛,跟您一样。”
“嗬,这哪能一样呀!”他奇怪地表现出一种不满的神情。
“您觉得哪里不一样了?”
“首先,你们有周末吧?”
“嗯,难道您没有吗?”
“呵呵,我们哪有,至少我是没有!”他拿出一根烟点着,吸了一口后,继续说道,“你看我——天天不得闲!”
我把手中的那包花生递给他,说:“这是送给您的。”
“哎呀,你还真客气。”他边说着边接过了花生,然后,站起来,从床上抽出一张挂历纸给我,说:“铺上吧,那椅子脏兮兮的平时也没人擦。”
“哦,谢谢啊。”我突然感觉一包花生的作用还是明显的。我问:“您每天都要在这里呆多长时间?像我们一般都是八小时。”
“我这跟你可不一样。”他说,“我每天早上五点左右来工厂,然后,八九点回家,下午三四点再来上班,一直到晚上六七点。”
他说到“早上五点”的时候,我的神经突然绷了一下,感觉像突然被人扎了一针,但是,为了谈话顺利进行,我尽可能让自己表现出平和的状态。我说:“哦,这样也挺好的呀。您家离工厂不远,就当作玩了。”
“当作玩?我可没有这么觉得!”他放大了声量说,“你看外面那一堆煤,我要一车一车地装车,然后再拉进来,送进锅炉,也够我累的!”
“您就当作锻炼身体了。”
“锻炼身体?呵呵。”他埋怨地说,“我的腰都累出病了!”
“您元旦那周请假就是因为腰病吗?”
“那可不是!”他说,“看病都花了一千块钱了!”
“那您的腰现在好了吗?”
“花了一千元还能不好吗?”
“现在看病都挺贵的。”
“可不是嘛。好在我的身体还可以,不然真看不起病。”
“您一个月——是多少钱?”
“五百。”他回答得干脆利落,但是可以听出不满的情绪。
“哦,那您像上回那样请假一周,扣工资吗?”
“管他呢,愿扣就扣呗。”
他的语气很轻松,我想要是扣钱的话,他肯定不是这样,肯定会满腹牢骚。于是,我试探地又问了一遍,说:“应该不扣吧?您是请的病假。”
“嗯,他扣我也没理由啊。谁不会有点病呀!”
“是,是,就是嘛。”其实我问他知道扣没扣钱,是想衡量一下他一周的工资与黑市中犬类交易所产生费用的差距。既然不扣,那就没有比较的意义了。就算他参与这次丢狗事件,那么,不管多少回报,他都是坐收渔利了。尽管内心深处,我不愿意这么去猜想一位老人,但他确实与大多数慈祥的老人不太一样。与他聊天的过程中,我明显感觉他的内心充满了抱怨,对工厂不满、对社会不满。
“你老家哪儿的?”他问。
“哦,我是南方人,在北京上学,毕业后就留在这里工作了。”
“多好啊!像我们只能干点烧锅炉的活。”
“您以前是做什么的?”
“过去啊,什么都干过!”他吸了一口烟,颇为诚恳地说道,“说实话,年轻的时候也偷过狗啊猫的。不过,那时候是因为穷,饿得没办法!”
“哦!?那——那些狗啊猫的主人,会找您吗?”
“找啊,能不找嘛。”
“都是怎么找的?”
“哎呀,也就是问问谁偷了而已。不像你这样……”
“不管怎么说,它也是活生生一条命啊!养了两年了,这感情在那呢!”
“谁家丢了狗,谁也不会舒服的,放心吧。”他说,“就说我后门那家收废品的,丢了狗也会嚷嚷几句呢……”
“那个收废品的是当地人吗?”
“不是。不过,他已经在这儿收了很多年废品了。”
“他就光收废品吗?”
“嘿,人家就干那一年也能挣个十万八万的。”
“不会吧?”我难以相信收废品的利润会这么高。
“人家现在把老婆孩子都接到北京来了!一家全干这个。”
“人家过年啊——那叫一个丰盛啊!山珍海味的!呵呵,我们这村里没有几家能比得上的!”他的脸色很难看,语气听起来酸溜溜的。
“他家丢的那条狗,都吃什么呀?”
“吃什么?人家每顿饭都有肉,那剩菜剩饭就已经让那狗吃得肥得流油!还想怎么着啊!”他说,“不过,人家还真没像你这样天天找狗的。”
“是啊,那条狗——我投入不少精力和休息时间,一个月还要花上近两百元的粮食费用呢。”
“唉,你们这些人啦,我看是钱多没处花!”他白了我一眼,不屑地说,“我家的狗一天就两个馒头,多的没有。”
“您家是什么狗啊?”
“一条纯种的大黑背。”他掐掉了烟头,说,“像你那条狗,根本不纯,没必要那么惯着它。”
一条纯种的黑背,在集市上都要好几百甚至上千元,他能花那钱去买?不可能!虽然这么想,但是,我没有去打破砂锅璺到底。我说:“我养狗不管它纯不纯,都会对它很好,就像是家里的一个成员!”
“那你干吗不放到家里养而放到这里来?让人看着别扭!”
“因为我已经有两条狗了,而且这是条大狗,没办法在小区的楼房里养着。”我说的是实话,我确实已经有两条狗了,而且都是成年的公狗,经常打架。由于奥运期间,政府部门对社区里的狗管理特别严,所以只好暂时存放在朋友Q的家里。因为他的家更偏离市区一些,而且活动的空间大。
“哦……那你也没必要对那黑狗好像搞得那么特殊似的。你看工厂其他的狗喂点剩菜剩饭就可以了。”
他怎么对我的狗意见这么大呢?我真不是想搞特殊的人,当初把黑子送来工厂的时候,我是答应厂长黑子的粮食是由我自己来提供的,只是让他们帮忙每天喂一下而已。因为我担心厂里没有那么多吃的,不想加重厂里负担或者减少其他狗的口粮。想想也确实,这样可能把黑子孤立化了,以至于黑子总是不能与其他狗融在一起。我说:“厂里的剩菜剩饭多吗?”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没个准。不过这狗啊,饿两顿也没事!哦,你以为饿两顿就死了?狗的命最硬了,尤其是普通的这种家狗。”
“都说狗有多少条命,我看不见得,在人的手下,一刀就完蛋了!”我想起了集市上触目惊心的宰狗画面。
“呵呵,这狗啊它毕竟还是狗。”
我不想和他再纠缠这个问题了,我说:“偷狗用的药都是毒药吗?”
“那不见得,一般都是迷晕的,回家拿冷水一泼,狗就醒了。卖死狗谁要啊?就像卖给你死猪你要吗?一样道理的。不过,像过去狗皮紧俏的时候,一张狗皮能卖好些钱呢,倒是有直接要死的。但是,现在狗皮不值钱了,就是吃肉。”
“那一般丢狗有找回来的吗?”我想尽快切入正题。
“这丢狗啊,其实也没那么难找的。”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是吗?怎么讲?”
他不语,只是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燃,然后低头抽着。
从他的话里,我越来越觉得他可能是一条重要的线索。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给他,我说:“老师傅,您就帮个忙吧,我对这带不太熟悉,无从找起。”
“不用,不用。”他边说着,边接过了我塞给他的一百元钱。
“老师傅,拜托您了!”我急切地说,“如果能找到不会亏待您的!”
“我试试吧,”他迟疑了一下说道,“我有个发小,也是一个老头,现在还偷狗呢。我帮你问问他吧,也许他认识什么人。”
“哦,那太好了,多谢啊!”我一下子兴奋起来。由于他要在下班前给锅炉添煤,我就借此告辞了。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身体轻了不少,这是黑子被偷以来,头一回有这样的感受。这个锅炉房的老头能给我带来希望的曙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