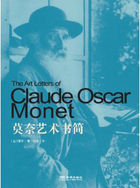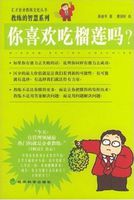尽管几千年来中外古今的许多学者用“秦声”这个优雅古朴并能显示其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词指代秦地戏曲,但是,15世纪初却出现了另一个新概念、新名词――“西秦腔”。我们也就顺乎历史潮流,把此后的秦声发展阶段标名为“秦腔时期”。这一时期,包括明清两代及整个20世纪,共约六百年时间。
秦风裹挟着秦声,跨过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在明代,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起,进入自己的繁荣昌盛阶段。这一阶段,随着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人性普遍觉醒,秦腔也随之更加“易入市人耳目”,从而“清游流播大江南北”,使“海外咸知”,成为中国戏曲“四大声腔”(有两种说法:一是“东柳、西梆、南昆、北弋”;一是昆曲、弋阳腔、梆子腔和皮簧腔)之一。有如清侍读严长明所说:
院本之后,演为曼绰、为弦索。曼绰流于南部,一变为弋阳腔,再变为海盐腔,至明万历后,梁伯龙、魏良辅出,始变为昆山腔;弦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枞阳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秦云撷英小谱》)
明人康海对南北曲风格的评论是:
南词主激越,其变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为朴质。惟朴质,声有矩度而难借;惟流丽,故唱得婉转而易调。(王骥德《曲律》卷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56-57页)
作为“北曲别派”“杂剧遗响”的秦腔,明清六百多年间,学者、文人和艺术家,仍异口同声地称其古名“秦声”。其发展历程,明显地可分为两个阶段:一、14、15、16世纪与南曲四大声腔(昆山腔、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抗衡,并开始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二、17、18、19世纪的流派纷呈,成为剧坛盟主,开创“花部”地方戏******。
一、明代秦腔繁荣昌盛
历史的车轮进入14世纪中叶,中国戏曲在元代繁花似锦胜境的辉煌中,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开始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新局面。这一局面的明显特点是:在各地民间音乐及说唱艺术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戏曲,在北曲杂剧和南曲戏文的影响下,遍地开花,烂漫在神州大地上。如北曲别派的秦腔、曲子、山东姑娘腔、弦索等,南曲的六大声腔: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青阳腔等,不仅在各地形成气候,而且迅速向周边地区以至全国扩展。它们都以自己浓郁而鲜明的泥土芳香与地方特色赢得了广大的观众。城市经济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帮、会馆的推动,不仅使这些土生土长的戏曲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满足了他们“邪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的目的。其中最大的商业资本有山陕商人、安徽商人及江苏、福建大商帮。正是这几个地区的地方戏,在这一时期有了惊人的发展。
陕西地方戏曲秦腔,正是在明代秦商及资本主义萌芽情况下,有了新的发展,甚至出现了繁荣兴盛的景象。
明代是秦腔的兴盛期,尤其是明代后期,秦腔随着城市商品经济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蓬勃发展,不仅锤炼和稳定了自己的艺术特色,表现出作为高度综合艺术的戏曲的成熟和规范化,而且不断从本土向神州大地迅速扩展,从而也影响了北方梆子声腔剧种和其他一些地方戏曲的形成与发展,而且成为梆子声腔剧种的代表性剧种,也成为在明清两代极富影响的权威性剧种,与昆山腔、弋阳腔、柳子腔共称为“四大声腔剧种”,即史学界通称的“东柳、西梆、南昆、北弋”。后来京剧形成后又与昆曲、弋阳腔、皮簧腔并列,为中国四大声腔。
综观明代的秦腔,有以下几个历史特点:
(一)板式变换体(简称板腔体)的音乐曲式结构日趋稳定和成熟
从金元时代开始,秦腔的音乐曲式结构逐步从唐宋大曲的板式变换与曲牌连缀共用,变为专以一只原曲为主的板式变换体,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陆续将北曲和唐宋大曲中的只曲用作伴奏音乐,开始从北曲四大套胚胎中逐步发展成为以板腔音乐结构为中心的戏曲音乐,有时又将套曲插入唱腔音乐中,接着又发展成为单纯的伴奏音乐,最后稳定为连接唱腔音乐的重要艺术手段,习惯称做“过门音乐”(共五种)。秦腔戏曲音乐的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三大板块:唱腔音乐的板腔体,伴奏音乐的曲牌体和打击音乐的罗鼓经,基本稳定了下来。尽管还不时地借鉴、吸收其他曲种(如说唱音乐、民间小曲和其他剧种音乐)丰富、补充自己的表现能力,却仍以“自己”为主。
元末明初的李十三的几本剧目,最先为我们提供了上述信息;正德、嘉靖年间的《二进宫》《回荆州》与《钵中莲》中的“西秦腔”表现出这种曲式结构的基本完成与稳定。晚明宫廷教坊与秦王、楚王梨园的演出,白莲教用“重三复四”的秦腔唱经,都说明这一时期上述曲式结构的定型和不断向其他地方扩张的历史。尤其是《蝴蝶杯》《打金枝》等剧目在城乡与省内外广泛演出,更为上述事实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史证。迨明末,关中八遗老之一的李灌(1600-1676)又把秦腔的板腔体曲式结构移植于合阳皮影戏“线腔”中,使之成为该剧种的主要声腔之一。仍采用慢板、二六板与快板三种板路,并在融化的过程中陆续增加了各板的起、落、间歇与转板的音乐手段。其他后来的小戏,诸如碗碗腔、眉户等,也由联曲体逐渐向板腔体靠拢。
在唱词的编写方面,七字、十字上下句与行腔上还吸收了弹词等一些艺术成分,使之更为丰富、成熟和稳定。
(二)演出的经常性与规范化
秦腔是群众的艺术,这种由群众创造的艺术也必然适应创造者的审美需要与美学情趣,而且主要是通过演出活动来实现和满足这种审美需要和美学情趣。也正是在这一演出活动中,审美对象(客体)与审美主体(观众)二者始终处于一种双向交流与多向撷取的自觉的融合之中。它们的反复作用与活动,不断地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使之臻于化境。作为高度综合艺术的秦腔,同作为审美主体的戏曲观众,始终处于默契和心心相印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中。而演出的经常性与规范化,也自然使这种艺术再创造进一步推动秦腔艺术的成熟与程式化。
(1)演出场所的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约定俗成的庙会秋神报赛演出。汉族是一个泛神论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泛神论的国家。在古代的农耕社会里,亚细亚生产方式支配下的广大群众,从西周开始就盛行淫祀,后来,随着儒、道、释三教的繁衍与交流,在汉族中形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神仙谱系。祭祀这些神仙的场所就是寺庙、宫观、祠堂。发轫于娱神的中国戏曲艺术,也由娱神逐渐演变成人神共娱和专门娱人,即使是从唐代开始的重在娱人的歌舞演唱故事,此时也是假娱神而实娱人,庙会戏曲演出极为兴盛。从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开始,由于朝廷敕祀城隍,这种庙会演出被推向了一个遍布神州大地的纵深地步,城隍级别从国家到州府县再到村镇社户,林林总总,形成了一个密如蛛网的人间冥司世界,也将人间、神仙天庭、冥国三界混同于一体;再加上山神、土地、龙王这些主宰一方水土的神仙,结果使中国大地上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庙宇。为了祭祀各路神仙,几乎每个庙宇前都修建有戏楼(又叫乐楼、戏台、舞亭或舞榭),所以陕西民谚有“城隍庙对戏楼”之说。对众神祭祀,又都有固定的日期(大都为诞辰日),这样,按日历排比,一年四季12个月365天,几乎天天都有庙会,有会自然有戏,而且往往是三天四夜,相沿日久,约定俗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庙会大都由一乡一地的乡绅或庙首主持,向群众是分文不取的,时间又都在农闲时节,所以届时四乡八邻的州府县镇的群众,就比肩接踵而来,史书方志中称这种盛况是“举县若狂”或“举国若狂”。明代随着城市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庙会又与商品贸易结合起来,范围和影响也日益扩大,有时一地的庙会竟有几个省、县参与,人数达一二十万,几近于今天人们说的“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但演戏和看戏仍是最红火、最有魅力的。
这种庙会演戏,也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规程。如对主办者、所选剧种、剧目、戏码及所约班社的艺术水平,以至戏箱子、行头、设备、艺人、角色行当,都有具体要求。如头一天的必演开场戏,求其热闹、烘场子,即招徕客人。第二天为正日,必须演神戏,又因神而异,一天三本十折。第三天为压轴戏,既总结三天演出,又要为观众留下想头,届时还要亮箱底。一年中春天祈福、秋日还愿,戏码和内容也各不相同。如果是两家对台或并台演出,或四台对台演出,就更显示出艺术水准的高低、阵容的好坏、角色的齐整与否、箱底的厚薄和影响的大小,有时还要做到三天三夜不落台。这样,不仅观众支持了秦腔的发展、演出,而且秦腔也进一步陶冶和培养了观众。二者的互动,则促进了秦腔的繁荣和更上一层楼。
第二种是冲州撞府的流浪演出,是秦腔作为群众艺术并借以娱人的主要手段。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迅速发展,这种演出虽然有时已带上商品交易的性质,但它作为艺人谋生的主要手段的本质并未改变。这种“卖艺”活动,在明代随着商品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日趋活跃,把艺人们从穷乡僻壤的故乡推向城镇及外地。比较广泛的艺术交流,也从这里起步。史载:明初陕西三河交汇处的秦腔艺人,已走出故土,过河迈向晋西南的临汾、蒲州和豫西的灵宝、洛阳一带,从而推动了这一“戏曲金三角”区域梆子声腔剧种的嬗变与发展;正德、嘉靖年间,西安艺人也常翻山越岭,走蜀道到四川北部的绵阳一带“游食演出”,进而又有到广、徽、赣的流浪演出。迨万历以后的晚明,随着农民起义军(白莲教起义与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转战东西南北,艺人们的足迹几乎踏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及东南沿海等地,演出场所也就因地而异,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空地或广场竟成了他们最便利、最简捷的演出场所。这种流浪演出,也自然使他们为了适应当地群众的审美情趣,不时吸收、加入当地的艺术品种与表演手法,促进了艺术的交流。
第三种是庭院寄情的缠头演出,随着人性的普遍觉醒,在明代,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人生取向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元代知识分子沦为“九儒”与“下僚”,使传统的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等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因此,不少知识分子“隐于市”同“八倡”为伍。寄情山水和“自比俳优”也成为时尚。正是在这一时尚的驱动下,陕西一批文人学士,在政治上失意之后,仍不忘积极地参与文艺的复兴活动。他们有的自组家庭私班,有的支持秦地的戏曲活动,有的为民间艺人做后台,使一度受挫的秦声在关中“复振”。而庭院寄情的缠头演出,成了这一复振的重要环节。像关中地区的王九思、张附翱、乔世宁、王三聘、胡蒙溪、韩邦奇、韩邦靖、何栋、胡缵宗、王元寿、王无功、马理、吕泾野、屈复、王承裕、刘天虞、赵时春、罗懋登、李灌、马汝骥、赵邦靖、王维桢,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不仅在归田后的很多年里,习惯于逛庙会,王九思还自组私家戏班、主持秋神报赛演出,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地方戏曲活动,经常延揽当地艺人,在自己家里举办饮宴、堂会,作氍毹演出,用以寄情抒怀。抚陕客陕的不少人,如谢茂秦、王世懋、常伦等大都在庭堂内的红氍毹上,偶尔也直接参与演出,不仅有先秦时“舞于庭”的余韵,而且自备行头,自操琴弦,规范演出,提高了艺术品位。一时风气之盛,声闻遐迩。到了明末清初,仍不减其风。钱谦益《列朝诗集》中云:“许宗鲁,家本秦人,承康王之流风,罢官家居,日召故人,置酒赋诗,时时作金元词曲,无夕不纵倡乐。关中何栋、西蜀杨石浸淫成俗。熙熙乐事,至今士大夫犹艳称之。”“顾大猷,字所建,江都人。尝游秦中,赋诗吊古,留连武功、户、杜间,访问康王遗伎,召致坐中,青衫白发,歌残曲,道故事,风流慷慨,长安少年至今传之。”这种演出后,主人往往按艺术水平的高下,赠给赏钱,称之为“缠头”。
由此扩延至诸藩王的宫中演出,如秦王、永寿王、永安王宫中的秦腔班子及其演出阵容庞大、行头讲究、技艺精湛,一仍“汉仪”。艺人有美莲、黑老婆、王兰卿、王桂兰、寇白等,都为人称道。
(2)戏班的三种体制
随着演出的经常化与规范化,秦腔班社从组成和建制、管理上,也逐步稳定为三种体制。第一种自乐班。这是一种由村社群众自发组建的以自娱自乐为宗旨的松散的季节性班社,往往是以社为单位,由一两个活动积极分子出面组织,参加者又多以串戏为主,所演节目多为秦腔传统剧目,杂以民间歌舞,自编自演自娱自乐。人员可多可少,极不稳定,但总有几个台柱子和拿手好戏。随农时活动,农忙歇伙,农闲搭伙,以应四时八节,特别是春节前后,最为忙碌。有时,还应乡村红白喜事、寿诞、娶妻生子的帮场。这些班社,几乎每个村镇都有。由于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也深受群众欢迎。第二种是私人家班。又有两种:乐户,由在籍的乐户人家组成。一是文人学士或有钱人家出资组建,由延聘或私蓄的艺人组成。演出上,前者主要是承应官场召唤,有时也冲州撞府作巡回演出,以谋生计;后者则主要为私家的应酬或娱乐。康海、王九思、许宗鲁等的家班就是这样。因主人的爱好与资金雄厚,所以演出艺术水平较高。第三种是固定班社。这是由一位艺人为主或担任班社长,延揽同行参加的戏曲班社,有比较固定的组织形式。一般人数都在十个左右,有班社长和派班长、跑班长和教练,各担其职。收入实行包场制,分配则是按各人份额办理。艺人也比较自由,不固定在一个戏班内。艺人培养则实行师傅带徒弟的制度。后来随着秦商的崛起,许多商人也出资组建固定秦腔班社,并以商号为名。
(三)随着演出的经常化与规范化,戏曲人物造型也逐渐规范以至程式化
秦腔作为造型艺术,既重视其作为高台教化的思想内容,又讲究外形的美观,即形式美,这就是从服饰(穿关)道具到形体动作设计的美观大方,绚丽夺目,使参与戏曲的各个门类都可以成为一件单个的艺术品,同时也将其内在美外化,诉诸观众的耳目,增强和显示它作为视觉艺术的美学价值。
(1)角色行当
这是一种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艺术处理,即对社会上所有人物进行基本分类,进行体现其基本属性与个性特点的艺术处理。秦腔在自己的长期实践中,将人物概括为十三类二十八门,俗称“十三头网子,无所不备”,这就是:
老生,分安工、衰派和靠把三类;
须生,分王帽、靠把、纱帽、道袍和红生五类;
小生,分雉尾、纱帽、穷生与武生四类;
幼生;
老旦;
花旦,分玩笑、泼辣两类;
正旦,分挽袖、帔蟒两类;
小旦,分闺门、刀马两类;
武旦;
媒旦;
大净;
毛净;
丑,分大、小、武三类。
须生和大净尤为重要,可以显示秦腔的风格特点。
角色行当的细分,表明它在揭示人物性格方面的细致、深刻与准确,是戏曲人物由类型化向个性化发展的具体体现。
(2)脸谱
这是角色行当的一种面部化妆的谱式,主要用于净角,旦角与丑角有时也用。它是区分净角所扮人物性格并使之外化的艺术手法。一幅脸谱即表示一个人物。明中叶的康海自绘秦腔脸谱共131个(即131个人物)。总体上是讲究庄重、大方、干净、生动和美观。颜色以三原色为主,间色为辅;平涂为主,烘托为次,所以极少过渡色。在显示人物思想性格方面,表现出“红忠、黑直、粉奸、金神、绿怪、杂奇”的特点。格调主要表现为线条粗犷、笔调豪放、着色鲜明、对比强烈、浓眉大眼、图案壮丽、寓意明确、性格突出。其谱中的图案多达四五十种,有动物、花卉、水、火、云纹等,是显示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方面。眉多为火焰与鱼纹眉,眼为丹凤眼。丑角脸谱多在鼻眼部涂抹白色,形状各异;旦角多为阴阳脸,一边为旦角化妆,一边为净角化妆。这些又都同陕西凤翔木板戏曲年画和汉中、大荔等地的门神脸谱相一致。这要比明后期的昆腔、弋阳腔脸谱进步得多,艺术含量重。
(3)穿关,即服饰
秦腔的服饰,通称戏衣,又称絷扮。通常分类装入箱内,所以又叫衣箱。具体包括服饰、头盔、道具、布景等。服饰包括从头到脚穿戴,有帽、盔、翅、巾、蟒、袍、帔、靠、袄、挂、衣、铠、蓬、翎、氅、肩等。先是采用“汉仪”,如进贤冠、黄色带和绣衣;后陆续采用明服装。从汉仪到明装,无疑是一大进步,使之更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更具概括性,也易于制作。
(4)道具、效果的普遍使用
道具上的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开始齐全,配以虚拟性动作,使舞台更加绚丽夺目,色彩斑斓。以鞭代马,以桨代船,也成为一种程式。以烟火烘托舞台效果,也已经普遍。嘉靖年间的《钵中莲?借缸》就是这样。舞台装置上的“一桌二椅”也规范化了。
(四)剧目的不断丰富与推陈出新
文人学士的广泛自觉参与、积极推动,使剧目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很大的提高,而且表现的内容更加丰富。封神榜戏、三国戏、水浒戏、西游戏、杨家将戏已经出现系列剧目,而且注意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有机结合,通过戏曲总结历史兴亡。如《吴宫教战》《昭君出塞》《白逼宫》《回荆州》《李逵夺鱼》《蝎子洞》《无底洞》等都有新开拓。值得重视的是出现了大量的反映明代现实生活的剧目,如《二进宫》《秦香莲》《蝴蝶杯》《南天门》等,都直接取材于明代中后期的历史现实,也表明了作者对现实的关心。
(五)迅速向国内许多省区扩散、传播,并影响和推动梆子声腔剧种的形成与发展
在有明一代,秦腔向本土以外扩展,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秦商及西秦会馆(后与山西商人合作共建山陕会馆)的遍布国内;二是艺人及班社的流动演出;三是白莲教与陕西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推动。农民军中的戏班子大都是以秦地班社、艺人为主。尤其是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秦腔为军乐,随之才有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山东、四川、湖北、云南、贵州等地梆子戏系统的远扬与繁衍;而白莲教用秦腔演唱经文,也才有湖北、四川、甘肃等地秦腔的兴盛。明中叶陕西流民大量拥入荆楚、豫西南,于是有《襄阳县志》中所说的本地人“尚秦声”“习秦音”。后来秦腔在荆襄一变为“襄阳调”,再变为“西皮”,成为徽、汉剧种的重要腔调,就肇始于此时。(详见第十章《秦腔的流布及对其他剧种的影响》)
总之,明代是秦腔的成熟与繁荣时期。虽在文字上仍称“秦声”,但“秦腔”的名称已经出现。它不仅能与当时昌盛的南曲四大声腔(昆山腔、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相颉颃,而且雄踞北方,成为北曲遗响的北方唯一戏曲声腔,也成为进入17、18世纪时花部戏曲取代昆曲为剧坛盟主的代表戏曲,从而奠定了中国戏曲史上第三个光辉灿烂时期的坚实根基。这些都表现出它作为板式变换体曲式结构与剧本体制的开创功劳,联曲体的历史随之逐渐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秦腔的板腔体与分场体制成为中国戏曲的两大曲式结构与剧本体制之一,为此后中国戏曲的百花齐放积蓄了内功。
二、清代秦腔成为剧坛盟主
清代是秦腔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而这一鼎盛正是在前述近千年间的积累与实践中必然的迸发。有如涓涓的溪流,在它流淌中由于不拒细流自然会形成长江大河一样。在从清初到清中叶长达二百多年的雅部昆曲同花部地方戏争妍斗奇的“花雅之争”中,秦腔也自然被推上“剧坛盟主”的尊位,从而“海外咸知”“清游流播大江南北”,并且陆续繁衍出一系列乱弹与梆子声腔剧种,在当时中国三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扬州、西安)享有极高的声誉。清初康熙年间京师北京人已不尚昆曲,而尚秦腔,使之成为北京继昆曲与京腔后的第三大剧种;在扬州也出现了“谁家花月,不歌柳七之词;到处笙歌,尽唱魏三之句”的说法,昆曲故地的苏、吴也出现了昆班弟子“背师而学唱秦腔”的情况;西安作为秦腔的故地,形成了“万紫千红”的胜境,这里不仅有剧团间不同风格与绝招的流派,也有艺人间各具风采、各有擅长的特色和流派,更有地域间声腔随地而异的地区流派,可说是流派纷呈。它标志着秦腔艺术的高度发展与成熟程度。秦地五路秦腔(东路同州梆子,西路西府秦腔,南路汉调桄桄,北路遏工腔,中路西安乱弹)争妍斗奇。以至有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西梆子、山东梆子、陇西梆子及江南梆子的“音虽递改,不过即本土所近者少变之”,但仍直呼之为秦腔。
正是在这一胜境中,出现了神州大地近两个世纪的“秦腔热”。从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看,洪?、孔尚任、王士祯、袁枚、吴敬梓、汤斌、陈宏模、王永、刘献廷、李渔、李声振、黄之隽、严冬友、李斗、昭梁壬绍、赵翼、阮元、曹雪芹、董榕、张潮、钱咏、王梦楼、吴太初、李调元、唐瑛、钱初竹、毕沅、吴景旭、张嗽石、李绿园、洪亮吉、孙星衍、孙枝蔚、徐大椿、梁廷楠、戴璐、杨静亨、刘熙载、刘廷玑、支丰宜、张亮际、焦循、杨懋健、铁桥山人、众香主人等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谈论到秦腔。他们之中有些是诗人、剧作家,有些是学者、作家或政治场合的要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参知“秦腔热”的状况。乾隆中期,秦腔艺术大师魏长生在西安、大荔学习五年后三次晋京,三次下扬州、苏州,又有江浙赣皖鄂川三年的行旅演出,更把秦腔这一具有西北黄土高原旷野牧歌性质的高亢激越的声腔剧种,撒遍江河两岸。魏派秦腔成为上述地区各地方剧种争相仿效、模仿的典范。清朝廷三令五申,甚至以榜牒碑石严禁,结果适得其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三庆进京祝厘,扎根京师的秦腔竟被请进皇宫,同徽班徽调“两下锅”演出,接着有“徽秦不分”的“合流”,从而培育出拥有二簧调和西皮腔的皮簧戏(即后来的平剧、京剧)。它的剧目、表演程式等,几乎全部照搬秦腔(齐如山语)。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秦腔的班社、艺人、剧目,都有了极光辉的发展与成就,也很自然地成为砍不倒、压不垮、砸不烂的中国花部戏曲的中流砥柱、剧坛盟主。
17、18世纪秦腔历史有下列几个显著特点:
(一)剧坛盟主的地位
清初,中国剧坛上出现了一场延续二百余年的“花雅之争”。这里所说的“雅”,就是正统、高贵、合乎规范的意思,主要指朝廷扶持并精心培植的昆曲;“花部”是指同雅部相对的非正统、通俗、不合规范的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说:
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
“花雅之争”大体经历了两三个世纪、三个大的回合。第一个回合,是从明末到清康熙中叶,历时一百多年,是秦腔、京腔共同与昆曲的争斗,最后京腔在京师争得一席之地。此后,从康熙中叶历雍正朝至乾隆末年,也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为第二个阶段,秦腔斗倒了昆曲与京腔,在京师取得了剧坛盟主地位,全国出现了“到处笙歌,尽唱魏三之句”的局面,昆曲子弟也纷纷“背师而学唱秦腔”,“借以谋生”;学术界也出现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秦腔热”。第三个阶段,即从乾嘉之际开始到京戏(当时叫“平剧”“皮簧戏”)的形成,也就是道光末年,花部诸腔,尤其是秦腔与徽调的合流,创造出二簧和西皮结合的皮簧戏。中国戏曲史上的第三个繁荣时期正处于此时。值得指出的是三个回合中,秦腔始终作为一支劲旅,走在斗争的最前列,这也为后来的秦腔改革与革命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二)秦腔流派纷呈
戏曲流派的出现,标示着戏曲发展的成熟。秦腔流派的纷呈,告诉人们:此时的秦腔已发展到一个极为光辉的阶段。从当时大量的史料记载可知,清代秦腔流派,繁花似锦,光彩纷呈,百花争妍,万千红紫。具体来说:
因流播地域有别而有东、西、南、北、中五路秦腔流派。
东路秦腔,又名东府秦腔;因主要流行在陕西东部的古同州府即后来的大荔一带,又称同州梆子,也称“大荔腔”“同州腔”。有平、侧二调,常多用拖腔,被称为“东”。著名艺人有喜儿等。
西府秦腔,又名西路秦腔,因主要流行于西安以西以凤翔为中心的陕西西府而得名。唱腔以慢板见长。明代已很兴盛,至清雄踞西府。清中叶吸收“礼泉腔”与“周至腔”“康王腔”的艺术特色,出现了不少连台本戏。并向西扩散至今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
南路秦腔,又名汉调桄桄,以南郑、洋县为中心,唱腔浑厚朴实。扩散至川北一带,对川剧的弹戏有重要影响。
北路秦腔即阿宫腔(又名遏工腔),唱腔翻高就低,以渭北富平为中心,扩及咸阳、渭南等地。中路秦腔,即西安乱弹。被称为秦腔正宗。曾融合其他四路及周至腔、礼泉腔、同州腔、渭南腔诸腔。剧目丰富,艺术力量雄厚,做派细致。
从声腔上说,清初有“秦声派”“西调派”等;中叶有四大声腔,即渭河以南的渭南腔、周至腔、礼泉腔,渭河以北的大荔腔。“音虽递改,不过即本土所近者少变之”。
从艺人的演唱风格与特长上分,则有在全国有影响的魏长生的魏派和西安的以扮相擅长的姚琐儿派、以唱腔擅长的樊小惠派、以表演技艺擅长的申祥麟派和兼有三者之长的岳色子派(简称姚派、樊派、申派和岳派)。他们都有自己的绝技和个性特点。有如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所说:
曲部中有三绝:有祥麟者,以艺擅,绝技也;小惠者,以声擅,绝唱也;琐儿者,以姿首擅,绝色也。
色子姓岳名森玉,长安人,艺少不及祥麟,声少不及小惠,色少不及琐儿,而能奄有诸人之胜,曲部中之刘真长也。
晚清时,又有以旦角见长、承继魏长生流风余韵的陈雨农的陈派;以须生见长、有活关公之称的润润子的张派,人称须生泰斗;有胎里红党甘亭的党派等等。他们都拥有自己的专业戏班子,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都为秦腔艺术的发展与繁荣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上述各艺术流派中,除他们的创始人外,都毫不例外地拥有一批风格相近、志同道合的艺人,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如魏派的再传弟子陈银儿的“闺妆健服,色色可人”;杨五儿的“扮卖婆、村姑,甚是称俏”;陈金官的“以碎步见佳,声容真切”;王湘兰的“以娇取胜,得魏长生真传”;刘朗玉的“歌音清美,每于淡处生妍,静中流媚”;满囤儿的“似怜似怯,传情在无意之间为之”;于三元的状乡里妇人,神情逼肖等等;岳派中的张南如、张友泉;申派中的豌豆花等。真是人才辈出。
在艺术上的创造,更是惊人。尤其是魏长生的改“戴网子”为“梳水头”以及“踩跷”的创造,把秦腔表演艺术推至化境。过去秦腔旦角头面部的化妆比较简朴,只用黑纱包头,他却将其改为在鬓角贴片子、梳彩头,这样不仅可以根据演员的脸型去造型,而且增加了面部的美,可使观众看到“与妇人无异”的面部,造型之美令人叹为观止。踩跷的运用,也有利于男旦碎步腰姿的训练和舞态的婀娜多姿。有如清人杨懋健所说:
俗呼旦角曰包头……今则俱梳水头,与妇人无异。闻老辈言:歌楼梳水头、踩跷二事,皆魏三作俑,前此无之。故一登场,叹为得未曾有,倾倒一时。
这一造型不仅为男子扮旦色的改变面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影响了后世其他所有地方戏曲剧种的旦色化妆。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就说:“他(魏长生)的化妆梳水头,给予旦行很大影响,而他的艺术风格,一直贯串到今天的老艺人于连泉(小翠花)先生身上。”其他如表演技巧与特技方面的“三鞭子”“三杆子”、甩梢子、耍翎子、耍牙、吹火、鞭扫灯花、血彩等等,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近一两个世纪的“秦腔热”,也正是形成于这一历史时期,而且不断升温。
(三)艺术的臻至化境
1.声腔上板路的齐备
秦腔比前代唱腔板路方面更加齐备。从清代中后期的90个剧本的声腔唱板的标示上,可以知道此时的唱板有二流板(又叫二六、流板),是所有板式的原板,中速,两句一个乐段;快板,即原二六板的紧缩;慢板,原板的放慢;滚板,速度自由,因长于表达痛唳的情感,有浓厚的悲怆色彩,所以又叫“哭滚”;齐板(又写作其板、起板、二倒板,又叫倒板)、乱板、过板、代板等十余种。还有由白到唱的“叫板”,结束时的留板;牌子曲数十种,锣鼓点三棰、垛棰等,而且均已程式化。
2.程式的稳定
角色越多越细致,明显表现为由人物类型化向个性化的推进和发展。据对101个剧目的统计,角色在四大行当中多有变化,如生行的有正生、生、小生、末生、老生(已分为武老生、黑老生、白老生)、儒小生、红生(又名红小生)、老红生、官生等;旦行的有正旦(即青衣)、老旦、小旦、花旦、旦、贴旦、丑旦、夭旦、边子旦、才旦、正老旦、魂旦等;净角的有大净、毛净(又叫二净)、番净;丑角的有丑、小丑、老丑和丑公。此外还有外、杂等共31类。其唱、念、做、打与服饰、脸谱等也都形成程式化。
3.剧本结构以“场”为基本单位的分场制
秦腔音乐上的板式变化体曲式结构,不仅开创了中国戏曲在曲式结构上的新天地,也为解决戏曲的音乐与剧本结构相矛盾的问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它在剧本体制上以板式变化构成每场戏的音乐结构,也能够根据剧情的需要,安排场次,可多可少,可有可无,可长可短,可繁可简,可动可静,可文可武,有起有终,有时间有空间,从而能够使音乐结构完全符合剧情的要求,这就突破了杂剧、南戏与传奇套曲分出的界限,加强了剧本的戏剧性,增强了它们的表现能力;同时,念白、做功、舞蹈、武打与唱辞等艺术手段的作用,可以充分得到发挥。剧本可以依据整个剧情的需要,选取最适合的表演手段,灵活安排大场子、小场子、过场戏、重场戏,并把多种艺术手段在各场里有机地结合起来。还可以根据题材、体裁的不同,以一种或数种手段巧妙地安排唱、念、做、打,形成以唱为主的唱功戏,以表演为中心的做功戏,以道白为重的白口戏,以武打为主的武打戏(又叫武功戏)。这种结构,使戏曲文学获得了最鲜明的表现形式。
(四)秦腔理论研究的蜂拥而起与理论著述的大量出现
秦腔理论研究的蜂拥而起与蓬勃发展,是秦腔艺术高度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进一步推动它向更高艺术境界发展的理论总结。“其声甚散而哀”,“易入市人耳目”的艺术鉴赏价值,更是鼓动很多学者濡墨摇笔对之做理论上的概括、探讨它们美学价值与艺术规律的驱动力。这里有声腔的研究,历史的探讨,源流的考核,艺人、班社的艺术特色与成就及剧作家与作品的品评,也有轶闻趣事的摭拾,等等。最早对上述问题作理论的探讨并写出《秦腔论》的是康熙中叶的三原人张鼎望。论中关于秦腔声腔的艺术特点的论述,竟使不熟悉秦腔而专心小说研究与编剧的张潮,备加赏赞。他在给张鼎望的信中说:“暑中急科琅函,兼得大著《秦腔论》,快读一过,如置身鲁桥八景中,听抑扬抗坠之妙,不觉色飞眉舞也。”这里所说“抑扬抗坠之妙”就是秦腔板腔变化的特点。此后不久,江南才子、曾做过乾隆侍读的严长明也在其名著《秦云撷英小谱》中评价秦腔说:“其擅场在直起直落,又复宛转关生。犯入别调,仍蹈宫音,乐经旋相为宫之义,非此不足以发明之。所以然者,弦索胜笙笛,兼用四合,变宫变徵皆具,以故叩律传声,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乎端若贯珠。”《秦腔论》写于康熙四十年(1701)左右。严长明、钱献之、曹仁虎合著的《秦云撷英小谱》,乾隆四十三年(1778)成书。它的显著特点是:把秦腔放在几个世纪的“花雅之争”中加以论述,并把花部的秦腔同雅部的昆曲加以对比,不仅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而且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秦腔必然战胜昆曲、成为剧坛盟主的必然性,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对当时西安剧坛的十四个著名秦腔艺人作了具体而详实、客观又中肯的评述。其中关于秦腔在地域与艺人间所形成的艺术流派的论述,也十分简要和准确。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曾有专门评价,说:“近严、曹、钱诸君,撰《秦云撷英小谱》,言之甚详,又复精确。”进而发议论说:“余谓苏、辛真北曲、秦腔乎。”随后,又有史学家吴长元的《燕兰小谱》(五卷,乾隆五十年,1785)、铁桥山人等的《消寒新咏》(乾隆六十年,1795)、小铁笛道人的《日下看花记》(四卷,嘉庆八年,1803)、留春阁小史的《听春新咏》(三卷,嘉庆初年)、焦循的《花部农谭》(一卷,嘉庆二十四年,1819)、杨懋健的《梦华琐簿》(一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和《长安看花记》(一卷,道光十七年,1837)、张际亮的《金台残泪记》(四卷,道光八年,1828)以及陈伯澜(即陈涛)的《群儿赞》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秦腔艺人、表演艺术、唱腔音乐、剧目等做了理论的探讨,而且各具千秋。秦腔理论研究与论著的风起云涌,在其他剧种中是不多见的。它与艺术实践互为表里,共同推动了秦腔艺术的发展。
(五)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秦腔的深远影响,是与秦腔在海内外的广泛流播相一致的。它不仅“清游流播大江南北”,而且“海外咸知”。在它的影响与哺育下,形成了一个遍布神州大地的“梆子声腔剧种系列”。后复南向为湖北汉剧、广东汉剧、江西汉剧也提供了不少艺术营养。
三、改革、革命、与时俱进阶段的秦腔
20世纪是秦腔不断改革、革命并与时俱进的阶段。时代的风云变幻,给秦腔深深地打上了烙印。改革、革命成为它的中轴线,纵的横的发展,无不被这一中轴线控制或操纵。陕西易俗社和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关中八一剧团及随后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也成为这个世纪扛大旗的秦腔社团。时代的腥风血雨,浸润着秦腔文学、音乐、表演艺术、舞台美术和技艺等许多方面,推进着秦腔的全面改革和发展。湘人叶德辉在《秦云撷英小谱重刊序》中说:
秦声之胜汉调,为人心不静之机。当乾隆盛时,两川用兵,秦中地当孔道,兵徭之困苦,将士之丧亡,西北一隅,皆杀气所蒙罩,而其时南人宦游斯土者,相率金迷纸醉,沉溺于北鄙之音,是殆气机所感动,莫知其然而然。光、宣季年,京朝官酷喜秦声,几如侍读之阿好,不数年革除事起,九鼎遂迁……世运之隆替,胥于声乐肇其端。
20世纪的百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亘古少有的灾难:在反侵略反内战的两条战线上,最终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实现了中国迈向新历程的理想。在“世运之隆替”的过程中,秦腔不仅“肇其端”,而且能够与时俱进,明显地表现出改革性与革命性。
这场改革和革命肇始于“文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界革命”的浪潮中,首先“揭竿而起”的是由李桐轩等同盟会成员创建的“陕西易俗伶学社”。这个秦腔实体在20世纪完成了几个三结合,实现了一个创新。
易俗社的秦腔改革,表现出了秦腔传统的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其社长高培支说:“易俗社的负责任,即是改良社会,改良即是革命,革命即是易俗。时间无停止,革命无停止,社会无停止,易俗无停止。”(《1929年易俗社第七期学生毕业时的训词》)正是这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使易俗社在极其复杂多变的情势下,不断排斥来自“左”的、右的各方面的干扰与冲击,不断革命,勇往直前,取得了令人欣慰和敬仰的社会效果和艺术成就,影响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戏曲革命。
易俗社的秦腔改革与革命,始终同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步进行。它虽然创建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但起步却在19世纪末叶,即中国文学艺术的全面改良运动时期。它的领导者与同仁,都曾亲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成为同盟会成员或积极参与者。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秦腔改革和革命始终与国民革命同步,并成为整个国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作革命的齿轮与螺丝钉;他们始终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尤其可贵的是在当时情况下,他们排除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干扰,坚持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近代戏曲运动的大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和有机组成部分。
(一)秦腔文学的改革、剧作家群体的出现
秦腔的改革首先是对秦腔文学的改革。易俗社的改革家们以身作则,并组织社内外数十名学者、专家、教师,结成了一个秦腔剧作家群体。20世纪前半期,共创作、改编了700多本剧目,而且都被搬上舞台演出。这个数字,比有元一代近百年的全部杂剧创作还多一百多部。按易俗社章程说,有就古今中外政治利弊及个人行为之善恶足以引为鉴戒者编演的历史戏曲,有就习俗之宜改良、道德之宜提倡者编演的社会戏曲,有就古今家庭得失成败最有关系者新编演的家庭戏曲;也有就浅近易解之科学及实业制造之艰苦卓著者编演的科学戏曲,就稗官小说及乡村市井之琐事轶闻含有教育意味者编演的诙谐戏曲。这些剧作家是王伯明(1859-1942)、李桐轩(1860-1932)、孙仁玉(1872-1934)、范紫东(1878-1954)、李博(1879-1969)、李干臣(1881-1952)、李协(1882-1938)、高培支(1882-1960)、吕律(1887-1927)、卢绾青、郝心田、******、赵松岩、封至模(1893-1974)、樊仰山(1909-1985)、王绍猷(1883-1971)、淡栖山(1897-1966)、冯杰三(1901-1973)、谢迈千(1895-1978)、薛寿山、郭道宣、张镇中、李一壶、张守铭等等,他们大都是些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或教师,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和学识水平,他们的加入对秦腔文学的提高与发展,起到了难以估计的作用。特别是李氏三杰(李桐轩、李约祉、李仪祉),八大臣匠中的范紫东、孙仁玉、高培支等都有几十种剧作作品,成为中国近代戏曲文学的典范。这些剧目故事曲折,文采斐然,歌调清新,博得观众喝彩,一个世纪以来盛演不衰。在每一时期又有结合时代要求,表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意识与群众审美心理的代表性的作品。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剧目,多偏重于反帝、反封建和发扬民族精神;五四运动时期的剧目多提倡自由平等与科学、民主;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则显示出高昂的保家卫国、同仇敌忾的精神。他们还编演了大批反映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中国人反帝爱国斗争历史的剧目,其中蕴藏着一种对“历史的艺术反思”。用范紫东的话说,就是“思痛录”,发挥了高台教化、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20世纪40年代诞生于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民众剧团与关中八一剧团,牢牢地把握着此一时期中国民心的向背与人们的殷切期望,创作了许多新秦腔剧目,也使秦腔进一步向百姓生活靠拢。一曲《血泪仇》唱遍神州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肯定地说,这百年间的秦腔剧目,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态与审美情趣上,都同20世纪的风云休戚相关。
(二)表演艺术的圆融与完善,大批表演艺术家的涌现
这场改革还表现在秦腔表演艺术上的圆融与日臻完善,并随之涌现出大量表演名家。
20世纪秦腔的定期会演、调演、献演和各种形式的比赛,极大地推动了秦腔艺术,尤其是表演艺术的日臻完善、精美。前期的西安易俗社和后期的陕西戏曲研究院,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大批表演艺术家得到了观众的好评。须生、青衣、花旦和大净这些真正能体现秦腔汉唐雄风与华夏民族风采的角色行当,人才辈出;须生中的麻子红李云亭、假麻子红郗德育,衰派一绝的刘毓中,须生泰斗张老五(润润子),“活孔明”王文鹏等把须生艺术的苍凉悲壮,气贯河山,发挥得淋漓尽致。青衣中的“秦腔正宗”李正敏和旦色中的何振中、孟遏云、余巧云、郭明霞、萧若兰、萧玉玲、郝彩凤等庄重朴实,在表演中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女性所固有的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秦腔净角中的大净角色,刚强正直,侠义凛然,确实可以体现西北人独有的风神面貌。从清末的雷大坪、四金儿、姜科儿到田德年、****南、安德功、王赖赖、张德明、耿忠义、张健民、李怀坤、周辅国、刘茂森、李可易等演员所扮演的包拯、尉迟敬德、常遇春、姚期、马武、张飞、乔国老、王彦龄、贾似道、黑虎、屠岸贾、晋怀王、殷纣王、闻太师、三教主、艾谦、严嵩、秦桧、钟馗、陆判、曹操、王彦章等,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功架讲究,唱功纯厚,表演尺寸得体,每每获得“活某某”的赞誉。自20世纪初在兰州首次以女性扮演旦角以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旦代替男旦已成一时时尚,大量的女性旦角随之出现。以女性演女性,给人们一种亲切自然的感受。
但与此同时,对旦角形体功的训练也有所放松,艺术上的锤炼也难免不够精纯。尽管真正的“大家”数量不多,但花衫小旦除孟遏云、萧若兰、苏蕊娥、马蓝鱼外,沈爱莲、李爱琴、李爱云、王玉琴、张彩香、王彩霞、马友仙、******、屈效梅、刘棣华、崔惠芳、全巧民、华美丽、宁秀云、李夕岚、段林菊、王麦兰、霍慧君、乔梅英、刘芳玲、张秋惠、李淑芳、张惠霞、孙玉梅、刘茹惠、张咏华、萧玉玲、戴春荣等等仍为秦腔唱念做打表演艺术增色添彩不少。丑行的聂大少、苏牖民、席子才、钟新民、马平民、汤涤俗、晋福长、阎振俗、王辅生、樊新民等的一言一行,都能使观众从他们诙谐幽默的表演中,引发出无尽的联想。总之,随着秦腔艺术的日臻完善,大量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表演大家也随之出现,在20世纪的秦腔天空中,出现了群星璀璨的局面。
(三)音乐的理论性自觉和唱功协律调品
20世纪秦腔音乐理论研究更加自觉、主动,传统音乐记录整理更加系统完整,推动了创腔的日新月异,百花齐放。
20世纪秦腔音乐的推陈出新,鲜明地呈现出三大板块,两条线索。这就是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民间(包括县及县以下)剧团班社的求发展中的出新和西安易俗社与陕甘宁边区秦腔剧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以出新求发展,前者表现为大普及中的缓慢提高;后者呈现出一种提高指导下的难于普及。甘肃省和兰州市的秦腔剧团、西宁市秦腔剧团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秦腔剧团在音乐上也属于前者的范围。一大批新的音乐工作者加入这一行列,自觉地推动了这一推陈出新的进程,也有意无意地散涣了这一进程。
从音乐唱腔和主奏乐器的改革上说,以秦胡代替二股弦是为一个阶段,唱腔音乐的“东西慢板”迅速消失,“二音子”“哎咳”拖腔的淡化和取缔,最为清楚,“叫板”人为的被取消(20世纪50年代以后)让不少人难以接受。这些都可以从白长命→陈雨农→李正敏→萧若兰的秦腔唱腔音乐演化中看得出来。这些变化有两方面的客观原因:一是女性演员迅速增加;一是文武场面乐队众多新乐器加入,从而出现了定调、换调、转调和音域应用方面的出新和唱腔音乐的创新。前者如《江姐》中江雪琴的唱段,《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智取威虎山》中常宝、杨子荣的唱段,《沙家浜》中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的唱段,《游西湖?鬼怨》中李慧娘的唱段,《朝阳沟》中男女声齐唱,《向阳川》中独唱、合唱与齐唱,《祝福》中的序曲和祥林嫂唱段,《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秋菊的唱段;后者如《刘巧儿》中刘巧儿的唱段“自幼儿许配赵家”,《烈火扬州》中的唱段“他”,《罗汉钱》中小飞娥唱段“罗汉钱酸辣苦甜”,《屈原》中婵娟唱段“适才间皮鞭打”,《窦娥冤》中窦娥的唱段“没来由犯王法”,《火焰驹》中黄桂英的唱段,《断桥》中白云仙的唱段,《谢瑶环》中谢瑶环的唱段和《三滴血》《赵氏孤儿》等的主要唱段。在腔格句式、板式运用,腔词结合、旋律加工和戏剧化、人物心理表现方面,都有创新。王依群、孙茂生、姚玲、李正敏、荆生彦、薛增禄、姚井明、王东生、萧炳、赵北海等人,功不可没。
(四)秦腔舞美的声光电色现代化。写意同写实、表情同表意的巧妙结合运用,三维空间的全方位进展
这方面的成就是随着电气化和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而迅速引进秦腔舞台艺术的。初期是零碎的,20世纪50年代后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而且与人物的规定情境、内心活动、舞台装置和效果融为一体,也同整个剧情互为表里。尤其在一些神话色彩浓郁的戏剧和童话剧中更为突出。
(五)秦腔技艺的戏曲化与情节化
有人曾觉得秦腔的技艺,特别是武打戏的“打”是从京戏引进来的。其实,这是只看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上的京剧技艺与武打,尤其是同锣鼓经的巧妙配合,以外形体现内在精神活动方面。历史告诉人们:上述东西都是京剧从秦腔手中学习和继承下来的,只是后来一段时间里秦腔这方面的技艺很少运用罢了。应该说,这些从秦汉百戏发展而成的秦腔技艺,经过一段的丢失和弃之未用后,20世纪50年代后又回了娘家,并把那些在京剧中发展、提高了的技巧也引了进来。诸如蒲剧中的翎子功、帽翅功,京剧中的水袖口、梢子,其他一些兄弟剧种中的“吹火”与烟火等等,也不例外。
上面挂一漏万地写出了20世纪秦腔的历史,着眼于高度综合艺术的五个因素(戏曲文学、戏曲音乐、戏曲表演、戏曲舞美与戏曲技艺)在秦腔艺术中发展的历程,表明它的与时俱进。
今天,人们喋喋不休地谈“世界性”问题,我们认为作为艺术,只要有了浓烈的民族性,也就成了世界性的。这在“振兴秦腔”的大潮中,在电影艺术片、电视艺术的开掘和发展中,无疑会进一步把秦腔推向21世纪信息化高科技的风口浪尖。
历史不会停止,秦腔还要发展,我们寄希望于未来从事秦腔艺术的所有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