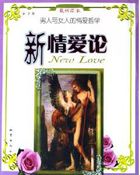治国之道关键是要处理好君臣间的关系,《淮南子》认为君与臣职责不同,君制臣,臣事君,不可相无,二者相辅相成,各得其宜,虽异则宜。并提出“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异道就是各司其职,不越位,不混则有序,从而达到异则一的殊途同归的整体和谐的效果。“不正本而反自然,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认为社会政治中君臣关系间应该遵循自然这一法则。这种自然就是事物的内在规律,不单是单个事物的特性,还包括事物间的本然联系。只有如实地把握这些自然特性,才能以逸待劳,使事物得以顺利地发展。
君制臣、臣事君的上下关系,是由道所决定的:
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故上下异道则治,同道则乱。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苛削伤德。大政不险,故民易道;至治宽裕,故下不相贼;至忠复素,故民无匿情。
从道的角度把道作为治理天下的理论依据,将君主的行为与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警示统治者应慎用权力,不可妄为,反对苛刑暴政。在治理社会的系统中君臣应分工合作、齐心协力,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有序性。在君制臣的前提下,充分调动群臣的才能和积极性,推动社会的正常运行。人主的高明之处在于善用众臣之能,虽不见不知,却能通过他人之知获取对外界的认识。但君制臣要靠人主的清明、虚心,才能调动群臣的积极性,尽其所能,君臣协力才是国家实现治理的基础,而不是仅靠君主的权势。同时认为圣的内涵包括智慧和好问学,这明显的是吸收了儒家的圣人观念。
《淮南子》重视君主的作用,提出尊君,但没有对君主的权力和地位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和论证。“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君主应是人间正义的代表,能“禁暴讨乱”、治理社会。“故义胜君,仁胜父,则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圣人在上,化育如神”,尊君的前提是义胜君,即君主行义则君尊,才能制臣。“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这是道家的君臣观。君主是国家的表率,因此,君主应寡欲无为,不扰民。“相忘”使臣不感到君权的威压,说明君臣间的某种平等性,实际抬高了臣的自主性。“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君主所操之名就是法和礼,以规范臣的行为。达到君制臣的目的。君无为,则臣效力。“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相连之物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并生的,君臣是相互依赖、相互回报的政治利益关系。臣尽忠,君尽赏,才能各得所需。而君之赏与臣之尽死都是有条件的,即君有德,臣有功。
君臣虽异道,但“君臣同志”,即目标一致,才能协同治国。“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死而民弗离,则为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上下利益具有一致性,齐心协力共同治理社会,这是上全之策,并且君应善居臣下,不与臣争功,这样才能消除上下间的冲突与对立,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整体和谐与发展。
要想使人无条件地服从、效法天,就必须在天人之间建立联系。在前面已论述过《淮南子》利用数偶、类推方式论证了天人的同类关系,进而从物类之间的感应推及到以气为中介的天人感应,这样,天人之间便自然地具有了一种相类相感的关系。但它与董仲舒赋予天以伦理的品格并将天神格化论证“天人感应”有极大的不同;另外,对君主主张其地位的长久要建立在行德施政方面,而不是对皇权来源的神圣性的论证。虽然用本末关系说明了二者确定的地位,但强调各尽其道、同志、相报、相忘等相互关系的论证,而不是一味地臣对君的服从上。实际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行为,这是《淮南子》未能被试图集权于一身的汉武帝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
《春秋繁露》认为人世间的统治权来源于天,从而为君主的统治获得了合法性和至上性。董仲舒对天的尊崇实际是要建立人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帝王既然是天之子,那么其权力的天赋性和至尊的权威性在人间应有体现,应当是完美的道德化身,是世人敬仰效法的楷模,且君主治理不善无须人们起而反抗,自有天的适时惩罚,而只有天具有这种权力,皇权是由天操控的。因此君主的立与废由天而定,由此君主只听从天、只对天负责,从而抽掉了人们反抗君主的基础与依据。人世间君主权力的至上性和权位的不可动摇性,使得只有宇宙的最高权威才能对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施予奖惩,因此百姓是被动无权的,对其现实不公平的命运不能作出任何反抗,一切都由天做主。而天地万物间的统治力量是神格化的天,这就为其后的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依据。天象的任何变动都是上天的启示,因此当时天文学的发达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观测天象是最重要的一项科学兼政治的活动,这样就使天文观测具有了深刻的政治目的。这既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同时又左右着天文观察的实际效果。天国与人间对照,认为天子应像天管理自然与社会一样,不见其行为,而万物都由其决定,即“无为而治”,天子代为其治理,天子应将具体事物的处理交于大臣。
在历史上,对理想君主的讨论是思想家探讨的一个中心内容,这实际是对人类社会理想秩序如何管理的问题,各个学派都有不同的设想。道家是以无为与有为展开的,无为指行为的客观性,就行事的依据、原则而言,因此,无为之治是道在社会领域中的表现。有为是就济世利民的实际功效而言,圣人是将二者统一起来,表现为君制臣,君无为而臣有为。《淮南子》将无为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之中,更具有了新鲜的生命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