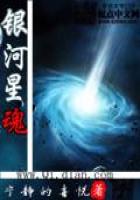林语堂对中庸、闲适、充满生命强力的北京文化的赞叹与推崇,体现出明显的审美现代性倾向。林语堂曾经两度在北京生活,即大学毕业后在清华任教的三年(1916-1919)和留学归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三年(1923-1926)。林语堂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少于上海(1927-1936)和美国(1919-1923,1936-1966),但是他却对北京文化情有独钟。他不仅有专门探讨北京文化的专著《辉煌的北京》,而且还有以北京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散文及随笔。散文与随笔数量较多,小说虽然并不是很多,但份量极重,一部《京华烟云》堪称经典,《风声鹤唳》和《红牡丹》对北京也有所涉及,并传达出作者的文化选择与感情倾向。这些作品大都是林语堂移居海外后所作。客居西方发达国家的林语堂,看到了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及感性生命受到压抑乃至窒息的状况,他断言:“今日世界之瓦解,可以证明是由于科学的物质主义侵入人文学思想的直接结果。”170在他看来,在“科学权力”的笼罩下,人文精神日益衰落,审美精神逐渐式微,现代社会虽然有着发达的物质文明,但物质文明并不能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特别是精神上的隔膜状态。就像《奇岛》中劳思所说,现代人“喜欢活在冷冰冰、赤裸裸的现实里,宁可剥去一切色彩和感情。”171正是出于对西方高度发达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的检讨,林语堂试图以温情闲逸又生机勃勃的北京文化建构一种理想的文化精神,以拯救物质主义对人类的漠视和戕害。北京文化滋养着林语堂的人生及其文学创作,他肯定北京文化的优秀部分,赞美并张扬北京文化的生命力,以此表达他对中西方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病的忧虑,同时进行揭露和诊治,体现出审美现代性倾向。从这个角度切入林语堂研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上海给林语堂提供了舒适的物质生活,而他却对北京文化情有独钟。
中庸理想
北京是一座中庸的城市,“近情”的城市,也是林语堂最喜爱的城市。他说,“这种极难诉诸文字的精神正是老北京的精神。”172实际上,他所说的难以诉诸文字的精神就是中庸精神。从城市生活方面讲,中庸式的生活应当“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173;而北京则具有“一种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理想”:“不必大富大贵,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当然也不能缺衣少食,忍饥挨冻”174,并且,“这种中等阶级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175北京的情感是“亦庄亦谐”的,居室是“差强人意”的,理想是远大的但又“不受它的羁绊”176,一切都因为“酌乎其中”,所以能够“有条不紊”177.他把同为中国都市之代表的上海称为暴发户,因为上海缺少这种中庸精神而“唯洋是从”,因此他得出“上海可怕”178的结论。“北京的自然环境、艺术与人们的生活协调地结合在一起”179;而上海等商业城市则“充满了斤斤计较的,赚钱狂似的商贩们的喧嚣与粗俗”180,也正因此,林语堂极力诅咒集中西陋俗于一体的商业大都会上海:
我想到你的浮华、平庸、浇漓、浅薄——想到你断伤了枝叶的花树,与断伤了天性的人类;也想到你失了丈夫气的丈夫与失了天然美的女子;
我想到你失了忠厚的平民与失了书香的学子;也想到你失了言权的报章与失了民性的民族;
我想到你的豪奢与你的贫乏——你巍立江边的崇楼大厦与贫民窟中的茅屋草棚;也想到你坐汽车的大贾与捡垃圾桶的瘪三;
我想到你的淫靡与你的颓丧——你灯红酒绿的书寓与士女杂处的舞场;
……
你这伟大玄妙的大城,东西浊流的总汇。你这中国最安全的乐土,连你的乞丐都不老实。
我歌颂你的浮华、愚陋、凡俗与平庸。
不知道是北京文化的中庸促成了林语堂的文化选择,还是林语堂的文化观使他选择了中庸的北京,总之林语堂与北京是和谐地融为一体了。
北京能够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找到平衡——既是发达的都市,又具有乡村田园格调,这恰好符合林语堂的中庸理想。北京是具乡土田园风格的礼俗社会,如师陀所说,故都北京是“半农村性质、令人难忘的老城”182.在林语堂眼中,“北京的魅力不仅体现于金碧辉煌的皇朝宫殿,还体现于宁静得有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乡村田园景象。就是从这样的城市中,人们既为它的艺术格调,建筑风格和节日风采而兴奋不已,同时也会享受到一种宁静的乡村生活。”183北京“代表着古老中国的灵魂,代表着文化和温和,代表着优良的人生和生活,代表着一种人生的调协,使文化的最高享受能够跟农村生活的最高美点完全和谐。”184“北京城宽展开阔,给人一种居住乡间的错觉,特别是在那秀木繁荫的庭院,在那鸟雀啾啾的清晨,这种感觉更加强烈。”185当他想到北京,“所有西方文明的记忆都似乎从脑海中消失了”186.在《红牡丹》中,牡丹经过不断的爱的选择,最后爱上了北京西郊的农民傅南涛,在他的住处,“嘎嘎乱叫的鹅鸭各处乱跑,几只黑羊正在篱笆下吃草,用长绳子拴在一根桩子上,这样就不致于吃菜园的青菜。”“房子是普通农家的房子,一间耳房敞开,是储存干草柴火的地方,已经多年没有粉刷。由于日晒雨打,没经油漆的木头部分,已经成为干枯的灰棕色。”187然而这一切,无不令牡丹高兴。林语堂笔下“红日西斜,归鸦阵阵,于我左侧绕树而飞,西天云霞红紫斗艳”188的乡间景致与工业文明的都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摩天大厦,和夜间成排透露灯光的窗户之外,还有什么可以使人欣赏的东西呢?”189乡村格调、田园特性是北京的独特魅力所在。
面对日益发展膨胀的都市,林语堂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心目中的理想都市并不是高楼大厦林立、充满工商业喧嚣的都市,也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极度膨胀的那种城市,而是具有双重性。就是说,既有“城市的舒适”,又有“乡村的静寂”。而北京正是理想代表,所以林语堂选择田园都市北京寄寓自己的文化理想。“北京是一个理想的城市,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有呼吸的空间,在那里乡村的静寂跟城市的舒适配合着,在那里,街道衢巷以及运河是那样地分布,使一个人能够有空地一块做果园或花圃,而且早晨起来摘菜时可以见到西山的景色——可是距离不远却是一家大的百货商店。”190在北京,“城市生活极高度之舒适与园林生活之美,融合为一体,保存而未失,犹如在有理想的城市,头脑思想得到刺激,心灵情绪得到宁静。”191林语堂厌恶并批判在纯粹现代工商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市,认为它们背离大自然并缺乏文化感,如他对上海的批判;但他也不赞成远离都市做陶渊明式的完全归隐,而是主张做城市隐士,他说:“如果一个人离开城市,到山中去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他也不过是第二流隐士,还是环境的奴隶。‘城中隐士实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力,不受环境的支配。”192“大荒旅行者与深林遁世者不同。遁世实在太清高了,其文逸,其诗仙,含有不吃人间烟火意味,而我尚未能。”193林语堂喜爱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都市。就是说,他希望将传统社会与现代都市融合,互为取长补短,从而为人类创造更合理的生存环境。林语堂将目光转向北京而不是商业都市上海或纯然的乡村,说明他并没有选择纯粹的都市文化或乡土文化,而是都市与乡土的融合。
北京这种中庸精神的获得是由于北京文化的兼容并包: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头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娱乐,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并列,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和尚、道士、太监,都来承受老北京的阳光,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在老北京,生活的欢乐依然继续不断。194
强大的融合力使北京文化能够容纳不同的文化景观与思想,从而具有宁静的田园都市景象,和谐的生活格调。因此,林语堂在作品中总是极力渲染北京的城市生活,把它作为人类理想生活之一种。在这里,没有必要追问,“古代社会真有那么美好吗”,或者“乡土社会真有那么美好吗”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关键是,它把一个自然健康的非人为分裂的世界凸显在了现代人的面前,人的感性在那个世界里,不仅没有受到压抑,而且以解放的方式成为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
闲适格调
林语堂反对“速度”,提倡闲适从容的生活方式。在谈到城市的魅力时林语堂特别提到北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他说,“使北京这样可爱的还有它的生活方式。它是那样地使一个人能够获得和平与安静”195,在这里,“你是自由的,自由地去从事你的学业,你的娱乐,你的癖好,或是你的赌博和你的政治活动。”196他曾感叹:“目前商业生活的速度太高了。”197而这种“完全不对”的速度,破坏了社会“悠闲的精神”198.与许多城市被时间追着跑、甚至人成为时间的奴隶的现代社会不同,北京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就如同老人的悠闲散步。“北京的生活节奏总是不紧不慢,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比较简单。”199因此,林语堂借助于北京文化,寻找从容闲适的生活节奏。
从容闲适的生活方式使北京人能够充分享受生活之乐。林语堂认为西方人虽然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却不懂得如何去享受它,只有中国人才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这在北京人的生活中有集中体现。在北京,这种享受生活的悠闲格调具体表现为空间的宽阔与时间的闲适。比如他对生活空间的描写,在北京,“每一个人家都有一个院落,每一个院落中都有一缸金鱼和一棵石榴树,在那里菜蔬都是新鲜的,而且梨子是真正的梨子,柿子也是真正的柿子。”200在院子里,可以种树、养花、养鸟、养鱼,还可以种菜。他又这样描绘北京雍容的时间感受:“正像逛庙会,人们从中体味到一种宁静悠闲的气氛。悠闲,一种对过去的认识,对历史的评价,一种时间飞逝的感觉和对生活的超然看法油然而生。中国文学、艺术的精华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不是自然状态下的现实存在,而是一种人们头脑中幻化出的生活,它使现实的生活带上了一种梦幻般的性质。”201这种人生境界能够避免人的异化,从而使人们充分享受生活的真实情境,感受人生的恒定性。这种宽阔的生活空间和闲适的时间感受在过于追求物质利益的城市是无法想像的。比如在上海,“我常看见上海的富翁,占着小小的一方地皮,中间有个一丈见方的小池,旁边有一座蚂蚁费三分钟即能够爬到顶上的假山,便自以为妙不可言”202.狭窄逼仄、千篇一律的居住空间中的人们,是无暇享受人生的。就像《奇岛》中的劳思所说:“美国办公室和商行都不停下来吃午餐,只花半小时坐在汽水自动贩卖机前的高凳上,匆匆啃完三明治,又回去工作了。工作!工作神圣!……一只狗抢到一块肉,还会叼到角落里,舒舒服服吃一顿。……一顿慢慢吃的午餐,就可能表示你被解雇了,或在办公室不受重视,或不被需要,你的时间算不了什么。原来如此。不,休息和安歇在美国‘爱身’中毫无分量。”203人“发明省力的机器后,反而比以前更辛苦了。进步的步伐太快,他陷入迷宫里,找不到出路。奇怪的是,大家仍然对懒惰皱眉头,享受悠闲是丢脸事儿,什么也不做是一种罪孽。……人对自己太残酷了。他不再驱赶驴子和马匹,却开始驱赶自己。”204在“人对自己太残酷”的感叹中,林语堂格外推崇北京的生活节奏。如《京华烟云》中的姚思安,淡泊名利,胸襟开阔,沉潜黄老之修,把家政交给妻子,把店铺托付给亲戚,只和书籍、古玩、儿女朝夕相处;他出巨资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支持抗日战争,却从不涉足仕途;在晚年他一心研读道家典籍,静坐修炼,最后云游名山古刹十年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无疾而终,一生崇尚自然,追求人情诗趣。其他如姚木兰,《风声鹤唳》中的老彭、梅玲等,他们蔑视世俗礼教,亲自然,张自我,不为物拘,不为物累,闲适从容,达到了内心和谐宁静、恬淡自适的人生境界。
原始生命强力崇拜
林语堂喜爱北京人的生命强力,通过北京人表现他面对社会的进步与人情的淡化所作出的反向思考。他喜爱北京人的种性,认为北京人是强壮的、自然纯朴的,在他们身上透出勃勃的生命力,这是南方人种尤其是上海人种不可比拟的。他说:“我是东南沿海的福建人,但我对江南地区那种柔弱懒散的人们没有多大的好感,虽然他们的文化更为发达一些。对气质纯正的北方人,我却充满了由衷的倾慕。……北方的文化虽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北方人基本上还是大地的儿女,强悍,豪爽,没受多大的腐蚀。”205相比较而言,南方人尤其上海人则显得油腔滑调,柔弱懒散,并且“略带女人气”206.
林语堂在小说中通过北京人表现出对原始生命强力的向往与热爱,发掘出埋藏在现代社会的人情美与人性美,从而塑造出他那个参照系中的理想人格。在《红牡丹》中这一主题表现得尤其明显。南方人金竹、孟嘉、安德年虽然都曾得到了牡丹的爱,但最终牡丹却属于北京的傅南涛,因为在傅南涛这里,她感受到了生命强力的释放。在这里可以将牡丹最终的选择——北京西郊农民傅南涛与牡丹来自南方的情人梁孟嘉作一个对比。北京人傅南涛以拳术家的身份出场,他有雄伟健壮的躯体,还有几分“粗野”,他可以为牡丹一句戏言而毫不犹豫地跳入水沟,能够直率地向牡丹表达自己强烈的爱慕,体现出自然淳朴、未受矫揉造作的现代文明侵蚀的本真状态下的生命强力。而梁孟嘉则是一个斯文的读书人,“是个文质彬彬非礼勿动的正人君子”207,当他得知牡丹结识傅南涛后,没有“热情像疯狂一般”,而只是斯文地说“了解”,“就这样好了”。牡丹说:“他这样斯文,倒使我失望。我原不应当如此,但是我想我是对他失望了。他耐性极好,极其聪明,什么都懂,这样就在我热烈的爱火上泼了一盆冷水,把我的爱火浇灭了。”208“在爱情上谁要什么理性智慧?所要的是火般的热情和坚强的肌肉”。对牡丹来说,“她宁愿和一个平凡的打把式卖艺的同房,而不愿意和一个满腹经纶的翰林同房。”209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牡丹选择傅南涛、离开梁孟嘉的真实心理。正如杜布费所言:“从个人角度说,我相信原始人的许多价值观;我的意思是:直觉,激情,情感,迷狂和疯狂。”210在对原始野性的赞美和颂扬上,林语堂与杜布费是一致的。只不过,林语堂通过北京人寄寓了这一文化思考。
林语堂对原始生命强力的崇拜,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否定。“对(人的)社会秩序与自然(包括自然人)之关系的新的理解,表现在理智(reason)与激情(passion)的著名对立中。激情愈来愈被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211.理智与激情的二分,实际上暗含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西方,自从卢梭大声疾呼以回到原始、回到野蛮、回归自然与文明社会抗衡之后,众多的作家、诗人,都对原始野性的世界表现出一往深情:梅里美、雨果在吉卜赛人那里发现了人的自然情感;戴·劳伦斯在查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间维护人性;杰克·伦敦让一只过度文明化的狗重新复苏野性,奔向冰天雪地的原始荒野;还有高更、尼采、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等人也曾竭尽全力,为人的自然本能辩解,为人的生命强力呐喊,赞美激情,张扬在人为的社会及法律中所没有的“一切‘野性的’东西”212,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少数作家能够在面对文明进步与生命力退化的二律背反现象时,作出与世界艺术家一致的审美选择与价值判断,以生命的强力来抗衡由“文明”带来的对人性的戕害和扭曲,比如林语堂、沈从文等。对原始生命强力的歌颂是东西方作家的共同选择,由此使林语堂具有了世界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