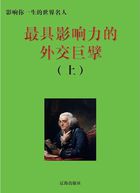非洲人不能投票,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不关心谁赢得了选举。在1948年的白人大选中,执政的合众党在珍纳罗尔·斯马茨的领导下反对复兴的国民党。当时,合众党正处于国际威望鼎盛时期。在斯马茨使南非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阵营的同时,国民党拒绝支持英国而公开同情纳粹德国。国民党的竞选运动以“黑人危险”为中心,在竞选中打出了两个口号:“黑人们留下”、“苦力们滚出这个国家”。苦力是南非白人对印度人的贬称。
在荷兰归正会的前牧师、一家报社的编辑丹尼尔·马伦的领导下,国民党是一个受仇恨驱使的党派。他们对英国人充满着仇恨,英国人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当作次等人;他们对非洲人也充满着仇恨,国民党人认为黑人是对南非白人文化的繁荣和纯度的威胁。非洲人只是对珍纳罗尔·斯马茨不忠,而我们则不仅仅是对国民党不忠。
马伦的理论平台就是种族隔离。种族隔离是新术语、旧思想。其字面的意思是“隔开”,它代表的是一种压迫制度下的所有法律、法规的总和,这些法律和法规使非洲人在地位上低于白人达几个世纪。这种或多或少的非法现实无情地被合法化。在过去300年中,偶然的隔离常常被巩固成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其行政手段是残忍的,行政范围是无所不包的,行政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种族隔离的前提是白人比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优越,其作用就是永远维护白人的霸权地位。正如国民党人所指出的那样:“白人必须始终保留其上司地位。”他们的理论平台是建立在“白人至高无上”这一基础之上的,“白人至高无上”的含蓄意思就是在各个领域内保持白人的绝对统治。这个理论得到了荷兰归正会的支持。荷兰归正会用宗教理论为种族隔离提供依据。这种宗教理论暗示南非白人是上帝选择的人,黑人是南非白人的附属。按照南非白人的世界观,种族隔离和教会两大武器要同时并举。
国民党的胜利起源于南非白人统治被英国人推翻。英语作为一种官方语言仅次于南非荷兰语。国民党的口号包藏了他们的使命:“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自己的土地。”按照南非白人扭曲的宇宙理论,国民党的胜利就像以色列人到“应许之地”一样。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南非应该永远是白人的国家。
这次胜利也是一种震惊。合众党和珍纳罗尔·斯马茨打败了纳粹,他们也一定能击败国民党。在大选的那天,我与奥利佛·塔博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了一个选举大会。我们仅仅是探讨国民党人政府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喜欢有这个政府。选举进行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卖报的售货亭正在出售《兰德每日邮报》:国民党人胜利了。我感到吃惊和失望,而奥利佛则说了一句更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喜欢这个结果。”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解释说:“现在我们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将采取什么立场。”
就连珍纳罗尔·斯马茨也认识到了这种理论的危险,他把“种族隔离”谴责为“狂热的概念”,是由于偏见和恐惧而产生的理论。自从国民党人选举的那一时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土地从今以后将成为紧张和冲突的战场。在南非历史上,唯我独尊的南非白人政党第一次把持了南非政府。马伦在他大选胜利后演讲时宣布:“南非属于我们了。”
同一年,青年团在穆达起草的、执行委员会公布的文件中阐述了自己的方针,这就是号召一切爱国青年推翻白人独裁统治。我们反对南非共产党人关于非洲人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受压迫而不是作为一个种族受压迫的见解,并且指出,我们必须在非洲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由非洲人自己领导发动一个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提倡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废除禁止非洲人从事技术工作的种族歧视法律,要求实行自由义务教育。该文件也重点批评了更极端的马库斯·加伟主张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青年团的民族主义两大理论之间相互拆台的做法。后者承认南非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我赞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极端革命倾向。我对白人不满,而不是对种族歧视不满。虽然我不准备把白人赶进大海,但是如果他们爬上他们的轮船自愿地离开这个大陆,我将十分高兴。
青年团或多或少地对印度人和有色人更友好一些,与非洲人一样,把印度人也说成是被压迫的人民。但是,印度人有自己可以依靠的祖国——印度。有色人也是被压迫人民,但是他们不像印度人,他们除了非洲之外并没有自己的祖国。
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方针政策,我愿意接受印度人和有色人。但是,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不相同的,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够真的投入到我们的事业中来。
马伦立即开始实行他的恶毒纲领。上台几周内,国民党政府就赦免了战时的叛徒罗贝·雷布朗特——他曾经组织叛乱,支持纳粹德国。国民党政府企图限制商会运动,废除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有限的权利。《选民分离代表法》最终剥夺了有色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权。《禁止通婚法》于1949年出台,随后紧接着又出台了《不道德行为法》,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性关系非法化。《人口登记法》把南非人按种族加注标签,使肤色成了个人最重要的仲裁条件。马伦出台了《社团区域法》,并把这个法描述成“种族隔离的核心”,要求为每个种族社团划分居住区。过去,白人依靠武力夺取土地,现在他们又通过立法把掠夺的土地合法化。面对来自政府的这种新的强大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走上不平常的历史性道路。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努力,把自身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青年团起草了行动纲领,纲领的核心就是发动群众运动。
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该组织采纳了青年团的行动纲领,号召举行联合抵制、罢工、被动抵抗、抗议示威及其他形式的群众行动。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过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策略一直是把其活动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青年团团员早就看到了采取合法的手段打击种族压迫的失败。现在,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开始迈出了更积极的一步。
如果没有内部的剧烈变动,这些变化是不会发生的。在召开年会的前几周,瓦尔特·西苏陆、奥利佛·塔博和我在索菲亚顿埃克苏玛医生的家里私下会见了埃克苏玛。我们向他说明,按照甘地在印度发动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和1946年开展的被动抵抗运动,我们认为采取群众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压迫面前太软弱。我们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终究要准备冲破法律的束缚,并且如果有必要则愿意像甘地那样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坐牢。
埃克苏玛坚决反对,声称这种策略是不成熟的,只能让政府抓住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借口。他说,这种形式的抗议,最终必然会在南非发生,但是,在眼下这个时刻迈出这一步是致命的。他明确表态,他是一个远近闻名且事业有成的医生,他不会去坐牢,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我们向埃克苏玛摊了牌:如果他支持我们建议的行动纲领,我们将在下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选举中支持他;如果他不支持我们的纲领,我们就不会支持他。埃克苏玛生气了,骂我们是敲诈,断然拒绝我们为他投票的条件。他说我们年轻气盛,不尊重他。我们规劝他,但是没起作用,他没有支持我们的建议。
深夜11点,他不礼貌地把我们从他家中轰出门外,然后立即关上了门。索菲亚顿没有路灯,那天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并且所有的公共交通早就停止运行,而我们则住在几英里外的奥兰多。奥利佛说,埃克苏玛至少应该为我们提供交通工具。瓦尔特在附近有个朋友,我们说服他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宿。
在12月份召开的大会上,青年团团员都知道不投埃克苏玛的票。因为有两个候选人,我们准备选J.S.莫罗卡为主席。他本来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Z.K.马修斯才是我们想选的人,但是,马修斯认为我们太激进,我们的行动计划太不可行。他称我们是幼稚的狂热分子,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成熟起来。
莫罗卡先生是一位希望不大的候选人。他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当时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组织。当他同意反对埃克苏玛的时候,青年团把他作为会员吸收进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时,他坚持把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全非洲的“国务院”。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不太了解,也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活动家,但是他尊重别人,支持我们的纲领。和埃克苏玛一样,他也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南非很富有的黑人。他在爱丁堡和维也纳上过学,而他的老爷爷曾经是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19世纪,他老爷爷曾经张开双臂欢迎南非白人,并且向南非白人赠送土地,后来却被出卖了。埃克苏玛被击败了,莫罗卡医生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奥利佛·塔博当选为全国执行主席。
在这次年会上行动纲领获得通过,它号召通过联合抵制,即罢工、不服从政府和不与政府合作,去争取政治权利。另外,大会还号召国庆节停止工作,抗议政府的种族歧视和反动政策。这是一种脱离单纯地依靠温和抗议的腾飞,许多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坚定分子在这个富有更伟大的战斗精神的新时代变得大为逊色。如今,青年团团员登上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舞台。我们正在引导非洲人国民大会走上更积极、更革命的道路。
我只能在远处庆祝青年团的胜利,因为我不能出席大会。当时我正在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上司不准我请两天假去布隆方丹参加会议。这家律师事务所虽然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律师事务所,但是,要求我忘记政治,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如果我去参加会,我将丢掉工作,我经不起这个损失。
群众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涨,但是我却对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采取的任何行动仍然抱有怀疑。1950年3月,由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扞卫自由演讲大会”吸引了上万人集中在约翰内斯堡的贸易广场上。莫罗卡医生没经过咨询执行主席,就主持了“扞卫自由演讲大会”,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但是,我仍然对此保持警惕,因为其背后的发起者是共产党。
在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鼓动下,大会通过了举行一天总罢工的决议,这一天是5月1日,被称作自由日。这次罢工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及所有种族歧视性法律。尽管我支持这些目标,但是,我认为共产党人企图抢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抗议日的胜利果实。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首先发动这次运动,所以我反对五一大罢工,并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搞自己的运动。
阿迈德·卡特拉达当时只有21岁,和其他青年一样,他极力为准备大干而小试身手。他是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一名骨干。他听说我对五一大罢工持反对态度。一天,当我走在总督大街上的时候,碰见了卡特拉达。他很生我的气,指责我和青年团不想同印度人或有色人合作。他用挑战性的口吻说:“你是非洲人的一个领导,我是一个印度青年,但是我相信非洲群众是支持五一大罢工的。我向你提出挑战。你可以指定在任何一个非洲人居住的城镇召开一次会议,我保证那里的人民将会支持我。”这纯粹是一种恐吓,但也使我感到很气愤。我甚至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共产党三方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并准备在会上提出申诉,但是伊斯梅尔·弥尔劝我冷静下来。他说:“纳尔逊,他年轻,头脑发热,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最后,我对我的这一行动感觉有点厌倦,并撤回了申诉。尽管我与卡特拉达有分歧,但是我佩服他的激情,我们之间出现的小插曲仅仅是个偶然事件。
运动在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支持下提前进行。正如预料的那样,政府禁止5月1日这天召开任何会议和集会。这一天,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洲人都在家中静坐。当天夜晚,尽管政府禁止集会,但是群众仍然在奥兰多聚集。当时,瓦尔特和我就在奥兰多西区自由日群众集会的外围。天上的月亮皎洁而明亮,当我们看着整齐的抗议队伍游行的时候,我们发现500码以外的小河对面有一伙警察正在集中。他们一定也看见了我们,因为他们忽然向我们这个方向开枪。我们假装被击倒在地上,看着警察冲向人群用警棍击打群众。我们躲进附近的一个护士宿舍里,在那里听见子弹射入墙中的声音。在这次不加区别的、无缘无故的袭击中,有18名非洲人被打死,另有许多非洲人被打伤。
尽管这次暴行遭到了抗议和谴责,但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是保持克制。几周后,政府出台了臭名昭着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个法律宣布南非共产党是非法的,使参加共产党成了犯罪,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这个法律的打击面太大,它把一切仅仅是最温和地向政府提出的抗议也列为违法,把犯罪范围扩大到在工会内进行任何引起“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骚乱或混乱”的理论宣传。这个法律基本上允许政府随意把任何一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禁止任何个人反对政府的政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新对策。除了其他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外,达杜医生也讲了话,他说,允许过去的分歧阻碍联合阵线反抗政府是愚蠢的。我发言支持他的观点:显然,对任何一个自由团体的镇压都是对所有自由团体的镇压。在这次会上,奥利佛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今天镇压的是共产党,明天将会是我们的商会、我们的南非印度人大会、我们的人民组织和我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在1950年月26日举行国庆节抗议活动,抗议政府5月1日杀害18名非洲人和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这项建议获得了批准,在准备国庆节抗议日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密切了与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共产党的关系。我相信,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可以使我们与我们的印度盟友和共产党盟友携起手来。
是年,我被较早地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接替了埃克苏玛医生的位置。埃克苏玛在落选后辞掉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职务。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我10年前来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是埃克苏玛医生设法为我安排了第一份工作,当时我还没有介入政治的想法。现在,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资历最深的人一道工作。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已经由一个“牛虻”变成了一个我一直反对的实权人物。这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感觉,让我百感交集。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更容易一些,因为他没有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必须权衡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而且还要预料到来自像我自己这样的反对者的批评。
群众运动在南非是危险的。在这里,非洲人举行罢工是犯罪,言论自由和运动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举行罢工,一个非洲人不但要承担丢掉工作的危险,而且还要承担丢掉他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危险,甚至还会丢掉他在本地居住的权利。
根据我的经验,政治性罢工要比经济性罢工更危险。因为出于政治上的不满而举行的罢工与因为一个明确的,诸如要求提高工资或减少劳动时间而举行的罢工相比,是一种更危险的活动,需要特别有效的组织。国庆抗议日正是一次政治性罢工,而不是一次经济性罢工。
在酝酿6月26日大罢工中,瓦尔特走遍了全国,征求各地领导人的意见。在他外出期间,我主持繁忙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这里是组织这次全国性大罢工的指挥中心。每天,各种各样的领导人都到该办公室了解按计划准备这次罢工的进展情况。他们有:达杜医生、迪利扎·穆吉、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J.B.马科斯、玉苏福·凯查利亚和他的弟弟毛尔伟、行动委员会书记高尔·瑞德贝、迈克尔·哈迈尔、皮特·拉宝罗克、库恩撒托·英特拉纳。
我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行动,与各地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我们一点闲空都没有,匆匆忙忙地做着各种谋划。
国庆抗议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尝试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政治性大罢工,也是一次恰到好处的、成功的大罢工。在城市里,多数工人都待在家里,黑人经营的商店和公司都关门停止营业。在贝索尔,后来成为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格特·西班德领导了5000人的游行队伍,这次活动成为全国各大报纸的重要新闻。国庆抗议日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给马伦政府传递了一个警示:我们不会在种族隔离面前一直保持被动。因此,7月日成为自由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解放运动中,它被看作自由日。
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我感觉到一种由于计划周密而取得对敌斗争胜利迸发出来的兴奋感和与可怕的敌人斗争中产生的同志情谊。
我正在学习的斗争是非常耗费精力的。如果一个人投身于斗争中,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家庭生活的人。在准备国庆抗议日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马卡托·莱瓦尼卡出生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正陪着艾韦琳住在医院里。但是,这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日常休息时间。他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自年到1924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二任主席的赛法库·马宝高·马卡托中的马卡托,一个是赞比亚主席莱瓦尼卡。马卡托是一个佩迪酋长的儿子,他曾经带领志愿者反对不允许非洲人在比勒陀利亚人行道上行走的种族歧视性法令,他的名字对我来说是胆识和勇气的象征。
在国庆抗议日的准备期间,有一天我太太告诉我,我当时只有5岁的大儿子泰姆比问她:“我父亲住在哪里?”我一直是深夜他已入睡的时候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他还没醒我就早早地离开了家。我不想离开我的孩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十分想念他们,不知不觉我竟然几十天没和他们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
我长期坚持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发生了动摇。共产党的总书记、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摩西·考塔尼经常深夜来我家,我们常常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考塔尼头脑清醒、自学成才,是德兰士瓦省一位农民的儿子。他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反对我们?我们都反对同样的敌人,我们不想独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权力,我们也是为非洲民族主义而工作。”最后,我无法找到理由反驳他的观点。
因为我与考塔尼、伊斯梅尔·弥尔和鲁思·弗斯特之间的友情和我对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观察,我越来越难找到对共产党抱有偏见的正当理由。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像J.B.马科斯、埃德温·莫福参亚纳、旦·图鲁麦和大卫·博帕佩这样的共产党人比别人更埋头苦干、努力工作,他们作为伟大的自由战士是无懈可击的。达杜医生,1946年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一位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一个争取人权的战士而起到的作用使他成为各个团体组织的英雄。我不能再怀疑这些人的诚意。
即使我不再怀疑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我仍然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哲学和实践角度提出问题。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又知之甚少。在与我的共产主义朋友开展的政治讨论中,我常常由于对他们的理论的无知而陷入尴尬的境地。我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我找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全套着作,探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我没有时间认真研究这些着作。虽然我对《共产党宣言》产生了兴趣,但是研读《资本论》却让我疲惫不堪。不过,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认为,这种思想与非洲传统思想很相似。在非洲传统思想中,生活是共同享受的,财产是共有的。我赞成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它既简单明了又慷慨无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辩证唯物主义似乎既是驱赶种族压迫黑暗的明灯,又是用来结束种族压迫的工具。我认识到要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通过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形势。因为,如果我们的斗争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超越黑人和白人的概念。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总是倾向于相信我能证实的东西。我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很有道理。商品价值是由进入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这个思想特别适合南非。统治阶级支付给非洲劳工仅供生存的工资,然后在商品成本中增加价值,这种增加的价值被他们自己留下了。
马克思主义号召采取革命行动像音乐一样响彻自由战士的耳旁。他关于通过斗争取得历史进步和革命飞跃中发生变化的思想同样富有感染力。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着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一个政治家解决面临的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苏联特别支持许多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就是我为什么改变对共产党人的看法、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欢迎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其组织的立场的另一个原因。
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能在坚持非洲民族主义的同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我来说,这并不矛盾。我首先是一个为我们从少数统治者那里解放出来而战、为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战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但同时,南非和非洲大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问题除了鲜明性和特殊性之外并不是独有的问题。因此,一个把问题置于世界范围和历史过程之内进行研究的思想是有价值的。我愿意使用一切必要的方式、方法加速清除人类偏见,加速结束沙文主义的、暴力的民族主义。我不必要为了同他们一道工作而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发现,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非洲共产主义者应当更多地加强团结,而不是加深分裂。悲观主义者总是说共产主义者正在利用我们,但是又有谁说我们不是在利用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