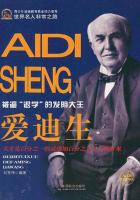当我们到达克朗金矿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黎明。克朗金矿位于寂静、昏暗的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大山丘平原上。约翰内斯堡是由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金矿于1886年建立起来的一座黄金城市,而克朗金矿则是这座黄金城市中最大的金矿。我本想能在这里看见像乌姆塔塔市内的政府大厦那样的大楼,但克朗金矿的办公室却原来是建在金矿前面的锈迹斑斑的铁皮房子。
金矿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光秃秃、坑坑洼洼,到处是污泥垢土,但就是没有树,四周围着篱笆墙。金矿就像是经过战争破坏过的战场,到处是刺耳的噪音:有轴式卷扬机的摩擦声,有电钻的冲击声,有发电机的轰鸣声,有下达命令的吼叫声。所见之处,到处是身穿工作服、看上去疲惫不堪、压弯了腰的黑人。
他们住的是凄凉阴冷、性别单一的简陋房,房子里有几百个水泥床,彼此相隔只有几英寸。
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采金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矿石的含金量低、矿井深。
只有成千上万的黑人,工作时间长、收入低、无人权可言的廉价劳力的存在,才能使白人拥有的、建筑于黑人脊背之上、超过十字军东征之梦的、暴富起来的黄金公司有利可图。以前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企业、这样大的机器、这样得法的组织、这样辛苦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南非的资本主义。我知道,我即将接受一种全新的教育。
我们直接去找工头。皮利索是一个粗暴的老工头,依靠他的冷酷无情谋生。
他知道佳士提斯,因为摄政王几个月前曾写过一封信,要求为他安排一个管理工作。这种工作在金矿上是最令人羡慕、最令人尊重的工作。但是,他不了解我。
佳士提斯解释说,我是他的弟弟。
“我只接受佳士提斯,”皮利索回答说,“你父亲的信没有提你弟弟的事。”他十分怀疑地看着我。但佳士提斯请求说,那仅仅是个疏忽,摄政王对我的事也发过信。皮利索那无情的外表之下也隐藏着有同情心的一面,于是,他让我担任金矿上的保安,并说,如果干得好,三个月后将给我安排一份管理工作。
摄政王的话在克朗金矿很有分量。在南非,所有的酋长都是如此。采矿官员都想从农村招募劳工,各个酋长对他们所需要的人都有控制权。他们需要酋长们鼓励自己的老百姓来矿脉做苦工。酋长的待遇与普通人大不相同。当他们来金矿参观时,矿主总是提供特别优厚的吃住条件。酋长的一封信足以使一个人得到一份好工作。由于我们的关系,佳士提斯和我被给予特别照顾。我们工作没有定额,我们被安排了较好的睡觉的地方,并且有少量的工资。第一天晚上,我们没有住简陋的铁皮房。出于对摄政王的尊重,皮利索邀请佳士提斯和我与他住在一起。
许多矿工,特别是那些来自泰姆布兰的矿工,拿着佳士提斯像酋长一样地对待,他们用现金作为礼物欢迎他。当酋长来参观时,这通常是一种惯例。这些人多数都住在同一个住所,矿工们通常是按部落隔离安排住处。矿主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不同部落为了共同的不满情绪而团结在一起,因此有利于管理。但隔离安排住处也常常会导致不同部落、不同氏族之间发生派系争斗。对于这种争斗,矿主没有刻意地加以防止。
佳士提斯把他得到的礼物也分给我一些,并且作为奖金另给我一点额外的英镑。开始那几天,我们的口袋里总是叮当响着新的有钱人通常有的那种硬币碰击声。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成了一个百万富翁。我开始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幸运之光就在我身上闪耀,如果我们不是在大学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说不定我们真的已经成了百万富翁!我又一次看到,命运把我抛弃了。
很快,我作为一名值夜班的金矿保安开始工作。矿上给我发了一身保安服、一双皮靴、一顶钢盔、一台闪光灯、一个哨子和一根圆头木棒。这是一种一端有大圆球的木棒。工作很简单:站在上面写着“注意,当地人从这里穿过”的警示牌的矿井入口,检查每个从这里出入的人是否有通行证。开始几天,我在矿上巡查并未发现任何事故隐患。然而,有一天深夜,我确实逮住了一位喝醉了酒的矿工。但是,他温顺地出示了通行证,然后就回了他的住所。
由于让成功冲昏了头脑,佳士提斯和我向我们在家就认识的一位朋友吹嘘起了我们的聪明,这个人也在这个金矿上工作。我们对他说,我们如何逃出王宫,如何欺骗摄政王等。尽管我们让那人为我们保密,但是,他却直接去找那位工头告了密。一天以后,皮利索召见了我们。他问佳士提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摄政王批准你弟弟出来工作的证明在哪里?”佳士提斯说他对此事已经作了说明,摄政王已经寄了证明信。皮利索并没有由于他的回答而态度有所缓和。我们感觉似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了一封电报。“我与摄政王已经取得了联系。”他用严肃的口气说,并把电报递给了我们。电报上说:“立即把两个孩子送回家。”
然后,皮利索对我们大为恼火,骂我们向他撒谎,说我们滥用他的热情和摄政王的好名声。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在矿工中集资,买火车票把我们送回特兰斯凯。佳士提斯反对回家,并说,我们仅仅是要在矿上工作,我们能自己做主。但是,皮利索根本不予理睬。我们感觉很丢面子,也感到受了侮辱。于是,我们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但下定决心不回特兰斯凯。
我们很快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去找A.B.埃克苏玛医生。他是摄政王的一个老朋友,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埃克苏玛医生来自特兰斯凯,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医生。
埃克苏玛医生见到我们很高兴,并非常热情地向我们打听穆克孜韦尼家乡的情况。我们告诉他许多有关我们来约翰内斯堡的半真半假的情况,并说很想在金矿上找个工作。埃克苏玛医生说他愿意帮助我们,并马上给金矿协会的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打了电话。金矿协会是代表矿主的很有权威的组织,专门管理矿工雇用事务。埃克苏玛医生告诉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我们是如何如何优秀,他应该给我们找个地方。我们谢别了埃克苏玛医生,马上去找维尔比拉伍德先生。
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是一个白人,他的办公室比我见过的任何办公室都气派。
他的写字台似乎有足球场那么大。我们在一位名叫费斯特尔的金矿老板的陪同下见到了他。我们把说给埃克苏玛医生的原话又向他复述了一遍,维尔比拉伍德先生对我说的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继续深造但并非完全是事实的理由印象很深。
“好吧,小伙子们,”他说,“我将介绍你们去与克朗金矿的经理皮利索联系,我告诉他给你们安排个管理工作。”他说他与皮利索在一起工作了3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皮利索从来没有对他不忠过。佳士提斯和我听后感觉局促不安,但是并没有说什么。尽管有些担心,但我们幼稚地认为,我们现在比皮利索占优势,因为我们有他的上司维尔比拉伍德为我们撑腰。
我们又回到了克朗金矿办公室。由于我们递交了维尔比拉伍德的信,所以,在那里有一位白人经理对我们很客气。就在这时,皮利索从办公室门前经过,他一眼看见了我们,于是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你们这两个青年人!你们又回来了!”他生气地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佳士提斯很镇定。“我们是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派来的。”他回答说,语气中带有一点挑衅的味道。皮利索先生考虑了一会儿。“你告诉他你们是背着你父亲偷着跑出来的吗?”皮利索反问道。佳士提斯没有吭声。
“你不用指望在我开办的金矿上找到工作!”他吼叫着说,“现在我不想见你!”佳士提斯挥舞了一下维尔比拉伍德先生的信。“我不在乎这封信!”皮利索说。我观察那位白人经理,希望他能管管皮利索。但是,他却像雕塑一样在那里不吭声,似乎像我们一样胆怯。我们拿皮利索毫无办法,只好乖乖地离开那个办公室,感觉比第一次还要沮丧。
我们的时运开始逆转:没有工作,没有希望,也没有地方住。佳士提斯在约翰内斯堡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他进城为我们寻找居住的地方。与此同时,我提着我们的行李箱,打算随后在约翰内斯堡南面的小城镇乔治高诗与他碰头。
我请求在老家就认识的一位名叫比基沙的人帮我把箱子提到前门,有一位保安把我们挡在门口,说是要搜查一下箱子。比基沙不同意,说箱子里没有犯法的东西。保安说搜查是例行公事。他草率地搜查了一下箱子,连里面的衣服都没有翻动。比基沙是个高傲的人,当保安正准备盖上箱子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找这个麻烦?我告诉你,里面没有什么犯法的东西。”这句话激怒了那位保安,他决定仔细检查箱子里的东西。当他搜查箱子里的每个角落并搜查每个衣服口袋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紧张。他一直翻到了箱子底,找到了我不希望他找到的那件东西:裹在我的衣服里面的那把左轮连发手枪。
他转身对比基沙说:“你被捕了。”然后,他吹响了哨子,哨音唤来了一群保安。当他们把他带往当地警察局的时候,比基沙用担心而困惑的神情看着我。
我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跟在他们后面考虑对策。老式左轮连发手枪是我父亲的遗物,是他临死前留给我的,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为了防身,我把它带在身上来到了这座城市。
我不能让朋友承担罪名,在他们进了警察局不久,我就进去要找负责此事的警察官。我被带到了一个警察官面前,尽量直截了当地坦诚说:“先生,在我朋友的箱子里发现的那支枪是我的。它是在特兰斯凯从我父亲那里传给我的。我把它带到这里,是怕遇上强盗。”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学生,我仅仅是暂时住在约翰内斯堡。警察官随着我的解释也和气了一点,他说,他将马上释放我的朋友。并说,尽管他不逮捕我,但是因为我拥有枪支,必须把我送上法庭。需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礼拜一上午去法庭应诉。我很感激他,告诉他我礼拜一上午一定去法庭。那天上午我真的去了,在法庭上我受到了名义上的惩罚。
与此同时,我也作出了安排,准备去乔治高诗镇,住在我的堂哥戈利克·穆贝基尼家。他是一个卖衣服的小商贩,只有一间盒子大小的小房子。他友好而热情,到了那里不久,我就把我准备当一名律师的真实愿望告诉了他。他称赞我有志气,并说他将对我说的话认真加以考虑。
几天后,戈利克告诉我,他准备带我去见“约翰内斯堡那个最好的人”。我们乘坐去市场大街的汽车来到了一个财产代理公司。市场大街是一个人口密度大、玩耍娱乐地方多的去处。这里的每条街道都有满载旅客的有轨电车和布满摊贩的人行道,让人感觉财富就在每一个角落。
那时的约翰内斯堡既是一个前线城市,又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屠夫就在办公大楼临近的大街上卖肉。拥挤的商店附近到处都是帐篷。与高耸入云的高楼为邻的女士们把她们喜好的东西从房子里挂出来。工业由于战争而得到振兴。
年,南非作为一个英联邦的成员国曾向纳粹德国宣战,农村为战争输送过人力和物力。劳工们的需求量很大,约翰内斯堡成了吸引非洲人从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的“磁铁”。我在约翰内斯堡的1941年到1946年之间,这座城市里的非洲人成倍地增加,每天早晨,人们会感觉这座城市又比昨天扩大了一圈。男士们在非欧洲化城镇上寻找工作和住处。这些城镇包括纽克莱尔、乔治高诗、亚历山大、索菲亚顿和西部当地人乡镇。数千个火柴盒式的房子像监狱般建造在光秃秃的不毛之地上。
戈利克和我坐在财产代理公司的会客厅里,一位可爱的黑人招待员向办公室里面的老板报告了我们的到来。报告完此事之后,她那灵巧的手指开始随着打印信函在键盘上来回跳动。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非洲人打字员,见到女性黑人打字员的机会就更少。在我参观过的乌姆塔塔和福特黑尔为数不多的政府部门和贸易公司里,打字员总是白人和男士。我之所以对这位年轻女士印象特别深,这是因为,那些白人男打字员只能用两个慢慢移动的手指打印信函。
她很快让我们进了办公室,在那里我被介绍给一位男士。此人看上去有30多岁,长着一张聪明、善良、表情丰富的脸。他身穿一件双排扣的上衣,尽管年龄不大,但在我看来却很老练。他也是特兰斯凯人,但他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通过人来人往的会客厅和写字台上堆着厚厚的材料判断,他是一个忙忙碌碌、事业有成的男士。不过,他并没有草率地应付我,似乎对我的到来由衷地感兴趣。
他名叫瓦尔特·西苏陆。
西苏陆的办公室专门配备了非洲办公用具,在20世纪40年代,仍然有一些私有财产允许非洲人购买。非洲人购买的小农场大多坐落在像亚历山大和索菲亚顿这样的地方。非洲人连续几代都在这里拥有自己的家,其余的非洲人则居住在城市,城市里有许多火柴盒式房子的住户需要向约翰内斯堡市政厅缴纳租金。
西苏陆由于既是商人又是当地的领导人而出名,他已经是社团的代表人物。
在我叙述我在福特黑尔遇到的困难、准备当律师的决心和想在南非大学注册以便通过函授教育取得学位的过程中,他一直认认真真地倾听。由于疏忽,我没有告诉他我到约翰内斯堡的情况。当我说完后,他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沉思我所讲的事情。然后,他看了看我说,他的同事中有一个白人律师,名叫拉泽·希代尔斯基,并称赞他是一位高雅而进步的人。他说,希代尔斯基对非洲教育很热心,他将与他谈谈,让我当他的合同雇员。
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英语水平和生意成功都是获得高学历的直接结果。我推断,西苏陆事业有成,他当然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我们离开西苏陆的办公室后,我堂兄告诉我,西苏陆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在约翰内斯堡,我必须忘却从福特黑尔大学得到的这个教训。我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取得文科学士学位就意味着当官,要想当官就必须有文科学士学位。但是,在约翰内斯堡,我发现许多杰出的官员根本就没通过标准四级教育考试。即便是我学完文科学士学位所要求的全部英语课程,我的英语流利水平和口才也比不上我在约翰内斯堡遇见的许多从来没有获得学历毕业证的人。
与堂兄一起住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后,我准备搬到英国圣公会教教堂的J.马布托牧师家里去住。他家位于亚历山大镇第八大街。马布托牧师是泰姆布人,也是我家的朋友。他是一个慷慨而信奉上帝的人。他的夫人(我通常称她高诰),是一位热情好客而乐意帮助别人的人,她也是一位高级厨师。作为一名对我家庭很熟悉的泰姆布人,马布托牧师认为有责任帮助我。他经常对我说:“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但是,我还是没有从克朗金矿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因为我没有把我离开特兰斯凯的情况告诉马布托牧师。搬到马布托牧师家中不久,有一位客人来拜访马布托牧师,我陪着他们喝茶。不凑巧的是,来客正是金矿协会的费斯特尔先生。当佳士提斯和我去找维尔比拉伍德先生的时候,费斯特尔一直在场。费斯特尔先生和我以彼此相识的方式相互打了招呼。尽管我们没提上次见面的事,但是,第二天,马布托牧师就把我叫到一边,明确告诉我,我不能再在他家住下去了。
我埋怨自己没有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我变得如此习惯于说谎,甚至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也说谎。我相信,如果我事先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他肯定不会介意。但是,他从费斯特尔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他感觉上当受骗了。在约翰内斯堡短暂的滞留期间,我说了一路的谎话,而每次说谎最终都会给我带来苦果。当时,我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胆小且没有经验。我知道,我还没有在新的生活中迈出正确的一步。在这种情况下,马布托牧师可怜我,于是又给我找了一个居住的地方,让我与他的邻居库玛住在一起。
库玛先生是亚历山大很少拥有土地的黑人精英之一。他的家坐落在第七大街号。房子很小,特别是他有6个孩子,房子就更显得狭小。房子虽小但很温馨,不但有一个圆形房子,而且房子前还有一个微型菜园。为了勉强度日,库玛先生像许多亚历山大居民一样,只好向外租赁住房。他在房子后面建了一个薄顶房,比棚子好不了多少,地面又脏又乱,没有取暖设施、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但是它却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天地。有这样一个小房子住,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同时,在瓦尔特先生的推荐下,拉泽·希代尔斯基同意我取得文科学士学位时聘用我。“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三人公司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受理黑人和白人的诉讼案子。除了学习法律和通过一定水平的考试之外,为了在南非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还必须经过几年的学徒,这种学徒叫供职约定。但是,为了能获得供职约定,我必须首先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在南非大学读函授。这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教育形式,人们可以通过函授获得学历证书和学位。
除了受理常规诉讼案子之外,该律师事务所还向非洲诉讼委托人提供财产交易方面的法律服务。瓦尔特给这个律师事务所介绍了许多需要财产抵押的诉讼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将受理他们的贷款申请,然后收取代理费。这种代理费需要分给非洲财产代理公司。事实上,律师事务所拿大头,剩下的一小部分留给非洲财产代理公司。黑人只能从桌面上拿一点点报酬,并且别无选择。
就是这样,该律师事务所也比其他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自由得多。这是一家犹太人开办的事务所。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犹太人在种族和政治问题上比白人心胸宽阔得多。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历史上偏见的牺牲品。作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拉泽·希代尔斯基能接受一个非洲青年作为约定雇员,这在当时是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儿。这个事实也是该律师事务所更崇尚自由的一个证明。
希代尔斯基先生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毕业生。我非常尊敬他,他对我也特别好。我到该事务所工作的时候,他只有35岁左右。他热心于非洲教育,为非洲学校捐钱,有时免费服务。他身材修长,有尊严、有礼貌,留着整齐的八字胡。对我的事,他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他告诉我,教育对我个人和全体非洲人都非常重要,只有大规模地开展教育,我们的人民才能获得自由。他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遭受压迫,因为他能够自我思考。他一遍一遍地告诉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也就为非洲人树立了成功的榜样。这就是我应该走的最有价值的道路。
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里与该事务所的多数职员见了面,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高尔·瑞德贝的非洲雇员。我与高尔就在一个办公室。高尔比我大十岁,他既是一个职员,又是翻译和通信员。他个子不高,但肌肉发达,很结实。他能流利地讲英语、索托语和祖鲁语,并能用这些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他很幽默,很有信心,也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和辩论能力。在约翰内斯堡的黑人社会里,他是一个着名的人物。
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第一天上午,一位年轻的白人秘书丽波曼女士把我拉到一边说:“纳尔逊,在这个律师事务所里没有肤色隔阂。”一位服务生托着茶盘和杯子来到了前会客厅。她说:“为了你的到来,我们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杯子,秘书负责给几位主管端茶倒水,而你和高尔需要自己端,我们也都是自己端。当茶水来了的时候我会叫你们,然后你们可以拿你们的新茶杯。”她还让我把这些话告诉高尔。对她的殷勤服侍我很感激。但是我知道,她那么认真地提及“两个新杯子”只不过就是她声称不存在肤色隔阂的一种证明。秘书们可以与两个非洲人共同喝茶,但喝茶的杯子不能混用。
当我把秘书丽波曼的话转告给高尔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他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一种有害的思想进入了一个小孩的头脑中。纳尔逊,在喝茶的时候不要担心,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11点钟,丽波曼女士告诉我们茶水来了。秘书和其他职员面前都有了茶水,高尔走到茶盘前假装没有看见那两个新杯子,而是从旧杯子中选了一个,紧接着慷慨地放入糖、牛奶,然后倒上茶水。他慢慢地搅动着杯子里的茶水,然后站在那里非常自我满足地喝起来。丽波曼瞪大眼睛看了看高尔。此时高尔向我点了点头,好像是说:“轮到你了,纳尔逊。”
我困惑了一会儿,我既不想冒犯丽波曼,也不想疏远我这位新同事。因此,我决定采取对我来说似乎是最谨慎的应对方式:我一点都不想喝茶,我不渴。当时我23岁,作为一个男子汉,作为一个约翰内斯堡的居民,作为一个有上百人律师事务所的雇员,我才刚刚独立,我把中间道路看作最好、最理智的道路。从此之后,一到喝茶的时间,我总是独自一人到事务所内的小厨房里去喝茶。
秘书也并非总想得那么周到。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在所里也更有经验了。有一天,我正在向一位白人秘书口授情况,这时,这位秘书认识的一位白人诉讼委托人走进了办公室,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为显示她并不是在听一个非洲人口授,她从钱包里掏出6个便士,傲慢地说:“纳尔逊,出去到化妆品商店给我买些香波。”于是,我离开办公室去给她买香波。
开始,我在律师事务所里干的都是些很基础性的工作,既是一个法律职员,又是一个通信员。找资料、整理资料、资料归档,这都是我要干的活。后来,我又为非洲诉讼委托人起草合同。但是,不管活多么小,希代尔斯基先生总是向我说明为什么干和为什么让我干。他是一个有耐心、宽厚待人的师长,不但努力向我传授法律知识,而且还告诉我背后的道理。他的法律知识面很宽,因为他认为法律是可以用来改变社会的工具。
在希代尔斯基先生传授他的法律观点的时候,他警告我要抵制政治方面的影响。他说,政治会在人们中间产生坏的影响,政治是麻烦和腐败的根源。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沾染上政治,我将有可能陷入可怕的境地。他忠告我,不要与他认为是制造麻烦和煽动是非的人在一起,特别是高尔·瑞德贝、瓦尔特·西苏陆。希代尔斯基在尊重他们的才能的同时,也厌恶他们的政治倾向。
高尔的确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这种表述恰如其分。他是一个在非洲社团内有影响的人,但对于其影响方式,希代尔斯基先生并不知道,或者说只是有点怀疑。他是西部当地人镇上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由位为了镇上的问题出面与当局交涉的人组成。尽管权力不大,但该委员会在当地人中却有很高的权威。我很快知道,高尔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又是南非共产党党员。
高尔是个很有主心骨的人。他对我们的雇主并不客气,常常为几位雇主对非洲人不公而谴责他们。他会说:“你们的人窃取了我们的土地,并奴役我们,现在你们又无情地剥削我们。”一天,我外出办完事回来走进了希代尔斯基的办公室,高尔转身对他说:“看!你坐在这里和老爷一样,而我们四处奔忙为你们办事。这种局面应该倒过来,有一天是会倒过来的,我们将把你们赶进大海里去。”高尔然后离开办公室,希代尔斯基在那里沮丧地直摇头。高尔虽然没有文科学士学位,但他却是比带着闪光的学位离开福特黑尔大学的那些人水平还高的一个榜样。这不仅表现在他接受知识快,而且也因为他勇敢而自信。尽管我有意为完成学业、获取学位去法学院学习,但是,我从高尔那里得知,学位本身并不是晋升的保证,只有走出大学、融入社会中证明自己,学位才有价值。
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我并不是唯一的约定职员。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人名叫耐特·布瑞格曼,他在我被录用前不久才开始在该事务所工作。耐特聪明、友好、思路开阔,似乎完全“色盲”,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白人朋友。他模仿能力很强,可以逼真地模仿简·斯马茨、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的声音。我经常见他对法律事务和办公程序发表意见,并不知疲倦地帮助别人。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办公室里,耐特掏出了一包三明治。他拿了一个三明治对我说:“纳尔逊,拿着三明治的那一头。”我不知他为什么让我这样做,但是,我饿了,因此决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好,掰一块。”他说。
于是我就掰了一块,三明治变成了两块。“好吧,让我们一起吃。”他对我说。
在我嚼着三明治的时候,耐特说:“纳尔逊,我们现在做的就象征着共产党的理论——分享我的一切。”他告诉我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并向我介绍了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我知道高尔是共产党党员,但是他从来没有向我介绍过共产党的基本知识。那天我听了耐特的话,后来,他在宣传共产主义优越性的时候试图劝我加入共产党。我听出他的意思,也提问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参加。我不想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希代尔斯基的忠告还在我的耳边萦绕。我对宗教相当执着,共产党对宗教的立场使我对它敬而远之。不过,我很欣赏那半块三明治。
我喜欢与耐特在一起,我们经常到外面走走,其中包括去听演讲和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我出去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我越来越了解我们国家种族压迫的历史,并且把南非的斗争看成是纯粹的种族斗争。但是,共产党则是通过阶级斗争的透镜观察南非问题,他们认为是有没有压迫的问题。这个理论激发了我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我又觉得这种理论与今天的南非似乎没有特别关系。它可能适用于德国、英国或俄国,但对我所了解的这个国家似乎不适用。即便如此,我仍然去听、去学这些东西。
耐特邀请我参加了几次聚会,那里各种人混杂在一起,有白人、非洲人、印度人,也有有色人 。这些聚会是由共产党组织的,多数参加者都是共产党员。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时自己心里有些担心,主要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服装。在福特黑尔大学,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参加任何社会活动都要系领带、穿正规衣服。尽管我的衣柜里的衣服极其有限,但是,我还是设法找到了一条领带去参加聚会。
我发现了一群有生气且喜欢群居的人,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肤色。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各色人种混杂在一起的聚会。我与其说是一位参加聚会者,倒不如说是一位观望者。我感到羞涩,担心出现什么差错,不习惯参加海阔天空、情绪激昂的对话。与我周围发表成熟见解的人相比,我的思想似乎还没有开化。
那天晚上,通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迈克尔·哈迈尔先生。我听说他是罗德斯大学毕业的英文硕士。我对他的这一学位印象尤其深刻,但到我见到他的时候,心中却在犯嘀咕:“这个人有硕士学位,竟然没有打领带!”对于这个认识上的矛盾,我无法理解。后来,迈克尔和我成了好朋友。我开始佩服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帮我抛弃了极其愚蠢的旧思想。他不仅是一个卓越的作家,也是一个执着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他能够享受很富有的生活,但是,他却坚持与非洲人相同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