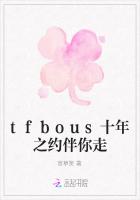对托马斯?阿奎那[4]来说,宇宙仍然是一个人;对于斯宾诺莎[5]来说,宇宙是一种物质;对康德[6]来说……宇宙是一种绝对命令;对庞加莱[7]来说,宇宙是一种便利;对于皮尔森来说,宇宙是一种交换的介质。这位历史学家不停地对自己重复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他认为他的教育是完全的,但又为其感到遗憾。作为一种爱好,他极力赞扬他在19世纪所受的教育——那时还在讲上帝是父亲、自然是母亲——在一个科学世界里,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好意。
美国经济的极大成功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太多安慰。正如年轻的沃尔特?李普曼[8]所说的那样,现代工业“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事实,它弄黑了我们的城市,养活了我们的孩子,是男人和女人头上的一个暴君,生产出了大量的产品——有好的、坏的和可怕的。”虽然所有美国人在每年的7月4日都要赞美“渴望自由地呼吸的拥挤的大众”,但同样的“不幸的拒绝”明显正在遥远而广阔的海滨建设一大群大型的东方城市。在波士顿和纽约的贫民区里,高犯罪率和疾病让人们感到恐怖。
但解救的办法也就在手边。美国钢铁公司成立的时候,查尔斯?施瓦布就强调,最大型的公司是由接受过“商业科学”培训的专家管理者来经营的: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流程的每一步都事先计划好了。所有的浪费都被砍掉了。”李普曼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时尚风向标,他也热情地对施瓦布的话做出了响应:“美国的商业已经经历了如此深刻的重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抓住它的真谛了……人类努力的范围比以前大多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范围内的全面变革。”但是,“新的商业世界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商人,因为,与管理以前的鼓风炉不同,管理这个钢铁托拉斯有不同的能力要求。”李普曼又说,那些要求解散托拉斯的人没有理解这一点,即一个公司的规模是否合理,“应当由新的管理科学专家来决定……事实上,管理正在成为一门应用科学,能够找到针对巨型公司的管理方法。”1887年,爱德华?贝拉米[9]写了一部乌托邦式的小说《回顾》;他在小说中预测,一旦把所有的生产都交给一个“单一的企业联合……大托拉斯”,那么社会矛盾和冲突就会消失。
从一个学者或者新闻记者的角度来看,像标准石油或者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巨型公司呈现出的是一个完美而安静的外表: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前,在费城的博览会上,柯利斯的巨型蒸汽机像一位沉思的神灵一样高高矗立,令人肃然起敬。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产生了明星似的吸引力,也强调了商业的科学方法。在博览会上,宾夕法尼亚铁路演示了一台机车的测试实验:巨型高架式起重机能够把最大型的机车吊放在机械托辊上,机车在获得动力后咆哮着以最高速度驶离——它的时速可达70英里——多个小组的机械师在认真地测量温度、燃料消耗、牵引阻力和牵引动力,还一次次地让机车停止运转以更换零部件或者调整设置。
“商人科学家”这一概念源自皮尔森的《科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他在书中坚持认为,科学在根本上讲的是方法。科学家追求的是纯粹的客观现实,它不带个人感情色彩,也不涉及价值。他又继续“在对事实之间的关系和顺序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认真而且通常是艰苦的分类;最后才发现一个简单的结论或者公式——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规律。”皮尔森写道,“科学就是方法,这就要求所有的现象,意识或者物质的——整个宇宙——都成为它的研究领域……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过去或者现在的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科学研究的素材。”总之,没有必要放弃对进步的承诺以及美国例外论;但是,通往一个明亮的城市的道路要靠科学之光而不是上帝来照亮。
(本页插图文字说明:原书296页
科学管理活动: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机车测试实验室,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阿尔图纳。之前,它曾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过。)
边际主义经济学好像支持了皮尔森的主张。市场中有无数最小单位的参与者,他们遵循着利己主义这一简单的原则;正是这些参与者的市场行为最终形成了正确的价格;这个过程就像是少数非常简单的规律规范了气体分子的自由碰撞一样。当时正在逐渐成熟的社会学研究也搭乘上了统计学这辆快车;1905年美国社会学协会成立时,它只接纳“科学的”实践者。社会学被明确地定义为一种“社会控制”科学,梳理出了个体互相作用的规律——正是这些规律创建了一个“社会平衡机构。”甚至连亨利?亚当斯也试图建立一个“动态的历史理论,”希望能够发现控制国家兴衰的起伏规律。约翰?德威[10]确信学校也能像“伟大的工厂”那样来管理,从而能按照他的自由民主观点为人民培养出具有自立精神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