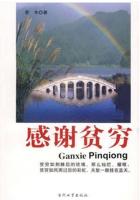1925年5月30日,上海有两千多工人和学生,为日商内外棉纱第七厂开枪打死20岁的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杀伤工人十余人的暴行,怒火冲天地前往各租界示威游行,在英大马路(即南京路)演讲时,遭到外国巡捕的棍棒驱赶和水龙头的疯狂扫射,并有一百多人被逮捕,扭进老闸捕房;这就更激起了上万群众(主要是学生和工人)的极大愤慨,便集中到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这时英帝国主义的爪牙“三道头”、“红头阿三”在捕房的甬道口,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密集的群众开放排枪,当场杀害了13人,受伤的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我那时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是参加了讲演队去游行的,亲眼目睹这场惨剧。
第二天虽然下大雨,我们却加倍坚决勇敢地再涌到英大马路去游行讲演,把“援助工人!”、“援救被捕人员!”、“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揭贴和传单散发给群众,并张贴在商店的玻璃门窗上;我们有数百名男女学生的一支队伍听从领队的指挥,直冲到河南路天后宫内,去包围总商会。总商会的负责人正在阁楼里跟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上海总工会的代表、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谈判罢市的事;我们就在外面呼喊口号,要求总商会负责人宣布罢市。谈判一直挨到黄昏时刻,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正会长虞洽卿到北京去了)在群众的威迫下,像接受“城下之盟”似的终于签字,当众宣布“同意罢市”。我们这才在“明天罢市”的欢呼声中有秩序地散去。
日棉纱厂枪杀顾正红是在5月15日,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把这次斗争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总工会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6月4日联合各界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随即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上海罢市坚持了将近一个月之久。
6月初,上海学生联合会派我和立达同班同学贺美璇去宁波宣传募捐。贺是宁波人,到宁波后,我们先到宁波学生联合会去接洽,被安置在四明中学(系教会学校)住宿。白天我们上街去,到市中心、热闹场所、城隍庙等处讲演自己目击的那些惨相,喉咙喊哑了,含着药片再继续讲。听众有许多被感动得流下了同情之泪,同声呼喊“为死难烈士报仇!”、“打倒英日强盗!”,我们同时也向商店及行人等募捐;夜晚我们到妓院去,向正在吃花酒的嫖客们宣传募捐。狎妓者大多数都是有钱的商人,喜欢在妓女面前摆阔气,我们也就利用这种心理向他们劝募捐款;其中有不少个确具爱国心,愿掏腰包把钱交给我们;但也有人在募捐册上故意写上几百几百,叫我们第二天去拿,我们也信以为真,其实他们见青年头脑单纯,是在愚弄我们,哪里还能拿得到钱,即使他们交了出来,妓院里的人也要从中贪污,不肯给我们。我和贺美璇在三四天内也毕竟募到了三四千元,想到上海罢工的工人等着要钱用,我们便赶快回去把捐款交给工商学联合会。
我在宁波四明中学结识了该校学生韩光汉。他后来到上海进学校,同我在上海景贤女中读书的大侄女陈智英结婚。光汉年少英俊,是共产党员,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在武汉清党时,他在那边做地下工作,因积劳成疾而病故。贺美璇回上海后,改名为贺大同,去工厂做宣传工作,不幸被捕而英勇牺牲。
我胞兄陈蕴玉见报上登载陈虞钦(交通大学的学生)被枪杀的消息,疑以为是我,急忙派一个老家人到上海学校找我。学校当局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老家人就在学校里坐等。等我从宁波回来时,他便催促我回老家去。后来我就在故乡乌镇继续搞运动,如组织“雪耻会”抵制英日货等等。
下半年学校开学时,我有位极知己的同班同学夏侠(松江县叶榭镇人)竟服氰化钠自杀了,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全校师生莫不为之震动!在此之际同学黄河清(即黄源)又悄悄通知我,巡捕房来抓人,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在同学自杀,上海又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下,我就无法再安心地在立达学园求学了,于是央求我姑母代为向我胞兄陈蕴玉说明我要去日本读书。那时东京的费用与上海相比较贵不了多少。这年年底我就和同班同学张贞黻出国去了。
在上海,我前后读过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小学(七年制)、吴凇中国公学(闹风潮我才跟着老师们离开)和立达学园(创办于上海小西门黄家阙路,后迁至江湾)等三个学校。1923年,在中国公学加入SY(社会主义青年团)秘密组织,介绍人是中公同学梅中林、杨显,在国民党清党时他俩都牺牲了。那时我的大表哥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二表哥沈泽民在上海《民国日报》编副刊;我时常接到《新青年》、《响导》这些进步的刊物,都是二表哥寄给我的。大表哥的家在闸北宝山路鸿兴坊,我每星期六下午都去他那里,下星期一早上才回学校。他家里一楼一底并不宽敞,晚上我跟姑母睡在楼上后边的小亭子间里。星期天来的客人很多,如瞿秋白、杨之华、杨贤江、恽代英、向警予各位先驱者我都见过。他们当时都是中共在上海发动革命运动的决策者和领导同志。我见他们时常围坐着一张八仙桌作“方城之戏”,他们只用筹码不用钱的赌博,起初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以打牌的噼啪声作为掩护,正在互通情报议论时政。“五卅惨案”前后,表哥家里的客人就更加多了,我也一天不止一次地向他家里跑,为的是去报告一些所见所闻的事情。表哥那时写的几篇散文速写,如《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风雨——五月三十一日》、《街角的一幕》等等,我现在读来确实感到非常真实而亲切!1973年10月2日,他深情地写给我的《寿瑜清表弟》七律首联的两句:“往时真理共追求,一掷何靳年少头。”后来他在写给我的屏条上把“寄踪”两字改为“萍寄”,也就是指我参加“五卅惨案”那段历史的。
8年前,我66岁,接到表哥惠赠我的《寿瑜清表弟》这幅珍贵的屏条时,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并流下了感激之泪!记得在回信中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六岁丧父母,从小就受着姑母和您的爱护与培养。我的一家人之所以有今天,是全仗您的大力帮助!因此,捧读着您对我这样垂青厚爱,将我微不足道的一生概括得这样全面,并鼓励我勤奋工作这美好的诗篇和挺秀的手笔,叫我怎能不感激涕零呢?!”
承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0月28日来函指示:1925年6月8日上海《申报》刊载消息:“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陈瑜清张秋人等50余人在后乐园召开宁波学联声援‘五卅’运动的紧急会议? ?”嘱我回忆有关张秋人烈士的事迹,为保存革命史料,教育后代作出贡献。于是我就开动脑筋,挖掘记忆,但想来想去,总是想不出有关张秋人烈士的事迹来。推究原因,大概是因为张秋人烈士比我年长九岁,我们既未同过学,又不是同乡(他是诸暨人,我是乌镇人),在宁波我与他虽有一同参加会议之缘,但这是五十六年前的事情,时光老人把我对他的记忆冲洗得不留一点痕迹了,所以只好交白卷,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我能记得的,略如上述而已。
原刊于《嘉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