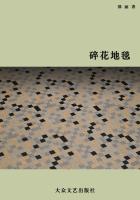“……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感到困惑不解的拉祖米欣反复说,竭力想驳倒拉斯科利尼科夫刚刚说的理由,他们已经走到了巴卡列耶夫的旅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和杜尼娅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们了,他们热烈地谈论着,拉祖米欣不时在路上停下来,单单就是因为他们还是头一次明确地谈起这一点,这就使他感到既惶惑,又十分激动了。
“你不相信好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漫不经心似地冷笑着,回答说,“你一向是什么也觉察不到,我可是把每句话都掂量过了。”
“你神经过敏,所以才去掂量……嗯哼……真的,我同意,波尔菲里说话的语气相当奇怪,尤其是那个坏蛋扎苗托夫!……你说得对,他心里肯定有什么想法,……不过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一夜之间他却改变了看法。”
“不过恰恰相反,恰恰相反!如果他们有这个愚蠢想法的话,他们准会竭力隐瞒着它,把自己的牌藏起来,才好逮住你……可现在……这是无耻和粗心大意!”
“如果他们有了事实,也就是确凿的证据,或者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儿根据的怀疑,那么他们当真会把他们玩弄的把戏掩盖起来,以期获得更大的胜利(那样的话,他们早就会去搜查了!),可是他们没有证据,一点儿证据也没有,……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模棱两可,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想法,……所以他们才竭力想用这种厚颜无耻的方式来把我搞糊涂,或许,因为没有证据,他自己也很生气,心中恼怒,于是就脱口而出了,不过也许是有什么意图……他好像是个聪明人……也许他是故意装作知道的样子,这样来吓唬我……老兄,这或许他自己的某种心理……不过,要解释这一切,让人感到厌恶,别谈了!”
“而且是侮辱性的,侮辱性的!我理解你!不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明确地谈起这个问题(这很好,我们终于明确地谈起来了,我很高兴!)……那么现在我坦率地向你承认,我早就发觉他们有这个想法了,当然,在这段时间里,这只是一个勉强可以察觉的想法,还不敢公然说出来,不过即使不敢公然说出来吧,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怎么敢这样?他们这样想的根据在哪里,在哪里呢?要是你能知道我感到多么气愤就好了!怎么:就因为是个穷大学生,因为他被贫穷和忧郁折磨得精神极不正常,在他神智不清,害了重病的头一天,也许早就开始神智不清了(请记住这一点!),他多疑,自尊心很强,知道自己的长处,六个月来躲在自己屋里,没和任何人见过面,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靴子也掉了鞋掌,……站在那些卑鄙的警察面前,受尽他们的侮辱;而这时又突然面对一笔意想不到的债务,七等文官切巴罗夫交来的一张逾期不还的借据,再加上油漆的臭味,摄氏三十度的高温,沉闷的空气,屋里一大堆人,又在谈论一件凶杀案,而头天晚上他刚到被杀害的老太婆那儿去过,这一切加在一起……可他还没吃饭,饥肠辘辘!这怎么不会昏倒呢!就是根据这个,他们的全部根据就是这些东西!见鬼!我明白了,这真让人感到愤慨,不过,要叫我处在你的地位上,罗季卡,我就会对着他们哈哈大笑,或者最好是啐一口浓痰,吐在他们脸上,越浓越好,还要左右开弓,扇他们二十记耳光,这样做很有道理,得经常这样教训教训他们,打过了,就算完了,别睬他们!精神振作起来!他们这样做太可耻了!”
“这一切他说得真好,”拉斯科利尼科夫想。
“别睬他们!可明天又要审问了!”他苦恼地说,“难道我得去向他们解释吗?昨天我在小饭馆里竟有失身分地和扎苗托夫说话……我都感到懊悔了。”
“见鬼!我去找波尔菲里!我要以亲戚的方式向他施加压力;叫他把心里的想法全都坦白地说出来,至于扎苗托夫……”
“他终于领悟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想。
“等等!”拉祖米欣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高声叫喊起来,“等等!你说得不对!我再三考虑,还是认为你说错了!唉,这算什么圈套?你说,问起那两个工人,就是圈套吗?你好好想想看:如果是你干的,你会不会说漏了嘴,说你看到过在油漆房间……看到过那两个工人?恰恰相反:即使看到过,你也会说,什么都没看见!谁会承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呢?”
“如果那事是我干的,那么我准会说,我看到过那两个工人和那套房子,”拉斯科利尼科夫不高兴地,而且显然是怀着厌恶的心情继续回答。
“为什么要说对自己不利的话呢?”
“因为只有乡下人或者是最没有经验的新手,才会在审讯时矢口抵赖,稍微成熟或多少有点儿经验的人,一定尽可能承认那些表面上的和无法隐瞒的事实;不过他会寻找别的理由来说明这些事实,硬给这些事实加上某种独特的,意想不到的理由,使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给人造成不同的印象,波尔菲里可能正是这样估计的,认为我一定会这样回答,一定会说,看到过,而为了说得合情合理,同时又一定会作某种解释……”
“然后他会立刻对你说,两天以前那两个工人不可能在那里,可见你正是在发生凶杀案的那一天晚上七点多钟去过那儿,单是这样一件并不重要的小事,就会使你上当受骗!”
“而他就正是这么盘算的,认为我一定来不及好好考虑,准会急急忙忙作出较为真实的回答,却忘了,两天前工人们是不可能在那里的。”
“这怎么可能忘了呢?”
“最容易了!狡猾的人最容易在这种无关重要的小事上犯错误,一个人越是狡猾,就越是想不到别人会让他在一件普通的小事上上受当骗,正是得用最普通的小事才能让最狡猾的人上当受骗,波尔菲里完全不像你想得那么傻……”
“他这么做,真是个卑鄙的家伙!”
拉斯科利尼科夫不禁笑了起来,但同时他又觉得,作最后这番解释的时候,他那种兴奋和乐于解释的心情是很奇怪的,然而在此以前,他和人谈话的时候,却是怀着忧郁的厌恶的心情,显然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不得不说。
“我对某几点发生兴趣了!”他暗自想。
可是几乎就在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他又突然感到不安起来,仿佛有一个出乎意外和令人忧虑的想法使他吃了一惊,他心中的不安增强了,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巴卡列耶夫旅馆的入口。
“你一个人进去吧,”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说,“我很快会回来。”
“你去哪儿?我们已经到了!”
“我有事,一定得去;……过半个钟头回来……你去跟她们说一声。”
“随你的便,我跟你一道去!”
“怎么,你也想折磨我吗!”他突然高声叫嚷,目光中流露出痛苦的愤怒和绝望的神情,使拉祖米欣感到毫无办法了,有一会儿工夫,拉祖米欣站在台阶上,阴郁地望着他朝他住的那条胡同的方向大步走去,最后,他咬紧了牙,攥紧了拳头,发誓今天就去找波尔菲里,像挤柠檬样把他挤干,于是上楼去安慰因为他们久久不来,已经感到焦急不安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
拉斯科利尼科夫来到他住的那幢房子的时候,他的两鬓已经湿透了,呼吸也感到困难了,他急忙上楼,走进自己那间没有上锁的房间,立刻扣上门钩,然后惊恐地,发疯似地冲到墙角落,墙纸后面藏过东西的那个窟窿那里,把手伸进去,很仔细地在窟窿里摸了好几分钟,把墙纸上的每个皱褶,每个隐蔽的地方都一一检查了一遍,也没找到,这才站起来,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刚才已经走近巴卡列耶夫旅馆的台阶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不知有件什么东西,一条表链,一个领扣,或者甚至是老太婆亲手做过记号的一张包东西的纸,当时可能不知怎么就掉出来,掉进哪儿的一条裂缝里,以后却突然作为一件意想不到和无法反驳的物证,摆在他的面前。
他站在那儿,仿佛陷入沉思似的,一丝奇怪的,屈辱的,几乎毫无意义的微笑掠过他的嘴角,最后他拿起制帽,轻轻地走出房门,他心乱如麻,若有所思地下楼,来到了大门口。
“那不就是他吗!”一个响亮的声音叫喊道;他抬起了头。
管院子的站在自己的小屋门口,正在向一个身材不高的人直指着他,看样子那人像是个小市民,身上穿的衣服仿佛是件长袍,还穿着背心,远远看去,很像个女人,他戴一顶油污的制帽,低着头,好像是个驼背,看他那皮肤松弛,布满皱纹的脸,估计有五十多岁;他那双浮肿的眼睛神情阴郁而又严厉,好像很不满意的样子。
“有什么事?”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到管院子的人跟前,问道。
那个小市民皱着眉头,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不慌不忙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随后转过身去,一言不发,就走出大门,到街上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拉斯科利尼科夫大声喊。
“刚刚有个人问,这儿是不是住着个大学生,并且说出了您的名字,还说出了您住在谁的房子里,这时候您下来了,我就指给他看,可他却走了,您瞧,就是这么回事。”
管院子的也觉得有点儿莫名其妙,不过并不是十分惊讶,稍微想了一下,就转身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去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跟在小市民后面,出去追他,立刻看到他正在街道对面走着,依然不慌不忙,步伐均匀,眼睛盯着地下,仿佛在思考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不久就追上了他,不过有一会儿只是跟在他后面,最后走上前去,和他并排着走,从侧面看了看他的脸,小市民立刻看到了他,很快打量了他一下,可是又低下眼睛,他们就这样并排走着,一言不发。
“您跟管院子的……打听我了?”最后拉斯科利尼科夫说,可是不知为什么,声音很低。
小市民什么也不回答,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两人又不说话了。
“您是怎么回事……来打听我……又不说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声音中断了,不知为什么不愿把话说明白。
这一次小市民抬起眼来,用恶狠狠的,阴郁的目光瞅了瞅拉斯科利尼科夫。
“杀人凶手!”他突然轻轻地,然而说得十分明确,清楚……
拉斯科利尼科夫在他身旁走着,他的腿突然发软了,背上一阵发冷,有一瞬间心也仿佛停止了跳动;随后又突然怦怦地狂跳起来,好像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就这样并肩走了百来步,还是完全默默不语。
小市民不看他。
“您说什么……什么……谁是杀人凶手?”拉斯科利尼科夫含糊不清地说,声音勉强才能听到。
“你是杀人凶手,”那人说,每个音节都说得更加清楚,也说得更加铿锵有力了,而脸上仿佛露出充满敌意的,洋洋得意的微笑,又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苍白的脸和目光呆滞的眼睛直瞅了一眼,这时两人来到了十字路口,然后小市民往左转弯,头也不回地走到一条街道上去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却站在原地,好长时间望着他的背影,他看到那人已经走出五十来步以后,回过头来望了望他,他仍然一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那久远的距离根本不可能看清楚,可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好像觉得,这一次那人又冷冷地,十分憎恨地,洋洋得意地对他笑了笑。
拉斯科利尼科夫双膝簌簌发抖,仿佛冷得要命,有气无力地慢慢转身回去,上楼回到了自己那间小屋,他摘下帽子,把它放到桌子上,一动不动地在桌边站了约摸十分钟的样子,随后浑身无力地躺到沙发上,虚弱地轻轻哼着,他的眼睛闭着,就这样躺了大约半个小时。
他什么也不想,就这样,一些想法,或者是某些思想的片断,一些杂乱无章,互不相干的模糊印象飞速掠过他的脑海:一些还只是他在童年时看见过的人的脸,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见过一次,从来也没再想起过的人的脸;B教堂的钟楼,一家小饭馆里的台球桌,有个军官在打台球,地下室里一家烟草铺里的雪茄烟味,一家小酒馆,后门的一条楼梯,楼梯很暗,上面泼满污水,撒满蛋壳,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星期天的钟声……这些东西不停地在脑海中变换着,像旋风般旋转着,有些东西他甚至很喜欢,想要抓住它们,但是它们却渐渐消失了,他心里感到压抑,不过不是很厉害,有时甚至觉得这很好,轻微的寒颤渐渐消失,这也几乎让他感到舒适。
他听到了拉祖米欣匆匆的脚步声以及他说话的声音,闭上眼,假装睡着了,拉祖米欣打开房门,有一会儿工夫站在门口,似乎犹豫不决,随后他轻轻地走进屋里,小心翼翼地走到沙发前,听到娜斯塔西娅低声说:
“别碰他,让他睡够了;以后他才想吃东西。”
“好的,”拉祖米欣回答。
他们两人小心翼翼地走出去,掩上了房门,又过了半个钟头的样子,拉斯科利尼科夫睁开眼,把双手垫在头底下,仰面躺着……
“他是谁?这个莫名其妙钻出来的人是谁?那时候他在哪儿,看到过什么?他什么都看到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他站在哪儿,是从哪里观看的?为什么只是到现在他才从地底下钻出来?他怎么能看得见呢,……这可能吗?……嗯哼……”拉斯科利尼科夫继续想,身上一阵阵发冷,一直在发抖,“还有尼古拉在门后拾到的那个小盒子:这也是可能的吗?物证吗?只要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埃及金字塔那么大的罪证!有一只苍蝇飞过,它看到了!难道这可能吗?”
他突然怀着极端恶劣的心情感觉到,他是多么虚弱无力,的确虚弱得厉害。
“我应该知道这一点,”他苦笑着想,“我怎么敢,我了解自己,我有预感,可是我怎么竟敢拿起斧头,用血玷污我的双手呢,我应该事先就知道……唉!我不是事先就知道了吗!……”他绝望地喃喃低语。
有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呆呆地只想着那一点:
“不,那些人不是这种材料做成的;可以为所欲为的真正统治者,在土伦击溃敌军,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忘记留在埃及的一支部队,在进军莫斯科的远征中白白牺牲掉五十万人的生命,在维尔纳说了一句语意双关的俏皮话,就这样敷衍了事;他死后,人们却把他奉为偶像,……可见他能为所欲为,看来这些人不是血肉之躯,而是青铜铸就的!”
突然出现的另一个想法几乎使他大笑起来:
“一边是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另一边是一个可恶的十四等文官太太,一个瘦弱干瘪的小老太婆,一个床底下放着个红箱子,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这二者相提并论,那便是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吧,他怎么会容忍呢!……他岂能容忍!……美学不容许这样,他会说:‘拿破仑会钻到’老太婆,的床底下去?唉!废话!……”
有时他觉得自己好像在说胡话:他陷入了热病发作时的状态,心情兴奋极了。
“老太婆算什么!”他紧张地,感情冲动地想,“老太婆,看来这也是个错误,问题不在于她!老太婆只不过是一种病……我想尽快跨越过去……我杀死的不是人,而是原则!原则嘛,倒是让我给杀了,可是跨越嘛,却没跨越过去,我仍然留在了这边……我只会杀,结果却发现,就连杀也不会……原则?不久前拉祖米欣这个傻瓜为什么在骂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勤劳的人和做买卖的人;他们在为‘公共的幸福,工作……不,生命只给了我一次,以后永远不会再给我了:我不愿等待’普遍幸福,我自己也想活着,不然,最好还是不要再活下去了,我只不过是不愿攥紧自己口袋里的一个卢布,坐等‘普遍幸福,的到来,而看不见自己的母亲在挨饿,说什么’我正在为普遍的幸福添砖加瓦,因此我感到心安理得,哈……哈!这是什么理论?要知道,我总共只能活一次,我也想……唉,从美学的观点来看,我是一只虱子,仅此而已,”他补充说,突然像疯子样哈哈大笑起来,“对,我当真是一只虱子,”他接着想,幸灾乐祸地想与这个想法纠缠不休,细细地分析它,玩弄它,拿它来取乐,“单就这一点来说,我就是一只虱子,因为第一,现在我认为我是只虱子;第二,因为整整一个月来,我一直在打搅仁慈的上帝,请他作证,说是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肉体上的享受和满足自己的淫欲,而是有一个让人感到高兴的崇高目的,……哈……哈!第三,因为我决定在实行我的计划的时候,要遵循尽可能公平合理的原则,注意份量和分寸,还做了精确的计算:在所有虱子中挑了一只最没有用处的,杀死了它以后,只从她那儿拿走为实现第一步所必须的那么一点点钱,不多拿,也不少拿(那么剩的钱就可以按照她的遗嘱捐给修道院了,哈……哈!)……因此我彻头彻尾是一只虱子,”他咬牙切齿地补上一句,“因此,也许我本人比那只给杀死的虱子更卑鄙,更可恶,而且我事先就已经预感到,在我杀了她以后,我准会对自己这么说!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恐惧能与这个相比吗!噢,下流!噢,卑鄙!……噢,我对‘先知,是怎么理解的,他骑着马,手持马刀:安拉吩咐,服从吧,’发抖的,畜生!先知,说得对,当他拦街筑起威—力—强—大的炮垒,炮轰那些无辜的和有罪的人们的时候,连解释都不解释一下!服从吧,发抖的畜生,而且,不要期望什么,因为这不是你的事!……噢,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我决不会宽恕那个老太婆!”
他的头发都被汗湿透了,发抖的嘴唇干裂了,呆滞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天花板。
“母亲,妹妹,以前我多么爱她们啊!为什么现在我恨她们呢?是的,现在我恨她们,能感觉到憎恨她们,她们待在我身边,我就受不了……不久前我走近前去,吻了吻母亲,我记得……我拥抱她,心里却在想,如果她知道了,那么……那时我会告诉她吗?我倒是会这么做的……嗯哼!她也应该像我一样,”他补上一句,同时在努力思索着,似乎在和控制了他的昏迷状态搏斗,“噢,现在我多么憎恨那个老太婆啊!看来,如果她活过来的话,我准会再一次杀死她!可怜的莉扎薇塔!她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进来呢!……不过,奇怪,为什么我几乎没去想她,就像我没有想到要杀死她似的?莉扎薇塔?索尼娅!两个可怜的,温顺的女人,都有一双温顺的眼睛……两个可爱的女人!……她们为什么不哭?她们为什么不呻吟呢?……她们献出一切……看人的时候神情是那么温顺,……索尼娅,索尼娅!温顺的索尼娅!……”
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觉得奇怪,他竟记不起,怎么会来到了街上,已经是晚上,时间很晚了,暮色越来越浓,一轮满月越来越亮;但不知为什么,空气却特别闷热,人们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着;有一股石灰味,尘土味和死水的臭味混合一起的味道,拉斯科利尼科夫在街上走着,神情阴郁,满腹忧虑:他清清楚楚记得,他从家里出来,是有个什么意图的,得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且要赶快去做,可到底要做什么哩,他却忘了,突然他站住了,看到街道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人,正在向他招手,他穿过街道,朝那人走去,但是那个人突然若无其事地转身就走,低下头去,既不回头,也不表示曾经招手叫过他,“唉,算了,他是不是招呼过我呢?”拉斯科利尼科夫想,可是却追了上去,还没走上十步,他突然认出了那个人,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个人就是刚刚遇到的那个小市民,还是穿着那样一件长袍,还是那样有点儿驼背,拉斯科利尼科夫远远地跟着他;心在怦怦地跳;他们折进一条胡同,那个人一直没有回过头来,“他知道我跟着他吗?”拉斯科利尼科夫想着,那个小市民走进一幢大房子的大门里去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赶快走到大门前,张望起来:那人是不是会回过头来,会不会叫他呢?那个人穿过门洞,已经进了院子,突然回过头来,又好像向他招了招手,拉斯科利尼科夫立刻穿过门洞,但是那个小市民已经不在院子里了,这么说,他准是上第一道楼梯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跑过去追他,真的,楼上,隔着两层楼梯,还能听到均匀的,不慌不忙的脚步声,奇怪,这楼梯好像很熟!瞧,那就是一楼上的窗子:月光忧郁而神秘地透过玻璃照射进来;瞧,这就是二楼,啊!这不就是那两个工人在里面油漆的那套房子吗……他怎么没有立刻就认出来呢?在前面走的那个人的脚步声消失了:“这么说,他停下来了,要么是在什么地方躲起来了,”这儿是三楼,要不要再往上走呢?那里多静啊,甚至让人害怕……不过他还是上去了,他自己的脚步声让他感到害怕,心慌,天哪,多么暗啊!那个小市民准是藏在这儿的哪个角落里,啊!房门朝楼梯大敞着;他想了想,还是走了进去,前室里很暗,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好像东西都搬走了;他踮着脚尖轻轻地走进客厅:整个房间里明晃晃地洒满了月光;这里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几把椅子,一面镜子,一张黄色的长沙发,还有几幅镶着画框的画,一轮像铜盘样月亮径直照到窗子上,“这是由于月亮的关系,才显得这么静,”拉斯科利尼科夫想,“大概现在它正在出一个谜语,让人去猜,”他站在那儿等着,等了好久,月亮越静,他的心就越是跳得厉害,甚至都跳得痛起来了,一直寂静无声,突然听到一声干裂的声音,仿佛折断了一根松明,一切又静下来了。
一只醒来的苍蝇飞着猛一下子撞到玻璃上,好像抱怨似地嗡嗡地叫起来,就在这时,他看出了,墙角落里,一个小橱和窗户之间,似乎一件肥大的女大衣挂在墙上,“这儿为什么挂着件大衣?”他想,“以前这儿没有大衣呀……”他悄悄走近前去,这才猜到,大衣后面可能躲着一个人,他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掀开大衣,看到那儿放着一把椅子,这把放在角落里的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太婆,佝偻着身子,低着头,所以他怎么也看不清她的脸,不过,这是她,他在她面前站了一会儿:“她害怕了!”他心想,悄悄地从环扣上取下斧头,抡起斧头朝她的头顶猛砍下去,一下,又一下,可是奇怪:砍了两下,她却连动都不动,好像是木头做的,他觉得害怕了,弯下腰去,凑近一些,仔细看看;可是她把头往下低得更厉害了,于是他俯下身子,完全俯到地板上,从底下看了看她的脸,他这一看,立刻吓呆了:老太婆正坐在那儿笑呢,……她止不住地笑着,笑声很轻很轻,几乎听不见,而且她竭力忍着,不让他听到她在笑,突然,他好像觉得,卧室的门稍稍开了一条缝,那里似乎也有人在笑,他简直要发疯了:使出全身的力气,猛砍老太婆的脑袋,但是斧头每砍一下,卧室里的笑声和喃喃低语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而且越来越清楚了,老太婆更是哈哈大笑,笑得浑身抖个不停,他转身就跑,但穿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楼梯上一扇扇房门全都大敞开来,楼梯平台上,楼梯上,以及下面……到处站满了人,到处人头攒动,大家都在看,……可是都在躲躲藏藏,都在等着,一声不响!……他的心缩紧了,两只脚一动也不能动,好像在地上扎了根……他想高声大喊,这时他却醒了。
他很吃力地喘了口气,……可是奇怪,梦境仿佛仍然在继续:他的房门大开着,门口站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正在凝神细细地打量着他。
拉斯科利尼科夫还没完全睁开眼,就又立刻把眼闭上了,他仰面躺着,一动不动,“这是不是还在作梦呢,”他想,又让人看不出来地微微抬起睫毛,看了一眼,那个陌生人还站在那儿,仍然在细细打量他,突然,他小心翼翼地跨过门坎,谨慎地随手把房门掩上,走到桌前,等了约摸一分钟光景,……在这段时间里一直目不转睛地瞅着他,……于是轻轻地,一点儿响声也没有,坐到沙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把帽子就放在身旁的地板上,双手撑着手杖,下巴搁在手背上,看得出来,他是装作要长久等下去的样子,透过不停眨动的睫毛尽可能细看,隐约看出,这个人已经不算年轻,身体却还健壮,留着一部浓密的大胡子,胡子颜色很淡,几乎是白的……
约摸过了十来分钟,天还亮着,但暮色已经降临,屋里一片寂静,就连楼梯上也听不到一点声音,只有一只大苍蝇嗡嗡叫着,飞着撞到窗户玻璃上,最后,实在让人受不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欠起身来,坐到沙发上。
“喂,您说吧,您有什么事?”
“我就知道您没睡,只不过装作睡着了的样子,”陌生人奇怪地回答,“请允许我自我介绍: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