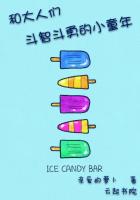蒙古民族千年以来已经形成一套极其适应游牧生活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只要拥有自己的畜群,游牧民几乎可以得到生存下去的所有的必需生活资料,而这种“肉为食,酪为浆”的生活,完全仰赖于安身立命的畜群。
在蒙古高原这片土地上,距今1.4万年至6000年前——中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驯服野生食草动物,即将野马驯化为家马、野牛驯化为家牛、野驼驯化为家驼、野山羊或盘羊驯化为家养的山羊、绵羊。
蒙古民族饲养的牲畜为传统“五畜”:蒙古马、蒙古牛、蒙古双峰驼、蒙古山羊和蒙古绵羊。
蒙古马
蒙古马是独立起源的古老马品种之一。现代蒙古马为乘、奶、肉兼用品种。蒙古马奶的营养丰富,具有保健和医疗作用。蒙古马抓膘快、掉膘慢,即使遇到“白灾”(冬春降雪覆盖牧草,牲畜无法采食,冻饿瘦弱死亡),也会刨雪采食,安全过冬。蒙古马对毒草有很高的鉴别力,很少中毒,抗病力很强。蒙古民族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于世。牧马是蒙古男子职守所在,牧马人在牧民中备受尊重。当年成吉思汗大军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蒙古马这种吃苦耐劳、推进迅速的代步工具,从而形成了其长途奔袭为主的运动战术,得到直逼欧洲列国,成就蒙古帝国的伟业。面对茫茫草原,无马代步根本寸步难行。在日常生活中,其游牧迁徙和走亲访友,都需要马匹代步。也因此有蒙古族的孩子自出生就会骑马的说法,在草原上三四岁的幼童即被扶上马背,十来岁的孩子即会骑马,完成人生中一个重要的仪式,标志着已经成年。在他跨上马背的那一刻,那剽悍骏马的身影已经融入他的血脉,注定了他终将成为马背上的骄子。草原上的牧人在马鞍上度过一生,马背生活塑造了他们独立、自信、勇敢的品格。蒙古马是蒙古人的精神信仰和寄托。
蒙古牛
根据考古学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8000年前),在亚洲的中部,蒙古牛由野牛驯化成家牛。蒙古牛广泛分布在中亚、东亚(包括中国的北方地区)、蒙古国和俄罗斯贝加尔湖周边地区。从外形特征看,蒙古牛胸深、体矮、胸围大,具有乳、肉兼用型的体征。草原上的蒙古牛多为终年放牧,无须棚圈和补饲。蒙古牛的主要特性可概括为耐粗饲、宜放养、抓膘快、适应性强(如抗寒抗热的温度区域在零下50℃至35℃之间)、抗病力强、肉的品质好、生产潜力大等特点。蒙古牛也是草原上重要交通工具勒勒车的拉载者,同时,也为蒙古民族提供肉食和丰富的奶制品。蒙古地区冬季高寒,游牧民通过多年的经验,以从牛奶中提取的奶油获得需要的热量。
同时,草原上不同的地域也存在着以牛奶为原料的不下几十种奶制品,酸奶、奶皮子、奶干、奶疙瘩和奶豆腐等,琳琅满目,品种繁多。
蒙古双峰驼
蒙古骆驼属于双峰骆驼(阿拉伯和非洲是单峰骆驼)。据考古学家、生物学家考证,骆驼科动物是距今约3000年前北美洲的原偶蹄类演化而来(即“二趾原驼”进化为“原驼”)。在蒙古高原,大约在3000—4000年前,对野生骆驼进行驯化。中国甘肃嘉峪关西北匈奴早期的文化遗物“黑山浮雕像”保留了许多骆驼和游牧人的石像,足以证明内蒙古阿拉善是双峰骆驼最早的驯化地之一。蒙古双峰驼的主要特点,除了乳、肉、绒等生产性能外,主要功能是作为长途运输工具且被广泛使用。蒙古双峰驼具有耐饥、耐渴、耐风沙、能负重,善于行走戈壁和沙漠的特点。目前,由于经济价值低,很多地区已经难得再见到蒙古双峰驼矫健的身影,近年存栏数锐降,目前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阿拉善等仍有饲养,呼伦贝尔草原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在迁徙营地时,仍然以骆驼为主要使役对象。
蒙古山羊
根据记载,山羊约在公元前7000—公元前6000年,起源于南亚、西亚、南非。目前山羊发展到140多个品种。蒙古山羊是从亚洲山羊演变过来的独立的品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内蒙古地区和蒙古国。蒙古山羊以它的用途分为肉用、绒用、奶用、皮用、羔皮用和地方品种等六个分类。蒙古山羊是一种优良的地方品种,是皮、绒、肉、乳兼用型的山羊品种。
蒙古绵羊
蒙古绵羊是蒙古高原的一个古老家畜品种。据科学家推测,野生盘羊可能是蒙古绵羊的先祖或先祖亲缘。大概在6000年前,蒙古高原已有了驯化的蒙古绵羊。现代蒙古肥尾羊在2000多年前已形成。蒙古绵羊的分布很广,同蒙古牛的分布区域大致相同。蒙古绵羊的基本外貌特征表现为:体质结实、鼻梁隆起,公羊多有角,毛质较粗,体毛多为白色,头、颈、四肢多有黑色或褐色斑点,尾大而肥。蒙古绵羊肉质细嫩,色味鲜美,营养成分高。放牧行走快,游牧采食力强,抓膘快,每日骑马放牧可走30—40里;大雪天扒雪吃草,生存力强;全年羊群多在露天草场卧盘;在冬季大风雪时,西北方向设简易风障即可过夜。蒙古绵羊具有耐渴的特点,秋季抓膘时,可采取走“敖特尔”野营放牧,可几天乃至十几天不需饮水,只要能采食野葱、野韭、瓦松和黄芪等多汁牧草,就可达到解渴和增膘的双重效果。
在这五畜之中,饲养品种因所在的地域而略有不同,但毫无疑问,绵羊,这上帝之子,是所有的游牧家庭中必须饲养的,它们为蒙古游牧民提供肉食、皮张,它们的奶制品也可以作为牛产奶接替不上的重要补充。
这是我在到达一个营地时拍到的,一只刚刚降生不久的羔羊窒息,牧民在为它嘴对嘴做人工呼吸。
在此时,恐怕牧人们不会考虑到会患上布氏病(即布氏杆菌病,又称波状热,是由布氏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其临床特点为长期发热、多汗、关节痛、睾丸炎、肝脾肿大等)这种危险,他们只是急着让这羔羊恢复生命。到我离开的时候,那只羔羊终于开始呼吸了。
在这五畜之中,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就是绵羊。
绵羊是牧民的生存基础。
牧民的富裕与否完全取决于羊群是否安好,这也是一旦发生白灾、黑灾(一般在牧区11月至12月初冬时,由于河湖、水泡冻结,无降雪或积雪少,牲畜无水可饮,无雪可食,因缺水而死)、旱灾、湿雪、冷雨、暴风雪、病灾、火灾、鼠害、风灾、雹灾、水灾、毒草、虫害等灾害,牧民往往会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的原因。
还有就是草原上千年以来从未被灭绝的狼害。
以呼伦贝尔草原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狼群很多,少则几十只结成一群,多则可达近百只。因此草原也出现过全盟全旗的群众性打狼运动。
这里一个小小的数据可以看出狼害对畜牧业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至1998年的50年内,由于狼害损失牲畜累计32161头(只),同时打狼除害大约16974只,其中仅在1953年一年内即打狼346只。”(《陈巴尔虎畜牧史》,莫希格编著)
其中没有提到牧羊犬捕杀了多少狼。
我想,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牲畜是游牧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而穷凶极恶的狼群是除了病害之外牲畜最大的威胁,牲畜受到侵害将直接影响到牧民的生活,上溯到并不遥远的年代,牲畜的兴旺与否将直接决定一个部落的兴衰存亡。
草原广阔无际,游牧民居无定所,追逐水草丰美之地,居住便于移动安装的蒙古包。
而牲畜白天在丰美的草场牧放,夜晚幕天席地,休憩于毡包附近的草原之上,没有任何圈棚保护。
保护这些牧民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完全依靠蒙古牧羊犬。每当夜幕降临,它们三两伏卧于畜群的外围,尽职尽责地守卫整个畜群。慑于牧羊犬的凶猛,狼群尽量远远地避开牧人的营地。但在最严酷的隆冬季节,在荒寒的草原上找不到果腹之物的狼群也会倾巢而出,结群攻击营地,抢掠羊只。于是,在冬日里,牧羊犬与狼群的厮杀几乎是持续整个夜晚的。有时,撕咬在一起的牧羊犬和狼翻滚撞击到蒙古包的毡壁上嘭嘭作响。这种搏杀直到天色将明,撕咬咆哮声才随着无奈离去的狼群而渐渐淡去。天亮之后,牧人走出毡包时,雪地上遍布牧羊犬与狼搏杀时留下的印记,一片狼藉,但畜群无一损失,而营地无畏的护卫者——牧羊犬正卧在冰雪之中舔舐自己在一夜的争斗中留下的伤口,看到主人,毫无倦意,一跃而起,到主人的身边问好。有时雪地上也会留下七零八碎的狼的尸体残块,当然,偶尔倒下的也会是牧羊犬。
这不过是草原生活中最普通的一幕。其实在这里,并不存在人类世界中道德意义上的划分,正义者或邪恶者,狼为了食物,为了生存,牧羊犬为了保卫营地。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只有最强壮凶悍的个体才能存活下来,狼群也在悄然间对蒙古牧羊犬的自然淘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节选我最近刚刚完成的一篇小说的一部分,诠释草原、牧人、牧羊犬和狼之间的关系。
在这无边的草原上,营地真正来自人类的威胁微乎其微。
令牧人头痛的仍然是羊群恒久的敌人——狼。
这个冬天,不知道为什么,往年总是随着第一场落雪而来的漫山遍野的黄羊群并没有出现在草原上。
狼族冬天稳定的食物贮备就这样消失了。
在这个食物链被撕裂的最初的日子里,它们以捕食野兔之类的小兽果腹,挺过了一段时间。在又一场暴雪从天而降之后,它们就找不到任何食物了。冬天的草原如此贫瘠,狼族体内贮存的最后一些油脂也被这严寒搜刮殆尽,它们瘦得弓腰瘪肚,浑身的骨头都支棱出来。为了生存,它们开始吞食那些更加虚弱的同伴。
但靠吞食同类,它们挨不过漫长的冬天。
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们将目光投向草原上牧人的营地,那里有肥美的羊只。更多的时候,它们懂得与人类在草原上共生的最基本的法则,就是相安无事,互不侵犯。它们十分清楚人类拥有可以瞬间攫取它们生命的武器。
但是,此时如果再不袭击人类的羊群获得食物,它们的种族就有灭绝的危险。活下去的热望压倒一切,冥冥中牧人与狼共同遵守的法则也就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了。
活着,就意味着一切。获得食物,到了春天,狼群里就会有新的生命降生,那时,这个已经行将末路的族群又会繁盛起来。
这是冬日最后的疯狂。布勒的营地是它们最后的机会,是否能够获得食物将决定着它们的生存。在多日品尝自己同类干瘪的皮肉之后,它们急于换换口味,用肥美的羊肉填充干瘪的肚囊。
它们伏卧在山顶向阳的坡侧,俯视着冒起炊烟的营地,耐心地等待。当夜色降临时,它们就悄然无声地开始逼近营地。
它们太瘦了,在明亮的月光下,像一些轻飘的影子滑过雪地,蹦跳着前进。
没有任何牧人敢于小视冬日里饥饿狼群的实力。在这样的冬天,很多牧人往往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所有的羊只都被咬翻在地。狼吃不了那么多羊,但在进入羊群之后,本能驱使着它们像魔鬼一样不断地杀戮。
最初的几个夜晚,听到外面的撕咬声,布勒还拎着布鲁棒子(草原上一种传统武器,榆木棒一端包铅并缀铜块)钻出毡包准备为哈拉助势。但是,站在黑暗的营地里,一片纷乱之中,他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发现人类出现,狼群迅速退入黑暗之中,但是,只要布勒刚刚进入毡包,它们又开始骚扰营地。就这样,它们反复地挑战着牧人的耐心。
索性,布勒不再走出毡包。
到了早晨,布勒清点羊群,发现不但没有损失羊只,营地上还会留下一两具狼被撕碎的尸体,而哈拉身上仅仅留下几处轻描淡写的伤口。
后来,夜晚再有狼群袭击羊群,布勒就放心地大睡了。
一旦放松下来,布勒就睡得极其坦然,他那剽悍的呼噜声倒是与外面哈拉与狼群对峙的咆哮相映成趣。
即使这些狼已经穷凶极恶得连风化的骨头都想啃上一口,但哈拉无所畏惧。在这些乞讨者般的饿狼面前,哈拉显得过于粗壮,它营养充足,结实的肌肉上包裹着厚密的脂肪,更像雍容的王。
当然,要想保护营地上的羊群,仅有帝王般的气质还是不够的。
饥饿已经让狼群丧失了仅有的谨慎,它们既然已经打定主意破坏固有的禁忌,冲击人类的营地,如果不能拖着肥美的羊只离去,无论如何也不会罢休的。
狼群的先行者开始试探,它们很快就发现,这头黑色的大狗与众不同。
除去最开始它那巨硕的体形给它们造成的直观震撼外,它还拥有惊人的速度。第一头狼眨眼之间就被咬倒,不但没有反抗的机会,甚至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它们根本没有看清哈拉是怎样完成攻击的。
它们明白,这头黑色的大狗不好对付。
哈拉迅速地跳开,背倚着毡包,掌握着主动权,不让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狼群迅速地发现,与它们对峙的这头大狗,和它们见过的其他牧羊犬完全不同,除了偶尔震颤般的低吼,它并不吠叫。不像那些牧羊犬,在这种情况下只懂得闭着眼睛狂吠,幻想以此驱赶侵入者,呼唤主人出来助阵。这头牧羊犬显然不需要这些。
当它们试图吸引它到开阔的地带进行攻击时,它对它们轻佻地蹦跳的邀战和嚣张的挑衅无动于衷,甚至闲散地卧在地上,舔舐着自己爪子上的饰毛。
不过,只要它们对羊群稍有动作,它就像一道黑色的光,一掠而至。在扑杀时,它的力量和速度都要优于狼族。它的诸多表现更接近于猛兽,而不是被人类豢养的牧羊犬。
而让它们真正感到崩溃的是,这头牧羊犬似乎拥有无穷的精力,在与它周旋一番之后,狼已经开始无奈地喘息,它的呼吸却仍然平稳,没有一丝变化。
现在,哈拉已经掌握了狼群的实力,它甚至将这一切视为一种游戏。它突然跳进狼群,以自己优势的体重和石头一样坚硬的身体冲撞它们,虚张声势地扑咬,甚至有恃无恐地挑逗那些尴尬的母狼。
狼群固有的秩序被动摇了。它们发现羊群的守护者显然比它们更加强大,它们无能为力,对于是否能够完成袭击心存怀疑。
这不是牧羊犬,而是它们的天敌,是断了它们最后一丝生存希望的恶魔。
塔娜几乎整晚都无法安睡,她侧耳倾听哈拉的咆哮,它与狼撕咬相撞时铿锵的声响,与狼缠斗在一起撞击在毡包外壁上嘭嘭的响声。这种混乱的声响直到凌晨才会渐渐地淡去,营地安静下来。
她隔着毡壁听到哈拉巡视营地时爪子落地时沉硕的脚步声,终于感到安心,才沉沉地睡去。
这头牧羊犬当着我的面,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将一颗羊头咬得粉碎,吃得一干二净。可以想象其咬合的力量以及牙齿的坚硬程度。
狼群并非无所作为,它们还是在哈拉的身上留下一些伤口,这些伤口每天早晨都被塔娜用黄油小心地涂抹。而布勒制作了一个缀满钉子、尖头朝外的项圈为哈拉戴上,这样,至少在与狼撕咬的时候,致命的部位不会受到伤害。
在哈拉杀死了第四头狼之后,狼群也就放弃了继续在每个夜晚袭击这个营地的计划。
对于这个营地,它们避而远之,甚至在草原上经过时,也会绕道而行。
直到它们成功地袭击了附近的数个营地之后,对于布勒的营地,它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站在哈拉的视野范围之外,远远地观望。
对于这个营地的守护者,它们心存敬畏。
——节远自我的作品《黑狗哈拉诺亥》
当然,出现在我这篇小说里的牧羊犬确实是佼佼者,属于那真正意义上的原生种,极其凶猛。
但万事总有两面性。
牧羊犬无论如何凶猛,仍然是狗,它们的食物还是来自人类的施与,它不需要为了生存获得食物而奔波;而狼是真正意义上的野兽,它们通过捕食获得食物,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狼应该比牧羊犬具备更强的厮杀能力。
但在草原上,当狼袭击羊群时,毕竟是作为偷掠者的角色,而牧羊犬,则是背靠营地和牧人,是捍卫者。在角色上牧羊犬就占了先机,而除去一般零星的捕杀外,狼群更多在冬天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而此时的狼因为缺少食物而体力不济,牧羊犬则饱食冻馁的羔羊,膘肥体壮,以逸待劳。
一般营地上很少仅仅饲养一头牧羊犬,一般都是三四头,甚至更多,所以只要不是力量过于悬殊,牧羊犬一般不会处于劣势。
但即使如此,牧羊犬与狼的厮杀也总是互有胜负,也经常有牧羊犬葬身于狼口之下。
而那种厮杀是相当惨烈的,失败者往往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草原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年老的牧羊犬身上带着痊愈后长出白毛的伤痕,而一些刚刚驱赶过狼的牧羊犬的身上总是留下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
脸皮被撕开,头上留下瘆人的伤口,甚至被咬断腿。
而那些牧羊犬一副顺应天命的样子,卧在营地上安静地晒着太阳,目光空茫,也许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吧。
两个动物是一头狼和巴努盖。
那日苏还勉强可以辨认出那是巴努盖。
但仅仅是勉强,它身上的皮被大片地揭开,一条后腿显然已经被咬断,耷拉着,脖子几乎被撕烂了,而致命的伤是腹部那道可怕的创口,腹部被自上而下地整个撕开了,几乎所有的内脏都流淌出来。
而被巴努盖压在身下的那头大狼,被巴努盖咬住了咽喉,早就窒息了。
那日苏无法想象没有视力的巴努盖是怎样迎击这些狼的,大概是跌跌撞撞地循着气味冲过去,一口咬住那头狼之后就再也没有松过口,任由其他的狼在自己的身上任意蹂躏,撕出巨大的伤口。
巴努盖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但仍然死死地咬着那狼的咽喉。
扎布试着慢慢地掰开巴努盖的嘴,但毫无意义,似乎已经锁死了。
这是一头10个月大牧羊犬的牙齿,我曾经测量过成年牧羊犬和成年蒙古草原狼牙齿的长度,二者几乎相差无几。由于牧羊犬成长期正是春季羔羊大量死亡的时期,食物充足、钙质补充及时,牧羊犬的四颗獠牙甚至比狼的更加粗壮。
终于分开之后,从巴努盖的口中发出像古老的门扇打开时的咯咯声。
巴努盖刚刚松开嘴,白雪和丹克就咆哮着扑向那头已经死去的狼,狠狠地撕咬着。
随着它们的扯动,那日苏注意到,那狼的颈骨已经断裂,而整个脖子几乎都被巴努盖切断了,只剩后颈还有一些肉连接着。
内脏摊淌了一地的巴努盖根本没有办法直接挪动。最后,那日苏找了一条皮褥子,和扎布一起将巴努盖抬起,放在褥子上。一起放在上面的,还有巴努盖已经被冻硬的内脏。
两个人将褥子拖进了毡包。
整个夜晚,扎布用酒洗了手之后,将巴努盖脱出的内脏填回到肚腹中,又用大号的钢针将伤口缝合。
巴努盖身上的伤口太多了。当扎布终于将它身上那些大块的伤口缝合好的时候,巴努盖看起来更像一头被重新拼凑起来的狗。
在整个缝合的过程中,巴努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那日苏不时地摸摸它的脖颈,感受到动脉缓慢的律动,以确定它还活着。
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巴努盖的眼睛偶尔会眨动一下。
天快亮的时候,扎布终于缝合了最后一道伤口,他呻吟着扶着腰站了起来,整个夜晚他俯身太久了。
扎布拿起酒瓶喝了一口,然后用破布擦了擦手,就歪倒在褥子上睡着了。
昏睡中的那日苏听到了什么响动,睁开眼睛,在包顶透进的微弱的晨光中,巴努盖竟然已经站了起来。
他一阵欣喜,轻轻地唤了一声。
但巴努盖对那日苏的呼唤毫无反应。
它仅仅是站在那里,但似乎有些东西失去了,好像在它被重新组装的过程中,它已经忘记了很多事。
也许是因为身上的毛都被血浸湿了,它显得小了很多。
它的身体僵硬如木头,腿几乎是僵直地移动,板硬地慢慢地向前。它在试探着,但它知道背对着位于毡房中间炽热的火炉,但它选错了方向,当它的鼻子碰到了哈纳(即蒙古包围壁的木架,以榆、柳或杨木制成。将木料制成粗细均匀、长短一致的木棍并刨光,再将木棍烤弯,在两端和中间钻眼,用马或骆驼的生革线将木棍交叉穿结成栅栏状。每块哈纳用30根木棍,高1.5米左右,长2—2.3米。一个蒙古包需要多块哈纳)时,停了下来,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用鼻子探索着哈纳,沿着哈纳的弧形慢慢地移动。
它太累了,每移动一步,似乎都要思考很久,是否还要迈出下一步。
每一步都耗费了它所有的力气,需要积聚很久的时间才能挪出下一步。
终于,它挪到了毡包的门口,将鼻子探出毡帘后,它的身体轻轻地抽搐了一下。
那日苏正想阻止它离开毡包——现在出去很容易冻伤刚刚缝合的伤口,听到扎布用鼻子发出一个制止的声音。
原来他也醒了。
就这样,巴努盖用鼻子挑开了毡帘,钻出了毡包。
一抹青色的晨光将它笼罩其中,随后,毡帘在它的身后合拢,毡包重又归入昏暗之中。
天大亮时,那日苏出了毡房。
丹克和白雪卧在毡包前舔舐自己身上的那些细小的伤口,看到他,起了身,摇了摇尾巴,算是打招呼。但是,它们看到那日苏循着巴努盖留下的爪印往草原里走,并没有跟过来。
其实,巴努盖也没有走出多远,它的爪印几乎一直在雪地上拖行。
它卧在毡包东南一个舒缓的雪坡上,头冲着营地的方向,毛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就那样冻硬了,那日苏试着将它抱起来扛回到营地里去,但它身上流出的血已经将它紧紧地冻在地面上,结实得像被焊在那里一样。
那日苏走回营地时,扎布正在剥那头狼的皮。
那日苏从他身边走过时,他并没有抬头。
已经冻硬的狼,应该放在毡包里缓一缓,否则皮根本就剥不下来。
——节选自我的作品《狼谷的孩子》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牧羊犬也完成了自然选育的过程,那些瘦弱胆怯的个体会在这种厮杀中失败,被淘汰,留下的都是最勇猛强悍的牧羊犬,它们的基因也会因此在草原上流传下去。
从古至今,牧人无不视狼群为仇敌,一旦在草原上发现狼的踪迹,定要一追到底,杀之而后快。
近些年,狼作为野生动物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牧人手中无枪,无法击毙,不过一旦发现狼只出现,牧民总是拼命追赶,将其驱逐出自己的牧场。
不过,现在曾经广阔的草原已经不再无边了,随着草场划分,无疆域的草场已经被草库伦分割成数不清的家庭牧场。
当狼只穿越草库伦而去的时候,无论是骑马还是骑乘摩托或者开车的牧人只能无奈地看着狼悠然而去,而无法穿越草库伦继续追赶。
这是一只夜晚捕食时撞死在草库伦铁而与狼同样体形的牧羊犬却可以穿越草库丝网上的鸮,被牧人挂在上面,摆出一副殉难者的姿势。 伦,继续完成驱逐或者捕杀狼的任务。
草原牧人因而喜爱他们的牧羊犬,在草原牧民的家庭中牧羊犬具有重要的地位,牧羊犬也是在草原的牲畜中唯一拥有自己名字的牧畜。
在草原上没有出售幼犬的习惯,牧人只会将幼犬相互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