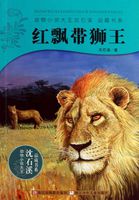想你,如急雨中挺立的芭蕉树,一脸泪痕。
想你,如破雾而来的古筝曲,凄婉,缠绵。
老屋,我又想起了你,离你愈久,相思愈是绵绵。
老屋,其实不是屋,它只是养育过父辈的一个小村,有人称老家,而我们习惯称老屋。老屋是我们一家随父亲下放回归故居停靠的一站,只是这一停便是10年。老屋为我们抵挡了10年的风雨,我们也把生命中最艰难、最难忘的一段留在了那里。
文革期间,在古云梦泽小县城当医生的父亲,受政治冲击脱下白大褂,回到祖居地府河边的老屋当了农民。从未干过农活,被老屋人尊称为“先生”的父亲,受特殊照顾,分配到了生产队放牛。在当时缺医少药的贫困乡村,拥有县城来的医生,可谓是老屋人一大幸事,几服草药,几根银针,10年间父亲无偿治愈病人无数。10年后父亲恢复工作,带着一家大小离开了揉进我们太多眷挂和屈辱的老屋。记得父亲走时,方圆几里送别的乡亲百十人之众。从乡亲们的泪眼里我读懂了父亲的崇高。10年后我由懵懂少年渐渐长大,在父亲的激励下,成为老屋人敬慕的医生、记者、作家。虽然离开老屋已经30年了,但我仍怀念老屋朴实的民风,怀念老屋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特别是那府河岸边高高低低的沟壑,它记录过我的成长。现在虽已模糊,却也无法抹去。
春天时老屋最是烂漫,花香四溢。金灿灿的油菜花盛开,看了一冬天灰白颜色的眼睛,一下子被它照亮,心也跟着明朗了起来。紧接着父亲在屋前苦心经营的草药园中芍药姗姗而来,灼灼其华,尤其在晨间,几滴露珠流转于花瓣,一派妩媚娇软之态。在叶绿得正好时,像星星一样点缀其间,越发绿得纯粹白得空灵,一同摇曳生姿,一同晶莹闪烁。
夏日的老屋夕阳如血,当晚风夹杂着泥土的清香飘过屋檐一角时,老屋终于盼来了惬意的时刻。大人们把大大小小的藤椅竹床搬到屋前的空地上,错落坐下。这个时候,劳作一天的人们摇着蒲扇,扯着家常或讲着故事,一天的劳累便随着汗珠的滚落而散尽。我们却早就坐不住了,于是踩到园子里凑近了使劲看树上的桃红了多少;看墙边的草莓长得多大了;摸黑爬上那棵老枣树看枣沙了没有……一切确认过一遍,就一头钻进黑夜里。在狭窄的乡间土路上,放肆地大叫大笑着追着萤火虫,嬉笑声回荡在老屋的半空。
儿时在老屋过中秋节别有味道,从黄昏我们就在盼望着月上柳梢头了,一家人围坐桌前,看月亮一点点爬上夜空,院子的一切便如水般清透起来。此时的我,总紧挨着父亲,听他讲述救死扶伤的故事。月上中天,老屋全村人都会聚在府河大堤上,欢歌笑语好不热闹,而我们这群小鬼便会在人群中乱穿,在堤两旁芦苇中捉迷藏,相互追逐戏耍。
如今,再也听不见父亲那娓娓的故事,再也看不到中秋堤上那涌动的人群了。只有那河岸边高高低低的沟壑依旧,只有那堤旁芦苇还郁郁葱葱。
冬去春来,岁月流逝。我们渐渐长大,老屋也随时光老去。今天的老屋建起了新村,修建了柏油马路,而老屋却在新村旁像个迟暮老人,衰朽、苍凉……
但在我记忆深处老屋就像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女,永远年轻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