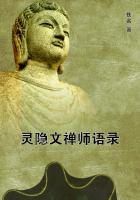思和同志:
你好!
收到你的信,格外高兴。九月杭州会议上,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事实上早就成了朋友。在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四年前,在上海《文汇报》上,你率先对拙作《“狐仙”择偶记》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此后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并因此使我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但我仍要感谢你。因为正是那场争论,使我的作品扩大了读者面,也使我自己增长了见识,世间的事原来这般有趣。
我以《卖驴》起步,至今在文坛上已走了四年多,长篇、中篇、短篇,乃至微型小说,都作了尝试,共发表了六七十万字。按速度不算太慢,然而惭愧,作品多属平庸,自然也就没有在文坛上“走红”。好在我还沉得住气。我一直在走着一条孤独的路,惯了。
说实话,发表作品之前,我并非不想投师。但不可能。我那地方四省交界,太偏僻,环境迫使我只能靠自己。我已经习惯于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斑斓的尘世,用自己的脑袋领悟人生的道理。除了读书,我最喜欢一个人坐在那里纳闷,那实在是一种享受。人做什么会受到限制,而想什么却是自由的。想想好笑,便独自笑了;觉得可恶,便发一通脾气;感到可悲,便红了眼圈,一个人在那里汹涌着感情。我曾担心,这样下去会弄出神经病来。据说,文坛是个热闹的去处,而我却独自在荒野里踯躅,会有个什么结果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钟山》的一位老编辑,他沉思良久,只说了一句话:“文坛的事,知道也好,不知道更好。”这位老编辑当年和赵树理是至交,他本人历经磨难。我知道他的经历,也就掂出了这话的分量。就这一句话,我把他看作恩师。可惜他已不幸去世了。
当然,我并没有打算与世隔绝。事实上,我每年都出去二三趟,看看听听,心中有数。我仍要走自己的路。
我脚下是一块沉重的土地,我无法写轻的作品。我喜欢凝重的东西,比如铁块、石头和黑色的土壤。但我又怕读者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作品中又常有些幽默,尽管有些是流泪的幽默。回顾自己的作品,大致不外写人生、人性、人情、人道、人格。我还会继续写这些东西。但一年多来,我有些不满足了。总感到一种莫名的东西在左右我的情绪。八四年春天考入鲁迅文学院以后,这种莫名的感觉愈发强烈。置身于繁华的京城,到处都有现代文明的诱惑。但我却陷入深深的孤独。不知为什么,反而那么强烈地思念旷野。我相信,这决不是一个乡下人不能享受现代文明,而实在说,我可怜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他们什么都不缺,独少了大自然的恩惠。那么喧嚣,那么拥挤,天空那么混浊,月亮昏昏的,连太阳都不够光艳,人在这里,怎么受得了呢?但人们生活得极其愉快。他们看乡下人的目光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我愈发觉得悲哀,也就愈发想往大自然。
八五年夏天,趁学院放假期间,我带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在乡下跑了二千里路。从家乡的苏北出发,经皖北,入豫东,转道鲁西南,对黄河故道进行实地考察。我一直在写黄河故道,我不能不看它,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而又屡屡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河,究竟是一副什么形态。沿河走去,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摇撼得厉害。黄河确是一条伟大的河。故道虽已破败,但那空阔、辽远的气势仍叫人惊心动魄。我分明感到这里埋着一部辉煌的史诗。那史诗沉睡在地下,透过厚厚的黄土,发出一种放射波,我感觉到了!历史上,黄河曾决口一千九百多次,每一次决口,都使大片大片的土地变成泽国。而每一次决口之后,紧随而来的又必定是乱兵、土匪、杀戮和饥饿。当然,人并没有因此而灭绝,而是一次次地站起来重建家园。我真是感叹中华民族的再生能力。但随着思维的延伸,我同时又在想,黄河老是决口,是不是因为人过于贪婪,把森林砍伐得太厉害了?人和大自然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包括今天“为人类造福”之类的口号是否有极大的狭隘性?科学和技术究竟会把人类引向何处?如此等等。竟是越想越觉得不妙。也忽然明白,一年多来那种莫名的悲凉感是什么了。
显然,人不能退回蒙昧去,必然会走向更高的文明层次。但如果不清醒,“现代文明”给人类的威胁将远比黄河决口大得多。我宁愿以偏激的观点表现这种担心。《那原始的音符》就是一次探索。今后一段时间,我可能还会写一点这类作品,并恳望听到你的意见。
顺颂
撰安
赵本夫
1985.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