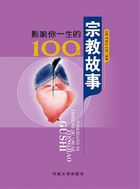刘舆去世的噩耗传到晋阳,刘琨因公不能奔丧,更加多愁善感,郁郁寡欢。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怎样排遣?哥哥在他的仕途上给予了很多的呵护,而他却没能给大晋一个强盛的并州。卢谌去拓拔那里也不少时日了,尚无音讯。他产生出一种事态不可把握的悲怆,把军事交给令狐盛,政事交由徐润。他无聊地与青荷她们欢歌曼舞,麻木着自己。
石若兰对刘琨心系洛阳家人的事情,虽说暗暗为他操心,也时常和他探讨音律,但感情上总是若即若离。她明白自己的处境。她和小婉常跟桃花去民间治病,有时也去红楼长歌。
这天,石若兰和桃花她们一道出诊。在一户人家,躺在炕头上的老人瘦得皮肤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皱纹,他抬手哆哩哆嗦地指一指炕沿:“姑娘,你们坐吧,喝口水。”
这个家只有两间破房,屋子看上去空无一物,锅台上的几斤豆子,在一个发黑的布袋里,金光闪闪似的。他的儿子女儿和刚几岁的孙子,像一群燕子一样,齐刷刷地站在屋里地上。
老人说:“姑娘,行行好,我家没什么营生,看不起病,儿子打仗伤了腿……”
老人得了痢疾,是吃野菜吃的。桃花给他留下了中药,安慰说:“你放心吧,我们不给你要钱的,刘大人交代过,我们出来不挣钱的。”
老人感谢说:“真不好意思,你们也不在我家坐会儿。”
石若兰道:“我们没事的,你好好养病吧。”
老人道:“刘大人爱民如子,老夫没齿难忘啊。”
石若兰目睹这样的场景,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这要是在十多年前的金谷园,她不可能相信一般人家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现在和桃花一起走街串户,每天面对的就是如此悲惨的一幅幅场面。再回忆起金谷园的生活,体会到活着的真实滋味。她倒是愿意天天这样,为苦难的人做一点善事。
街上,一阵吵闹声吸引她们凑了过去。原来是几个百姓和两名军士争执。石若兰认得,其中有个当官的叫令狐泥。
只听一人说:“你凭啥抓我们?”
令狐泥盛气凌人地道:“嘿,小子,还不服气呀。你服了劳役咋着,就有功啦,本官现在让你服兵役你就得去。”
那人据理争辩道:“你们说的服一年劳役免一年兵役,为何出尔反尔?”
令狐泥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告诉你丁全儿,你们几个乖乖的跟我走算是没事,不然的话,株连全家。”
丁全儿说:“走,我们找徐大人评理去。”
令狐泥哼一声,说道:“你小子胆子不小哇,敢顶嘴。给我打二十军棍。”
他旁边的士兵举棍就打。和丁全儿一道的人纷纷鸣不平。
令狐泥得意地道:“你们也一样,来跟着我干没错,有吃有喝,将来升官发财,娶媳妇。”
丁全儿哀求说:“大人,你饶了我们吧。”
令狐泥指着他们的脸骂:“你们简直是愚蠢至极。国家正当危难,你们却畏缩不前,该当何罪,带走!”
丁全儿等人急了,跟令狐泥他们厮打起来。这时,晋阳府的几名衙役过来了。石若兰她们方匆促离去……
徐润接了晋阳府的事,忙得不亦乐乎。此时,他正坐在堂上翻案卷,衙役张三娃来报。“大人,不好了,街上有人滋事。”
徐润眼皮抬上一下,责怪道:“什么呀,街上滋事这等小事也来报告本官,你自行处置。”
张三娃答:“报告大人,小的不敢。”
徐润怒责道:“连个滋事的人都治不了,还要你们何用?”
张三娃答:“大人,此人非一般贫民,他是……”
徐润不容属下说下去,道:“不管他是什么人,一律拿来是问。”
张三娃答:“是,大人,就按您的吩咐去办。”
不一会儿工夫,张三娃他们带上几个人来。徐润一瞧,呵呵,是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他骑虎难下,吭哧了两声,大声问:“堂下何人,为何滋事?”
令狐泥答:“徐大人不认识本都尉了吗?我正在执行公务,你们的人胆大包天,将本官与人犯一起押来,是何居心?”
徐润眨一下眼皮,问:“怎么回事?”
衙役如实回答:“我们看他们几个厮打在一起,那个人被打伤了。就去管事,谁知,这个人却将我们大骂一顿。”
令狐泥不吭气,丁全儿连连喊冤叫屈。徐润问:“你是何人?为何跟军爷滋事?”
丁全儿泪声俱下地道:“我兄弟俩,我哥去年与我一道修城墙,他连累带病地死了。现在我家中就剩下我和六十岁的老母了。今天这位大人非得拉我当差,我不去他就打我。”
徐润道:“你说的可是实情?”
丁全儿道:“句句是真,有半句假话,叫我不得好死,他们都是我修城墙的工友,他们可以为我作证呀。”
徐润说:“那你们先回家去等候差遣,等本官查实再作处理。”
令狐泥眼巴巴地看着这几个人走了,急问:“徐大人,你为何将他们放了?”
徐润道:“本官才发布告示,像丁全儿这样的可不当差,为的是体恤百姓,恢复生产。”
令狐泥道:“现在强敌当前,护城需要兵员,你却自作主张,我找刘大人去,有你好看!”令狐泥说着甩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