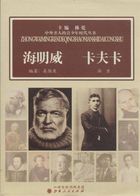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西边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校园内大部分建筑是17世纪建造的,环境幽静典雅。这间私立大学聚集着一批全美国最优秀的教师,它的毕业生遍及全球,在哲学、物理、化学、医疗、法律等专业中出了不少冒尖人才。还出了一批总统、部长和大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他们使自己的母校名扬天下,多次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名列前茅。
奥本海默1922年秋进入哈佛大学化学系学习。这时的奥本海默已经不是一个神经质的孩子,但仍然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青年,过分的敏感一直困扰着他。他常常试图从敏感和无尽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但他从母亲那继承来的这种天性却总与他相依相伴,挥之不去,令他懊恼不堪。
进入哈佛大学后每学期他经常选修6门计算学分的课,一般的学生只能按学校的要求选修5门。哈佛大学不同于其他学校,选修5门计算学分课的学生,成绩要想得A都很困难,一般都只能在B或B以下。但他时时处于一种对知识的饥渴状态,他在选修6门计算学分的课的同时,还旁听了4门他喜欢的课程。
哈佛大学教学严格,要求标准高在全美出了名,各学科的前沿知识在哈佛的课程中都能系统地体现出来,这对于其他学子真有点不堪重负,而对于奥本海默来说,却能自由轻松地边学习边挑选,看自己适合学什么、做什么。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习惯这种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具有超人的才智。
奥本海默在理性激情的后面也有痛苦。他说他不能像恩里科·费米或马克斯·波恩等欧洲人那样,从最早的时候就表现出坚定。奥本海默在哈佛大学也确实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哈佛的学习中,总夹杂着狂热和不安。他在给赫伯特·史密斯的信中暗示了这一点,他写道:
“你很关切地问我做了些什么。除了在上星期那封讨厌的短信中所说的活动,我一直在苦干。写无数的论文、笔记、诗、小说以及废物;我到数学图书馆去读书,并到哲学图书馆一边读吾师(原意为德文)贝特兰·罗素,一边思念一位美丽而可爱的小姐。她正在写一篇关于斯宾诺莎(荷兰哲学家)的论文——这真是迷人的讽刺,你不认为如此吗?我在三个不同的实验室制造臭味,听阿拉德议论拉辛(法国剧作家),喝茶并同几个迷惘的人进行谈话。周末出去把低级的能量提炼成欢笑和疲惫,读希腊文,犯错误,在我的桌上找信件,并希望我已死去。为什么?我也不清楚。就是这样。”
在知识的海洋里,奥本海默像个海盗。只要是财富,他就掠夺。他的一个同班同学说:“他在知识上抢掠了这个地方。”奥本海默也把自己假想成是一个来到罗马的哥特人(古日耳曼族的一支,在公元3至5世纪入侵罗马帝国)。他认为通过学习,所获取的知识是偷来的,而自己则是一个贼,一个掠夺者,一个不折不扣的抢掠知识的海盗。
1963年奥本海默说:“直到现在,甚至在我几乎无限延长的青年时代,我都难得采取一次行动,难得做什么事而不引起我自己很大的反感或犯错误的感觉,无论是一篇物理论文,还是一次讲演,还是我如何读一本书,我如何同一个朋友谈话,我如何恋爱,莫不如此。”
1949年奥本海默曾十分不安地对杜鲁门总统说,他有一种手上沾着血的感觉。杜鲁门在这之后告诉艾奇逊:“别再领那个家伙来……他不过是个造原子弹的,我才是让它爆炸的。”
且不说杜鲁门的话显得多么幼稚,单就奥本海默本人而言,他的这种做任何事都有犯错误的感觉是由来已久的。
在哈佛,他的朋友很少看到他这一面,其实在哈佛也如同他后来在1949年和1963年说的一样,无论做什么都有一种罪恶感。原子弹爆炸后给他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肯定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大学时代。
他的这种思维方式还可以理解为对事情的求全,求尽善尽美,但又不全是这样,其中又包含了他总是在向更高层面的努力。他喜欢追求顶点,喜欢向极限挑战。这种思维方式用在自然科学中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用于思考一切问题上就难免有失偏颇。用中国人的话说,他是一个做完事就后悔的人,而且无论什么事。可笑的是他在学习上也是这样,他喜爱掠夺,但蔑视掠夺者。他自我憎恨,有“一种很大的反感和犯错误的感觉”。
当然,他的这种感觉的深层上还有一种狂妄。他憎恨他所接触的知识没什么是他自己的。在这里他显得没什么创造性,他失去了在道德文化学校时“神童”的美誉,过去的光环都暗淡了。这使他难以接受,他对自己不能容忍。
他害怕平凡。他只能抓紧时间学习,学习又使他感到非常难堪,无地自容地认为自己是强盗,这无疑是自我作践。因为刚入大学的学子,就想把自己凌驾于世界著名的知识殿堂——哈佛大学之上,只能是精神失常的人才会想到的。
奥本海默在哈佛虽然主修化学,他要学四个学期的化学,还要学两个学期的法国文学,两学期的数学,一学期的哲学和三个学期的物理。这些还只是一些算学分的课。他的哲学和数学一直超前很多,课堂上学的只是他自学的重复。
有一次全校举行大型基础课会考,他的哲学、数学分数遥遥领先,有的学生对此很不理解,并将情况反映到了教学管理部门。其中的理由之一是奥本海默经常不来上这两门课,学生们怀疑奥本海默有作弊行为。这在哈佛校园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为了验证奥本海默的实际知识水准,校学术委员会组织了答辩会。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奥本海默引经据典对答如流,征服了所有的听众。
奥本海默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到图书馆自学,这个秘密在这次答辩后才被同学们发现。
他还自学了语文,像以前一样灵感一来便写诗和短篇小说。所以,他在大学的书信更像文人而不像是科学家写的。他一生都保持这种较高的写作能力。写作能力对他很有好处,首先他认为文学上的技巧能为自学知识打开道路。他说写作能力、阅读能力是提高自学能力的良好途径,而自学能提供创造力。同时,他也希望写作会或多或少地使他个性化。
在哈佛,他阅读了新出版的《荒原》,这是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诗集。艾略特是现代派诗歌的创始人和现代派诗人领袖,长诗《荒原》是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荒原》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凄凉景象:没有生命,没有阳光,没有水,茫茫一片荒原。人们在绝望中挣扎,呼救,像在地狱里一样受煎熬。诗的内容引起了奥本海默的共鸣。二战后,奥本海默常借《荒原》中的诗句抒发对二战期间人类遭受的磨难,对法西斯、希特勒的暴行感到无限的悲愤和感慨。他非常同意艾略特对世界的看法,同意《荒原》中反映的世界苦难感。
奥本海默还开始从印度哲学中寻找严肃的安慰。他同新到哈佛任教的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一起钻研贝特兰·罗素和怀特海德合著的三卷本《数学原理》。这部著作是罗素的主要数学著作,倡导数学的逻辑性。此外只有另一个学生敢于参加这个研究班,几十年后这个学生对自己能参加这个研究班感到终生自豪。
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关键时刻,著名的物理学家珀西·布里奇曼的物理课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他转向布里奇曼门下。许多年以后布里奇曼获诺贝尔奖。奥本海默说,“这是一个你愿意当他的学徒的人”。他学了不少物理,但却是无计划的。
他开始找到构成化学基础的物理学,找到他人生新的坐标。他说:“我发现我在化学中所喜欢的东西非常接近于物理。假如你在读物理化学,显然你会碰到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的概念,你将要了解它们……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从来没有读过初等物理课。”
他的兴趣开始从化学转向物理。在此之前做一名化学家一直是他所希望的,在这以后他追随布里奇曼开始了他漫长的物理学研究。
有一次布里奇曼上课时涉及到很复杂的一项数学运算,稍有失误,奥本海默马上站起来,拿起粉笔演算起来,步骤简练,运算精确,连布里奇曼都不由得发出由衷的赞叹。
周末,奥本海默偶尔驾驶着他父亲给他的27英尺长的单桅小帆船,或整晚同朋友徒步旅行。他的同学关系比在道德文化学校要好一些,朋友也比以前多。但他一般不愿在课外活动和在小组中抛头露面,也不同女孩约会。他还不够成熟,只限于远远地崇拜漂亮、丰满、比他稍大一点的女性。
他后来评论说:“我虽然喜欢学习,同时学许多东西,但不愿让人发现。”他努力的结果是一份成绩绝大多数是A、只有几个B的毕业证书;而且他仅用了3年的时间便修完了大学本科4年的课程,并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毕业后,他常说哈佛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代。我确实有机会学习。我爱它。我几乎觉醒起来”,“我掠夺了哈佛”。哈佛大学像一位伟大的母亲,用她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他。哈佛为人类又培养了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她又培养了一位值得她永远为之骄傲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