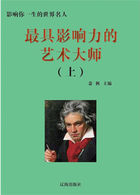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八一三”,是日军对华步步进逼的六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热情日日高涨的六年,也是胡适一直“主和”的六年。他不主张中国“主动”对日作战,而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以赢得抗战“准备时间”。
胡适所以不主战,主要理由是中国“没有能力抵抗”。他分析热河沦陷时张学良部队不战而退、日军长驱直入的惨痛情形后说:“九一八”时不抵抗,“实在是没有能力抵抗”。1933年3月13日胡适亲闻蒋介石“军事上不能抵抗,外交亦无办法”的表态后,就更加确信:中国政府对国难既无解决的能力,也无解决的办法。他的这一判断,一直持续到“八一三”上海抗战之前;所以平津失守后,他仍不主战,仍力谋和平。他的理由极为明确: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
既认定中国无力抵抗,胡适乃把积蓄力量、努力谋自身的现代化视作救亡图存的首要之务。他坚信:“只有一个现代化成功的中国方才可以解决远东问题”,“必须先有个国家,然后可以讲抗日救国”。把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抗战的前途紧密联系起来,这是胡适观察中日冲突的第一个鲜明特点。在胡适看来,实现现代化既是终极目标,更是目下解决民族危机的紧迫手段。他呼吁国人要努力工作,拼命工作,拼命谋自身的现代化,因为“一个民族的兴盛,一个国家的强力,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长期努力的必然结果”。他强调:“救国的唯一大路是齐心协力的爱护我们的国家,把我们个人的聪明气力都发展出来好为她服务,为她尽忠。”惯于自责和反省的胡适一直把“九一八”的耻辱归咎于中国人的不努力,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荒废了宝贵的实现现代化的时机所致。他一再批评国人缺乏自责态度,不知道反省自己;告诫国人“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埋头苦干,要努力充实自己的实力,要多责己而少责人,多在内政上努力。在亡国危机日甚一日的情势下,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宣战、收复失地”的强烈呼声里,胡适的这种“缓不济急”的主张,虽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颇为接近,但并不为多数国人认同。
至于胡适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更不为国人所谅。首先需要指出,胡适对日本侵略的谴责和揭露历来都是严厉的,其和谈主张不是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更不是“媚日”,更不能代表他不爱国。起初,他是希望通过谈判来收复失地,保全将失之地。他在1932年提出与日本交涉的目标是“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但随着日本退出国联、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时,他就不再主张对日交涉了。热河沦陷后,胡适已经看到“日本军阀的欲望是不能满足的:把整个的中国做他们的保护国,他们也不会满足的”,“日本军人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但到了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自治时,尽管胡适也对时局做出“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的正确判断,但他仍通过王世杰向政府建议“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方法是“有代价的让步”,他所提出的“让步”甚至包括承认“满洲国”!这与之前的主和主张,是一种明显的变化。胡适一再表白这是谋求短时和平的权宜之计,目的是换回“十年的喘气时间”,以为抗战做准备。因为他已虑到会出现求和而不能和的情形,那就只有痛下“绝大牺牲的决心”,“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为了准备这个“混战”、“苦战”,必须先“详细计划一个作三四年长期苦斗的国策”。所以,胡适提出了这么一个权宜之计。胡适出此计,还有另一目的:保全华北。针对胡适的建议,王世杰认为,“在今日,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某种条件既万不可得,日本亦决不因伪国承认而中止其侵略与威胁。而在他一方面,则我国政府,一经微示伪国之意思以后,对国联,对所谓华府九国,即立刻失其立场,国内之分裂,政府之崩溃,恐亦绝难幸免”。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王世杰拒绝将胡适的建议转呈蒋介石,胡的这次和谈主张再度不了了之。1937年7月下旬,胡适仍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应负起和平解决的责任。”8月初,日军已经占领平津,但胡适仍谋在大战前“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其中的一条理由是:“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他提出的目标是:“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充分运用眼前尚有实力可以一战的机会,用外交方法收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为达此目的,胡适再度提出以“放弃东三省”作为让步。在胡适看来,似乎只要放弃东三省,就会阻止日军的侵略步伐,就可“求得此外一切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中国就可努力实现现代化,然后再收复东北。这真是抱薪救火、与虎谋食的书生之见。一周之后,胡适的美妙理想即被“八一三”的炮火粉碎得灰飞烟灭,而他在这次抗战中也深深领教了中国军队的“能打”和“肯打”,至此,他开始觉悟到“和比战难”,逐步走上毫不动摇的坚持抗战之路。胡适所以放弃和平之路,除了中国军队的出色表现,还因为卢沟桥事变后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他1935年预言的中国已经“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日本军阀灭亡中国的野心和行动已经再清楚不过,而这时也只有“不顾一切”,做困兽的死斗,用中国的“焦土政策”来应付日本的“焦土政策”。假如此时还不应战,岂不是要坐视整个中国都要沦为第二个“满洲国”?
和谈之路,本是一条死路,因为日本军阀“灭亡中国”的既定国策绝不会轻易变更,而看清了日本侵略野心的中国政府也不会选择这条路。尽管和平之路走不通,但胡适的主和立场六年间从未放弃,且事后亦终不悔。假如我们只是单纯考察胡适和平主张的是非得失,而不把它与中国现代化联系起来,是很难全面、准确理解胡适的抗战思想的。胡适的主和,是放眼长远,其根本目的在求得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相对和平的环境,以根本解决民族危机。他所说的现代化,不只是军事现代化,还包括国家的统一、宪政、民主、思想言论自由和教育学术文化的进步等方方面面。不学时髦高喊救国口号,而把着眼点放在中国现代化方面,强调“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各方面”做“长期拼命的准备”,这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对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恰是至关重要的。
胡适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中国方面应该如何自卫,那是我们自身努力的问题”。这类似于后来中国政坛上的一个流行话语:“独立自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抗战能脱离国际大环境独自完成,相反,作为一个坚定的世界主义者,胡适一直把中日冲突放在国际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将中国抗战的前途与未来世界的命运相结合。这是胡适观察中日冲突的另一个鲜明特点。
胡适在揭露和谴责日本的对华侵略时,多次强调:这不单是对中国的侵略,更是对世界正谊的挑战,是对数十年来理想主义的世界新秩序的破坏。1932年日本承认“满洲国”时,胡适怒斥这种行径是“破坏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和国联盟约,是向世界的舆论挑战”。1933年日本无视国联的调解建议而进攻热河时,胡适评论道:这“已不仅是中国与日本的冲突了……乃是日本与世界正谊的作战”。早在1932年,他就预言,如果日本的疯狂行动不被制止的话,中国和整个文明世界“都将准备过十年的地狱生活”;而日本的行为若不悛改,“这个世界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全,必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的一日”。1935年,伴随着日本的侵略步伐加快,胡适又断言:“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的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事实证明,这些预言也都准确无误地应验了。
胡适所以特别强调国际局面的重要,其理由是:“国家的生命是国际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可因为怕一个强暴的敌人就完全抛弃了全世界五六十个同情于我们的友邦。”他认为制定外交方针时“要把眼光放的远一点,认清国际的趋势,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朋友和敌人,并且努力增加朋友,减除敌人”;相反,“我们此时若离开国际的局面而自投于敌人手下,不过做成一个第二‘满洲国’而已”。“八一三”之后,胡适更加寄希望于国际局势的转变。他从事战时外交五年,最坚决主张的是“苦撑待变”:“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于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他认为“苦撑”是“变”的前提,只要中国付出庞大牺牲,美国才会卷入战争。而他在美国的演讲活动,仍然将痛斥日本破坏世界新秩序的责任等作为主要内容,与战前是一脉相承。
一方面特别重视中国现代化,一方面又不忽略国际局面,这是胡适观察中日冲突后提出的两条基本的因应之道。所有“和”、“战”主张以及前后变化,都是以上两条因应之道在具体形势下的具体主张。早前,学界在研究抗战时期胡适的对日态度时,主要把研究的视角和重点放在由“和”到“战”的变迁方面,也取得不少成果。即将出版的日本北海道大学胡慧君博士所著《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适》一书,亦是按照“和”、“战”主张及前后变化的思路加以研究的。
2012年8月,笔者初识来本所访问的胡慧君女士,并就胡适研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其时,胡女士正在对其博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适——其战争观的变化及在美国的演讲活动》做最后的修改,并联系在国内出版。稍后,胡女士来函告知,出版事宜已经商妥,并将书稿电子本发来请笔者提意见,还提出要我做一篇序言。因深知自己才疏学浅(这绝对不是什么自谦),实在不愿接受这一邀约。但胡女士至为诚恳,也只有勉为其难。答应此事后,我先是找来能看到的胡适有关这方面的政论、《日记》、书信、演讲以及所有的相关研究论著。在反复思考的基础上,我写下了上面的文字。然后,我数度精读胡女士的著作,现在也把感想报告给读者。
胡著共四章,就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两章(《从主和到主战》、《胡适的枙墨子·非攻枛研究与其战争观》)研究胡适的战争观,后两章(《作为驻美大使之胡适的演讲活动》、《作为特使与驻美大使之胡适的演讲活动之意义》)剖析胡适演讲活动的内容和意义。
在第一章,作者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8月6日,胡适的基本路线是主张议和。作者不同意余英时“至晚从1935年7月始,胡适已逐渐修正其和平看法”的观点,认为胡适此时依然还在主张议和,只不过“萌发了抗战的决心”。1937年8月13日,胡适看到了中国军队勇敢抵抗了日军的情景,毅然扔掉了议和主张抗战,从而变为彻底地全面地支持对日抗战。
对胡适在全面抗战前顽固的和平主张,早前的研究者只笼统地提出“和他早年的和平思想有关”,而未有深论。作者根据《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线索,在第二章仔细研究了《墨子·非攻》的战争论、“义”与“利”以及胡适的理解,阐释了胡适的战争论与《墨子·非攻》中、下篇的关系。作者将《墨子·非攻》的基本思想与胡适从主和到主战的转变以及他作为驻美使节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加以对照研究,指出《墨子·非攻》上篇是胡适作为极端和平主义者的思想根源。应该指出,这种研究视角和结论都是全新的。
演讲是胡适从事外交活动的主要手段,考察和评价胡适的演讲活动历来是研究胡适战时外交生涯的首要问题。但先前的研究只是根据胡适的有关表述,笼统地说胡适演讲甚多,至于五年间究竟演讲多少次,在何时、何地演讲,演讲对象为何人,演讲的内容是什么,等等,则尚未有全面、系统地梳理。《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适——其战争观的变化及在美国的演讲活动》一书则根据胡适的《日记》、年谱等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对历次讲演的时间、地点、标题、对象者、出处·根据、备考等六个方面的信息详细列述。据作者统计,从1937年9月23日到1942年9月18日,胡适共做讲演238次,其中的35次以演讲记录的形式发表,另有34次以论文形式发表。这种扎实、细密的资料工作,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一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补白意义,且为其进一步分析胡适演讲的内容和意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者指出,胡适演讲内容的“关键词”有八:九国条约(世界新秩序、国际新秩序、新国际主义、新世界道德);自杀愚行(日本切腹);福奇谷作战(Valley Forge);苦撑待变;为世界作战;民族生存、抵抗侵略;美国的国际领导权;日本的侵略行为。
战时日本的报刊如何刊载、报道、评价胡适的演讲活动,这是“胡适与抗战”研究的薄弱环节。对此,胡著做了深入研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胡著还对日本刊载的胡适的演讲文稿与中文以及英文原文加以比较分析,以此了解胡适的演讲在日本的反应,以及对日本的影响,并以此探究胡适演讲对日、美开战所起的作用。作者通过仔细比对指出,日本报刊在登载胡适演讲时不仅故意地把“侵略”(aggressive policy)译成“政策”,把“日本帝国主义”(Japanese imperialism)和“日本军国主义”(Japanese mili-traism)只译成“日本”;还有意删掉了揭露日军暴行的语句:“我不想强调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毒害沦陷区民众中所表现道德沦丧的事”,“于是决定在中国获得安定和强盛之前要粉碎国家主义的中国”;有意删掉了揭露日军战时困难的具体事例:每天伤亡近千人,新公债无法售出,为购买战争物资使进口额远超过出口额;有意删掉了表明中国人抗战决心的语句:“这次战争非到中国获得公平和荣耀得和平是不会终止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者对每次删改,均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如关于上引最后一条,作者就分析道:“如果日本国民知道了中国的这个决心,那么也会让日本国民知道这个战争将会变得长期化、泥沼化,也同样会使他们增加厌战心情。可以推测:对日本来说,如果举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会给日本国民带来坏影响。”通过比对和分析,凸显了胡适的演讲对日本的影响。作者的最后结论是:“……形成支持中国舆论的基础的是胡适的外交活动,特别是他的演讲活动的效果最大。正是胡适自1937年9月末开始对美国国民等做的400次之多的演讲造就着这个支援中国的舆论基础。正因为有着这样踏踏实实的努力,慢慢地在美国形成了支援中国的舆论,造就了约三年之后去美的宋子文对美外交的基础。”笔者以为,这是平情之论。
要之,这是一部颇有新意的胡适研究著作,值得胡适研究学界关注。
宋广波
2012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