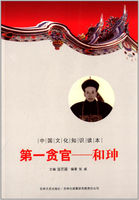十多年前,我在日本关西地区工作。现在记不起因什么信息,慧君千里迢迢从北海道来看我,同来而先后到的是北海道开拓纪念馆的同行,则自然因为一是同乡相会,也更是同行的交流了。我们相处也就两三天时间吧,但似乎十分的默契和亲热,不然这友谊也不会持续到现在,当然还应有将来。
慧君当时在北海道留学,或许语言能力强,翻译水平高,所以当地的教学文化单位常请她当临时翻译。和北海道开拓纪念馆的关系,大概也是这一原因吧?慧君应该是聪慧的、勤奋的,这是我从朋友处的交谈中感觉到的。而我对她的印象最深的是好学,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并努力去了解熟悉。
虽说一衣带水,我们平日联系还是偏少,尤其是我国的邮政凡寄国外的都贵得出奇,我即便为公家邮寄,都尽量节省,个人的更是小气,所以书信往还并不多。但我知道她考上硕士研究生了,又考上博士研究生了,所以一直为她高兴。
记得江泽民去日本访问,当时我也在日本。有一天收到一张大照片,是江泽民在北海道接见在日工作者与留学生代表的合影,此中就有慧君。慧君或许还没想到寄照片和我分享一下那份快乐,而这照片居然是日本朋友寄来的,可见那朋友也为慧君有这份荣誉而高兴。如今对于领袖人物,我们国人似乎早已没有当年那种神圣的甚至狂热的感觉,但是,我们还是可依此推断慧君在学习上该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我们同样为看到这一照片而欣喜。
后来,有了E-mail。或许因我是电脑盲,用不好,汉字发不出,所以我俩写信都是用拼音文字,那毕竟也比写信邮寄简便多了。必要时,请人帮我用图片发。再后来,一切都好使了,才有如今的方便。我也知道她对五四时期的前辈学者感兴趣,我很激动,因为过去隔行如隔山,现在终于有了共同点了。而从学业上,我的前辈正是那批人。后来,她又告诉我,她开始搞胡适研究了。我说好啊,我对胡适同时的人有些了解,对胡适知之甚少,也可趁机多了解些。
不知什么时候,我知道她嫁人了。丈夫是个律师,是个经常免费为穷人、为中国劳工打官司的好律师,也就等于说是个不太富裕的律师,是个与在日本的中国王选一样有正义感的人士。慧君自己也免费为中国劳工做了近十年的翻译。或许是因为我和王选同姓,也更有同乡的感觉吧。她可能是带着对王选的一份感情,所以才问我和王选是否本家或是否熟悉。我潜意识里似乎为了让她在异国他乡多一丝暖意,也就尽量“套近乎”般地说,我和她是同一年大学毕业的,第一年暑假批中考卷好像在同一教室(我现在真想不起了,当年她并不有名,怎么会知道其名并记住),还有好像是我姐夫家的亲戚。
她的丈夫长相除了日本人的特征较明显,并无特别之处。她的儿子也因小而可爱,其他也没什么感觉。不过,这些是我从她寄的贺年卡中了解的。日本有个好风气,是我们没接触过的人不理解的。我曾学日本人寄过印有我照片的贺年卡,有朋友以为是我在炫耀我照片拍得得意,所以我在某篇报上文章中特意顺便解释一下。我曾听日本朋友说,日本的贺卡是全世界用得最多的。他们一直以来都时兴在贺卡里印上自家喜气洋洋的照片,告诉亲友他们过得很好,不像我们只给对方一声问候。但照片归照片,当我亲眼见到她儿子时,十分地喜欢。长得斯文、白净、漂亮,我不禁要赞美他妈妈。在那以相夫教子为妇女主要工作的国度里,我赞美他妈妈应该没错。记得在日本时,有位日本同事喜洋洋地说,他儿子考上东京大学了。有一中国同事马上附和说,那是你教的好儿子。可那朋友听了,好像并不怎么开心。我开玩笑般地提醒他,你是否认为他尽了他夫人应尽之责了?换个说法吧。我说,了不起,像你!他就开心了。
慧君在家庭中,也是个相夫教子的角色。但是,她却同时又兼着天下最忙(我认为)的学者身份。儿子降生,一家人都围着他转,这常是国人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持批评态度的一点。但是,她连被批评的福气也没有,外公外婆远在中国,爷爷奶奶我猜想在这家庭也不方便,所以照顾孩子的事主要由她担任。研究写作的时间,没得选的只能放在孩子睡觉之后。带孩子是极辛苦的,带过的人都深有体会。管孩子是整天无时无刻不紧张,孩子睡了,自己也累得快趴下了,不管躺到哪里都能呼呼入睡的。但这个哺乳期的妈妈这时还得摇身一变为学者,开始了爬格子的艰苦劳动。
我们还有一点没想明白的是,她所研究的资料,写作的素材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研究资料是她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老报刊中一点一滴挖掘的,有中国的,更有日本的、英美的。而她毕竟不是英语或日语专业出来的,对于阅读研究,都有一定的或相当的难度。虽然在日本很多年,要写作一本纯学术的日文著作,其难度也是可以想象的。当然,这里最值得称道的是查找资料所下的功夫。这是日本或欧美学者做学问的长处,虽然中国学者也同样注意搜集材料,但那种专注,那种细心,那种上天入地不懈探寻的钻劲,还是大多数中国学者无法比无法学的。这一点,明显是她受了日本老师的影响,更得到了日本同行教授们的指教。
前几年我曾为一个日本学生修改博士论文,因其语言障碍,我改那论文改得非常辛苦。也正因他注意深入搜集资料,在论述中资料充实,证据丰满,竟在和中国学生的“竞争”中获得优秀论文,我也算没白费心血。我特别指出这点,也是希望与中国学界同仁们共勉的。
胡适是五四时期非同小可的人物,在中国文化舞台上,一直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哪怕在当年的动乱时期,从反派角色的角度,他仍是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亦即批判对象。我虽然是“文革”结束后上的大学,但那时胡适照样是高校里的批判对象。在我们的印象中,胡适好似文化界或学术界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大学里有一个好处,虽然遭批判,但是他的书还是可借阅的。我借阅他的第一本书是《尝试集》,那是一本他刚刚尝试着用白话写现代诗的诗集。看了后印象还真不好,就像缠脚老太婆走路,歪歪扭扭的,实在难看。直到后来,也就是近些年吧,胡适早不算“坏蛋”而成“好蛋”了,但我还是不舒服,还是希望他仍是“坏蛋”。就在前几年出版的书中,我还在一章里以较大篇幅从逻辑学角度批评了他关于校勘学的论述。当然,我写作中并未认定了他仍是坏人,我是以我学术的角度去看待他的。那心底里是否还有过去的情结呢?大概没有,但也许是另一种影响或暗示。那是我心里有我敬仰的导师,人称真正的“国学大师”的姜亮夫先生,还有我同样敬仰的我导师的导师王国维先生与梁启超先生等。另外也有后来所得的印象,五四运动的激进者,同时也把传统文化给破坏了。就如台湾某学者说的,胡适他们一代人国学功底好,他们中许多人自己成了一代大师,而他们回过头来反对传统文化,结果后辈再也出不了大师了。
胡适有极好的旧学功底,所以凭此而早有大名。或许也因此而被推上历史舞台又下不来了,所以后来几乎成了文化学者或文化政客。在那一大摞著作中,真正属于学术研究成果的比例并不太大。在今天,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但是,正如慧君说的,我“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在我所受到的教育中,胡适是‘卖国贼’”。胡适究竟何许人也?今天的人们都会好奇,慧君也好奇,所以就有了此后的研究。
胡适为何是“卖国贼”呢?该著作没研究这点,而是研究作为国民使者和驻美大使的胡适,他究竟想了什么、干了什么,以及他的所思所做在当时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
在我们过去的印象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抵抗是消极的,用老话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关于积极反共这点,在今天看来仍是毋庸置疑的,但消极抗日呢,或者说不抵抗主义呢?看看本著所写的,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似乎也是事实。但那是什么样的一种背景呢?
就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中国留美学生呼吁对日开战的反应一样,胡适给留学生们写的公开信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我们至多只有十二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胡适在1935年夏天给有关人士写信也同样坚持这一观点:“我举一例为伪国(即伪满洲国)的承认,我提出的代价有三:一为热河归还,长城归我防守;二为华北停战协定完全取消;三为日本自动的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种种条件,如平、津、沽、榆一带的驻兵,及铁路线上我国驻兵的限制……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好一个“喘气的时间”,正是由于我们还无法回答“拿什么去作战”的重大问题。所以,慧君在论著中有以下的文字: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之时,就算中国要抗日,但由于军备不充足,当然没有胜算的可能。正像胡适自己所说的一样:“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他在担忧着中国的军力。胡适到此时还因为跟日本作战不会取胜,作尽可能回避战争的努力。
胡适站在即使承认傀儡满洲国,即使作最大的让步,也应极力避开战争、选择和平之道这样的立场上,看起来好像有如《非攻》中、下篇一样的在叙述着利与不利,但实际上他在极力避免大规模“杀人”的战争,与《非攻》上篇精神相通,在根据义不义的观点来分析情势。而事实上,议和才是极力减少“杀人”的方策。
由上所述,无论胡适做法对否,但至少不会轻易认为他是不抵抗主义甚至是卖国。那胡适是在什么情况下由主和而转为主战的呢?作者认为,一是日益加剧的日本的侵略,与日本的议和已经不能实现了;二是看到了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中中国军队的奋勇作战。这使他感到中国也能抗战,从此他的观点也随之变为对日作战了。现在看来,对这样的观点并不难理解。写此文期间,出门上出租车,爱国的司机聊起中国的军力,他竟说了句,小平不是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因为现在实力还斗不过人家。可见这样的道理谁都懂,但或为政治原因,或情况不明,不抵抗主义或卖国贼的帽子是很容易被扣上的。
作者对胡适主和、主战的思想变化过程的研究是极细致的,运用材料是准确而充实的,她以一点一滴的事实,构筑了胡适关于抗战思想一个完整的形象,读之真实可信。作者将胡适的演讲与日本报刊翻译转载的文字一一进行比对,指出了涉及侵略等字眼多被删略。一方面说明了日本政府向国人掩盖侵略的真相,一方面更揭露了其侵略的野心与本质。
我们常赞美鲁迅先生的文笔,赞美他什么呢?有一点,就是生动可感。就如人们熟悉的《记念刘和珍君》,其中有一段是: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鲁迅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去细细交代刘和珍等如何倒下呢?就是他虽然没有亲见,但是听目击者极细致的描述,就如身临其境一般,就不能不让人相信。看着学生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一个个倒下,你能不愤恨这残暴的段祺瑞执政府吗?慧君对历史资料的运用,也正有类似的妙用。
不过,我以为慧君对胡适《墨子·非攻》研究与战争观的问题这一研究题材的开发更值得称道。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以“兼爱”为其理论基础的,是以维护本国百姓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非攻”对大国与强国,尤其是对好战的君王是个批评,而对小国、弱国则是个保护。墨子既不赞成国与国之间的攻占掠夺,也不盲从“春秋无义战”的看法。他对战争性质有深刻的分析,故他支持正义之战而谴责不义之战,并由此而将战争分为“诛战”与“攻战”。攻战即是不义之战,诛战则是抵抗侵略的正义战争。
胡适是个驻美大使,但他首先是个学者,在美国人眼里,他更是个由美国人培养出来的学者,则多几分亲切感和信任感。那么,他的演讲不仅有事实的分析,还有传统文化作为学术依托,他的演讲也就更有魅力,更有说服力,也就更有号召力。他“行万里路,演百余讲”,对于美国(包括欧洲)政府与人民,认清日本侵略的本质,转而同情中国并支持中国的抗战,不能不说起了重要的作用。
慧君作为日本北海道大学的学者来访问我,对于一个老熟人来说是格外感到高兴的。她还带来了博士学位证书的彩色复印件《学位记》,虽是迟到的消息,还是多添了份喜气。如今中日两国正处于钓鱼岛争端的敏感时期,慧君写的又是在日本教授指导下有关抗日战争的书,其主要内容是胡适关于宣传抗战揭露日本侵略。此时此刻阅读此文,还是颇多感慨的。
王宏理
壬辰中秋前夕
于老杭州大学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