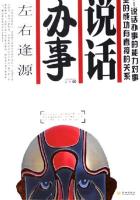一
他以哇哇啼哭的姿态降临尘世那年,南国的小镇意外地飘起了纷纷雪花。
寂寥的冬夜,惟有我和父亲在气喘吁吁地奔跑着。他一面奋力摇晃着笨拙的身体,一面抬手拂去饭盒上的雪花,欢喜着说:“你有弟弟了,高兴么?”当时我只有六岁。对一个连加减乘除法则都记不全的孩子来说,弟弟实在是一个玄之又玄的称谓。但我还是由衷觉得愉悦,因为弟弟意味着我从此再不用孤独地睡在床板上,再不用一个人对着花白的天花板背诵乏味的唐诗宋词,也再不用搁下手中的玩具去街口打一瓶又一瓶黑乎乎的酱油。
我仅仅以为,弟弟就是一个比我还要弱小的形影不离的玩伴,他排遣我的孤独,且对我言听计从马首是瞻。
我笑了,踩着松软的雪花跟在父亲身后,踉跄的脚步,如同胸中高低起伏的莫名喜悦。
时间真是一支微妙的画笔。当他挣脱母亲的怀抱,执拗着要独立行走,他的一举一动便深深牵扣了父亲的心。
他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时,父亲如临大敌般跟在他的身后,谨慎地张开双手;他奔跑着摔倒在门前时,父亲温柔地握住他受伤的小手,一面爱怜地吹气上药,一面替他擦去委屈的泪水;他第一次在书本上写下爸爸这两个字时,父亲喜笑颜开地将他抱在怀里,直到吃饭也舍不得松开。
我终于开始后悔了,我不该有这样一个弟弟。他的出现,从始至终就不曾给我带来过任何好处。反而,剥夺了那份本该属于我的父爱。
很快,我向父亲提议分房。那时我已步入学堂,他整夜不定时的吵闹,时常让我从梦中惊醒。偶尔我会朝着他恶狠狠地吼道:“别哭了!再哭我就撕烂你的嘴!”
我的恐吓从来没有起过半点作用。他哭得更凶了。尖细的声音像一根根利刺,锥醒了隔壁的母亲。母亲慌张地拖着鞋子推门,心疼地用纸巾擦去他脸上的涕泪,一遍又一遍地轻哄:“哦,哦,宝贝不哭,不哭,妈妈在这儿呢,谁欺负我们家宝贝了?告诉妈妈,妈妈帮你打他。”
他不说话,伸开白嫩的手指朝我所在的方向指来,非得等到母亲弯腰,重重地在我的被子上拍打几下,他才肯把那根细弱的手指收回去,继而止住哭声。
二
他终于到了需要伙伴的年纪。可惜,整条街的孩子都不愿和他一起。原因极其简单,因为我在背地里不止一次说过,谁要是和他在一起做他的朋友,那就是我李兴海的敌人。
与我同龄的孩子嫌他年纪太小,不屑与他一起玩。而与他相仿的孩子们,又迫于我的缘故,对他避之不及。于是,他就整日整日地跟着我,左一声哥哥右一声哥哥,叫得人心烦。
每年春天,我都会躲在后院的角落里赶制庞大的风筝。他知道我的秘密,时常趁父亲不注意跑到后院找我。我跟他说过无数次:“倘若父亲知道你丢下作业只为来看我偷做风筝的话,又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我了!我求你,不要再害我行不?你害我还不够多吗?”
他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偶尔,他会站在卧室的沙发上,踮起脚尖趴在窗前,隔着玻璃审视我的工作。这一刻,我的内心是纠葛复杂的。我既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报复他,一解心中的怨气,又渴盼他能快些长大,并且懂事,一补我俩之间的隔阂。
我们就这么幼稚地明争暗斗,悄然成长。转眼,他便到了入学的年纪。
清早,母亲将他交到我的手里,令我务必将他送到教室门口。我握着他冰凉的小手,看他欣喜若狂地摇晃着背后的新书包,笑若桃花。我知道,母亲一定在背后默默地注视。因此,直到拐出那条幽深的小巷,我才将他的小手奋力甩开。
人群中,他像只受惊的兔子,一路紧拽我的衣角。经过早餐店的时候,我进门买了两份煎饼果子。他一直跟着我,不肯松手。我将其中的一份煎饼果子随手递给了他,他不接,喃喃地说不饿,我又递了一次,他照旧不接。我有些火了,转身吼道:“你不吃不会早说吗?现在买都买了你才说不吃?你以为我想为你多花钱呀?”
他捏着我的衣角,站在风起的路口,泪流不止。我记得他当时说过的话,他说:“我知道我一松开手,你就会把我扔下。”
那是我第一次被自己仇视的弟弟所感动。我踅身将打开的那份早餐递给他,而后腾出一只手抓住他的书包说:“吃吧,放心,在你没到教室之前,我绝不松手。”
那年,他刚满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