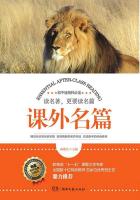任由外面的人焦虑不安,而萨拉只是穿戴整齐地独自呆在窗前,她心里乱极了,她要嫁给一个自己从没有爱过的人,而心上人的身影又占据了她全部的心身。
带饰物的斗篷滑落到地上,露出许多钻石在她的手臂上闪闪发光。这些首饰又烘托出她那自负的和庄重的痛苦。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穿着雍容华贵的古典式衣服的当奴隶的美人。
她多么希望现在自己穿着的雍容华贵的新娘礼服是为帕兹而穿戴的。
事实上,她并不看重金钱,只要与她相亲相爱的人在一起,就算沿街乞讨也是幸福的。但那些只能是幻想,现在,她必须面对事实,痛苦和悲伤折磨着她的灵魂。
她透过绿色的窗帘观看幕色下的田野。突然,一条黑影很快闪到木兰花林荫道里,她开始一惊,但很快又放松下来,那是她的仆人里贝尔塔,他好像正窥伺着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一会儿躲在一座雕像后面,一会儿又躺在地上。
难道有坏人进来了?那人想干什么?年轻姑娘有些不安,她环视一下自己的周围,只有她一个人,确实只有她自己,她的目光移回花园,她的心再次缩紧。
她看到了什么?里贝尔塔和一个大个子男人打了起来,高个子把里贝尔塔打倒在地,里贝尔塔只能发出唔唔的声音,好像有一只粗大的手捂住了他的嘴。
萨拉睁大眼睛,终于鼓足了勇气,准备喊人之即……仆人站了起来并指着面前的人……“你!你!你!”他叫了起来。
接着,高个子揪着里贝尔塔来到萨拉的阳台下。萨拉刚要大叫的嘴改变了口形,那声尖叫也变成了另外一种惊讶的声音:
“你!你!你!”
谁,是谁让年轻的姑娘既惊喜又不安?
长久以来,从没有人让她如此激动过,能够引起她强烈反应的只有一个人——马丁·帕兹。
他像阴间来的幽灵一样出现在她的面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萨拉,用冷冰冰的口吻说:
“听到为你的幸福奏起的欢快音乐了吗,美丽的未婚妻?宾客们都挤在客厅里要一睹你娇艳的容颜呢!准备当那个该死的人的殉难品的人,是不是甘愿让这些贪婪的人一饱眼福呢?一张痛苦、苍白的脸,眼睛里闪着苦涩泪水的少女,怎能面见她的未婚夫呢?”
接着,马丁·帕兹又用无比温柔的口吻说:
“未婚妻既然不情愿埋葬自己的爱情,那她就应该摆脱束缚,还自己少女之身,越过父亲的家,越过让她悲伤、忧愁的地方。在那里,没有纷争,没有压迫,没有痛苦,男人们心胸开阔,女人们精神焕发、心情舒畅!”
说完,他抬起手,萨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仿佛看到了那充满阳光的幸福地带。这时,她的神智开始模糊,只听到情人在跟她说话,而且那声音越来越温柔了。
突然,一阵脚步声打断了这美好的感觉,这是她父亲和未婚夫的脚步声,印第安年轻人机警地关掉了他头上的灯,随即一声吹哨子似的叫声响了起来,使人想起马约尔广场上听到的哨声,打破了夜空的宁静,姑娘失去了知觉。
萨拉的房门被撞开了,萨米埃尔和安德烈冲了进来,显然他们也听到了哨声,仆人拿着灯火及时赶到。然而,房间里已空无一人!
“无耻的泼妇!”混血儿嚷道。
“她到哪去了?”萨米埃尔问。
“这件事,你要负全部责任。”安德烈恶狠狠地朝犹太人喊道。
萨米埃尔吓得直冒冷汗,心里在不停地打鼓。
“都跟我来。”他朝仆人们喊,随后冲到了房子外面。
黑暗笼罩的大街上,马丁·帕兹抱着少女飞快地在前面奔跑;仆人里贝尔塔紧随其后,但看样子并不像要为安德烈夺回未婚妻。
在离犹太人的居住地200步远的地方,帕兹找到了几个随行的印第安人,他们是听到哨声后聚集在一起的。
“回到我们山里的牧场去!”帕兹大声说。
“不,回到堂维加尔侯爵的住处去!”另外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他转过身,看到一个西班牙人站在他的身边。
“现在,你想保护这个姑娘?”侯爵问。
马丁·帕兹点了点头,压低声音,对他的随从说:
“好吧,现在到堂维加尔侯爵住处去!”
然后,一群黑影快速地奔向侯爵住处。
这边,在萨米埃尔的家里,再也找不到喜庆的音乐,无声的哀乐充斥着整个住宅。他们翻遍了所有的房间,找遍了每一个角落,没有,没有萨拉,没有萨米埃尔的女儿,没有安德烈的未婚妻。
安德烈的朋友们加快脚步,他们在圣·拉扎罗市郊仔细地搜寻着,匆忙地打听,但一无所获。犹太人烦燥地走来走去,整夜千方百计地追寻都毫无结果。
“马丁·帕兹还没死!”安德烈·塞尔塔怒吼道。
他的猜测没有错,现在警署被告知一位犹太少女被绑架,立刻,最积极的警察开始追踪,印第安人被通缉;既然大家没发现少女离开,这就明确地证实了最近要有反叛活动,这和犹太人的告发很吻合。
为了找回未婚妻,安德烈不惜重金打听她的消息,但城门的守卫者一口咬定没有看到一个人从利马出去,那么可以肯定,少女就藏在城中。
送完女主人回到犹太人家里的里贝尔塔,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他经常被传讯。至于是否是他绑架了少女,所有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然而,就在犹太少女失踪后,安德烈看到了可以证明马丁·帕兹还活着的证据,一个人,他就是桑伯。当安德烈听到哨声时,他看到桑伯在大街上走过,安德烈熟悉这哨声,这是他们集合的标志,所以,无疑桑伯参加了这次绑架活动。他追随他到了堂维加尔侯爵的住宅。
马丁·帕兹抱着萨拉从一扇暗门进入一间休息室,只有西班牙人才能打开这扇门,马丁·帕兹把少女放在一张躺椅上。
当堂维加尔侯爵从正门来到这间休息室时,他看见帕兹正跪在萨拉的面前,他很气愤,斥责帕兹的这种行为,而帕兹对他说:
“您看,我的父亲,我是多么爱您啊!您为什么要挡住我的去路呢?我们大山里已经自由了,我怎么能听您的话呢!”
堂维加尔侯爵一时不知所措。他开始不安起来,他肯定受到了马丁·帕兹的爱戴。
“有朝一日,萨拉离开您的家,回到她父亲那里与她的未婚夫成婚时,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您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朋友。”
这时,帕兹的眼泪已经滴到了堂维加尔的手上,这是他自长大以来第一次洒泪。
既然堂维加尔侯爵对这样的人都加以责备,那只能表明他对这少女的重视,他开始赞赏并喜欢上了萨拉,并准备把她嫁给印第安青年。
就在萨拉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面前有个陌生人。“这是什么地方?”她问。
“这儿有位让我称他为父亲的先生。”马丁·帕兹边说边指着一位西班牙人。
萨拉猛然回忆起自身的处境,忍不住哭了起来。
“你可以下去了,朋友!”堂维加尔对这个印度安青年说道。
马丁·帕兹无奈,只好退下。
这样,屋子里只有堂维加尔和萨拉了,堂维加尔便对萨拉进行了耐心的开导,萨拉则专心地听这位好心人善意的话语。在萨拉的口中,堂维加尔知道萨拉还在感激她的救命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