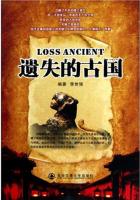刘炜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刚满十八,特招人稀罕。听说在后来的日子里,上门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其中有门当户对的高干家千金,也有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刘炜在欧洲曾周游列国,什么样的女孩子没见过?但他生性只看重功名,原先是发奋读书,现在是发奋工作,对儿女之事十分淡薄,一切都交由母亲做主。而部长夫人呢,除了要求未来的媳妇与儿子般配,更希望她能有一份孝心,和自己投脾气,对心思。从这点上讲,她倒是和普天之下的母亲或婆婆没有什么两样。
等到韩露十八岁那年考取了医学院,部长夫人亲自打电话到聚丰楼包下一桌宴席,说是为韩露庆贺,也捎带替两家人的一双小儿女订了婚,件且讲好了,等韩露一毕业就办事。
刘炜很忙,几乎抽不出时间和韩露约会,也很少到岳丈家。难得的几次,部长夫人在某个周末的晚饭后将他俩支进刘炜的房间,他总是很抱歉地对韩露笑笑,说实在对不起,我手头有个报告必须得赶出来,或是为某司长写的发言稿明天就要,一面指着书架问韩露喜欢看什么样的书。韩露真的是进退两难,她对那些外交方面的书籍不感兴趣,尽管她生性喜静,但在这会儿也宁可到客厅里和大家伙儿一起看看电视,说说话儿,或是去厨房里帮着刷锅洗碗,可又怕拂了未来婆婆的一片好意。
等韩露算计着坐够了钟点儿,起身告辞时,刘炜总会抢先替她拉开门,再一路送到公共汽车站。还好,他一般都会陪着她等到汽车进站。等着的时候,两人有时也会相互依偎。刘炜喜欢在这个时候轻轻地抚摸韩露的长发,偶尔也拈起一小绺,在手指间细细地搓捻。韩露后来想起这些心里不免有点酸酸的,因为刘炜几乎从来没有在她告辞的时候留她多坐一会儿。哪怕只是装装样子呢,韩露想。
韩露很快就发现,刘炜对她的一头秀发似乎情有独钟。他俩在一起看过几次内部电影,部长夫人总能搞到紧俏的招待票。其实也用不着她去“搞”,到时候自然就会有人送来。等到灯光暗了下来,刘炜便会不动声色地解开绾在韩露脑后的“马尾巴”, 任由手指在那道黑色的瀑布间流连忘返,或将自己的脸庞深深地埋进她的长发。
没过多久,刘炜就被派了驻外,一开年就走,都等不及韩露的第一个寒假。韩露记得她去机场送完行,又匆匆赶回医学院参加期末考试。从那以后,韩露每隔一两周就要按照部长夫人的吩咐去刘家等国际长途。电话打来了总是做母亲的先接,同样的千叮咛万嘱咐每次都要絮叨好儿遍,然后是父亲,然后兄弟姐妹还要聊上一阵子,才轮到韩露。这时候众人总是很自觉地退到其他房间。别看刘炜在单位上讲起话来有板有眼,跟韩露在一起就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只有那么三言两语,而且说来说去总不外乎 “好好念书。”“我妈身体不好,你是学医的,得空过来照顾照顾。”韩露想,你妈身体蛮好的,就是喜欢无病呻吟,但这话不能说。完了又总是“问你父母好”。韩露对这些倒也无所谓,总算是免了写信了。若要写信,除了鸡毛蒜皮的流水账,她还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呢。
韩露的宿舍里住了六个女孩子。一开始,大家去哪儿都兴结着伴儿,上课、吃饭、下午绕着校园的长跑锻炼,连到图书馆占座儿都挤在一起。渐渐地,有人谈起了恋爱,就从“315帮”分化出去了。“315”是她们的宿舍房间号码。众人先还开玩笑说谁谁谁“被拉下水了”,到后来,岸上只剩了俩,水里倒有四个。一直和韩露相跟到毕业的是一位又矮又胖又黑的“小眼镜”,两个人往那儿一站,绝对反差。其实她俩倒并不寂寞,到哪儿都有个把男生陪着跟着,而且见天儿地换人。先是本班的,再是别班的,后来又是外系的。韩露明白男孩子们的意图,又不忍驳了人家的面子,便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那距离就是“小眼镜”的肩宽——“小眼镜”的位置总是在他们中间。三个人一路走过去,便有知情者在背后指指点点:“瞧那傻帽儿,嘿!”也有心肠软的女生叹道:“等他知道了韩露已经是人家的人,指不定多伤心呢。”
宿舍里被拉下水的占了绝对优势,她们也叽叽喳喳地垄断了每晚十一点熄灯以后的“闺房姐妹悄悄话”。这群学医的女孩子聊起男女之事来一点儿也不吝,常常将课堂上学来的理论联系实际,评说某男生“虎背熊腰,性欲一定旺盛”,或是“身子骨太单薄,精子质量成问题”。她们还敢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与男友偷情的细节,甚至口无遮拦地讨论达到性高潮的种种手段。
等到多年后韩露成了刘炜的媳妇,每每行完夫妻之事,便会想起当年女孩子们黑了灯躺在上下铺上说过的那些话。结婚也有些日子了,你来我往的探亲也有过好几回了,但韩露还从没体验到女伴们形容的“像触电一般”的刺激和兴奋,或“欲死欲仙”的快活。韩露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她琢磨了许久,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丈夫开口。
令她不解的是,刘炜感兴趣的似乎仍是她的头发。他总喜欢在睡觉的时候让韩露转过身子,把脑后的长发均匀地铺在枕头上,他就枕着这一匹黑油油亮闪闪的缎子,心满意足地搂着妻子入睡。韩露记起还是在她当学生的时候,同宿舍的女生们临放暑假前一起走进学校附近的一家发廊,剪成了六个一模一样的“运动式”。适逢刘炜回国休假兼汇报工作,看见韩露一头爽爽朗朗的短发竟勃然大怒。那是刘炜唯一的一次在韩露面前失去自制力,而且好像整个假期都没再舒心过。从此韩露再不敢进理发馆,因为刘炜也不喜欢烫过的头发。
后来到了美国,有一次韩露信手翻阅一本医学杂志,看见其中一篇文章说,专家们认为有理由相信,人们获取性满足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有的人喜欢窥视他人做爱,有的人喜欢将舌头搅来拧去的法式接吻,也有人喜欢抚弄性伙伴的脚、耳垂或头发。
35
推开公寓大门,韩露一眼就看见了门房窗台上的一大束橘红色玫瑰,足足几十枝。正待夸几句,管理员老太太就叫:“露,这是给你的。”
“我的?! ”
“花店送来的。”
韩露把手里的提包挎到肩头上,好腾出手来拿花。另一只手上捧了一纸袋的黄瓜西红柿,那是同实验室的一位老美从家中后园子的菜地里摘来给众人尝鲜的。洋人兴这样,常常把自家出产的蔬菜水果,桃呀、杏呀、南瓜胡萝卜呀,带到办公室,放在门口的桌子上,愿者自取。这一来是为了与同事们套近乎,表示“有福同享”,也带着炫耀的意思,让别人看看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多滋润,多田园。
玫瑰花丛中夹了一张小巧玲珑的卡片。韩露也斜了眼,见上面用英文写着:“你的房间太素净了。美丽如你的女人应该有玫瑰相伴。”底下是龙飞凤舞的落款“J.Lee”。韩露知道,这是李晋川的英文名字詹姆斯·李的缩写。
韩露给花瓶里续了水,又在书架上挪出一方台子。鲜艳的玫瑰往那儿一摆,果然是光彩照人,满屋子生辉。韩露后退两步,歪着头满心欢喜地打量一阵,欣赏一阵,又走过去将其中的几朵插插好,这才取下卡片,发现背面还有一行英文字:“To My Dream Girl,With Love.” (给我的梦中情人,为了爱情。)
韩露顿时红了脸,心头活像闯进了几只小鹿,怦怦然跳得自己都能听见。韩露喜欢这种被人恭维,被人当做知己的感觉,特别在这冷冷清清人情淡漠的外乡客地,更让她感受到了一份亲切。韩露将卡片翻来覆去又念了两遍,脸开始沉了下来,心情也随之黯淡。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本来吃了一顿饭,再回赠一束花,算得上是礼尚往来。但如果这样的卡片也收下,那可不就承认两个人是情人关系了吗? 一直以来,韩露对李晋川给予她的种种帮助和照顾心存感激。有这样一位护花使者般如影随形左右不离地陪着她,韩露也觉得很惬意。星期六晚饭后,李晋川临走时说的那句话有些唐突,但也很突然,韩露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再者说,他们那天谈到了刘炜,这样的暗示应该是再明确不过的。
但是这个李晋川好像并没有规避的意思,现在又夹在花里送来了这样的卡片,这不明摆着的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吗?韩露有些恼火,也有些难受,心说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偏偏遇到这种进不是、退不是的尴尬事儿。
韩露凝视着玫瑰,一朵朵花儿千姿百态,千娇百媚,茸茸的花瓣上沾了些许水珠儿,亮闪闪晶莹欲滴。韩露越看越觉得心疼,越看越觉得不忍,一直硬憋着的眼泪开始很不听话地、很没出息地涌了出来,顺着脸庞流到下巴颏,再滴到胸前的衣襟上。花儿是没有错,但她不能留它们。
韩露咬咬牙,起身抹去眼泪,走进厨房,从水斗底下的杂物柜里拿出几只超市的购物袋,一狠心,将那明媚娇艳的一大束橘红,连同瓶子,一股脑儿地塞了进去。花束太大了,一只袋子兜不住。韩露又上下左右地套了几只,全都遮严实了,这才拎到楼底下,眼一闭,扔进垃圾桶里。
上得楼来,隔着门便听见屋子里的电话铃一迭声儿地鸣,算来应该是李晋川。果然,几遍铃声之后,电话留言就响起来了:“韩露,我,李晋川。在家吗?……就想问问那束花挑得是不是合你的心意,颜色、造型……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我可是真不懂。没别的事,你好好歇着。有空给我回个电话。拜。”
第二天下班回到家里,电话录音上的红色显示灯闪烁不停。韩露按下播放键,里面竟有五六条留言,全是李晋川的。其中一段儿说:“韩露,还是我,李晋川。为什么不接电话?我真的很担心,是不是病了?……”直听得韩露热泪链链,心想,我只身一人在此,如同孤魂野鬼一般,要是真有个仨病俩痛的,这世界上除了他,还有谁会想到?有谁会知道?又想,这家伙存心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只字不提那张卡片的事,弄得你就是想要数落他也是狗咬刺猬——没地方下口。
正这么寻思着,电话铃又响了。韩露还是不接,她拿定主意 不理李晋川。但是奇怪,这次没有人留言。
不多时,韩露听见门铃响,不觉一惊。怎么,找上门来了?看来这人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
门铃响过两遍,就听见一个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像是铆足了劲儿似的喊了一嗓子:“麒麟阁外卖! ”
韩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踏踏实实地放回到了原处,却又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失望。韩露打开门,走道里站着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国小伙子,一脸憨厚的笑,一头淋漓的汗,衣服倒是穿得笔挺,一看就是那种刚到美国,在这样的大热天里还得靠蹬自行车谋营生的新华侨。
见韩露满眼的迷惑,小伙子就问:“是韩小姐吗?”
“嗯。”
“李先生给你叫的外卖。”
“我——我已经吃过了。麻烦你还带回去吧。”
“钱都已经付了。”
“我——我不要,真的。”韩露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身进到里屋,急急地从提包里翻找出皮夹子,抽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递给小伙子:“给,你的小费。”
“他都付过了——我是说,李先生已经付过小费了,用信用卡一起付的。”
韩露点点头,心说,真是一个老实孩子。韩露问:“你家远吗?”
“不远,过两个路口就是。我没车,打不了远工。”
“这样吧,你先把这饭菜送回家去,千千净净的,白扔了多可惜。家里还有别人吗?”韩露知道,餐馆里面管饭,不稀罕。
“我爸妈和我妹妹。”
“那就给他们吧。”
小伙子谢过韩露,转身要走。韩露又叫住他:“你是怎么进来的?”平素有餐馆来送外卖的,总是被管理员拦在楼底下的门房口。
小伙子说:“墨西哥老太太给你拨了电话,没人接。我对她说,李先生嘱咐我一定要亲自送到你手上,看你是不是一切都好,回去好跟他回话。老太太说她看见你进的门,你好好的,没事儿。我说客人吩咐的事,您还是让我上去眼见为实的好。她就让我进来了。”
韩露倚在门框上想,难得他还肯用这番心思。
从此一连数日,李晋川没了音讯。韩露这边则是越来越频繁地和老公通电话,和国内的父母家通电话。刘炜对这种事情仍是一如既往地麻木没感觉,翻来倒去只会劝妻子“坚强些”“要挺住”,说两人之间不过六小时的飞行距离,大不了跟导师请个假。倒是韩露的母亲从女儿的语气中听出了蹊跷,待要追问,韩露便用了一连串的“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来搪塞。末了,母亲只好叹一口气,说:“你好生合计合计,不行了就回来。别跟自己个儿较劲儿,别硬撑着,啊。博士就那么重要吗?”
这天是星期五,实验室的几个小洋妞吃罢午饭便匆匆回家换了一身行头,一个个打扮得跟花蝴蝶似的,人还没到,一阵阵香气儿就已经飘了过来。女孩子们都很愿意到韩露跟前展示一番,叽叽喳喳争先恐后地讲述自己这一身装扮是从哪家公司的广告上看见的最新搭配,或这种眼影的描法又是什么杂志介绍的今夏fashion (时尚)。临了还总忘不了说一句,还是露好看,那样的天生丽质,是无论什么样的粉儿霜儿都堆砌不出来的。
韩露知道,她们下班以后就会直接去date (约会),而且常常还没到钟点儿,男朋友的车就已经在楼底下不耐烦地揿喇叭了。星期五下午,即便是最严厉的老板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反正这些大姑娘小伙子们的心思已经不在工作上了。年轻人一般都会有大半个通宵的安排,先吃顿晚饭,再看场电影,然后去酒吧酣饮,或是到夜总会里狂舞。警察们照例会在夜半时分倾巢出动,每周换着点儿地在不同的要道路口设立关卡,瞅着谁不顺眼就从车里揪出来,先让你对着一个古里古怪的仪器吹气,测洒精含量,再让你顺着地上画出的一条直线脚尖抵脚跟地紧走几步,走偏了就罚款。据说那一晚上罚的款足够警署发半个月奖金。就即使这样,也挡不住人们在星期五晚上饮酒作乐。连拖家带口的中年人也会不时地把孩子交托给邻家的老奶奶,然后夫妻双双出去浪漫一番,找回点当年谈恋爱时的感觉。对于劳作了一周,看了一周老板脸色,强忍了一周相思和情欲的美国人,星期五的夜晚 无异于一个小型的狂欢节或情人节。
五点钟,下班的时候了,韩露强作欢颜,和所有从她身边经过的人们一一道别道晚安,祝他们玩得痛快。秘书检査完毕门窗水电,见韩露还在电脑前忙活,就说:“别太用功了,露。”韩露仍是一脸的笑吟吟:“放心吧,我不会的。”
韩露磨蹭着,今天晚上她特别不愿意回家。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心境,假如李晋川打来电话,她真的有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韩露本来就不喜欢星期五晚上,也许应该说,害怕星期五晚上。冷清清的房间,冷清清的楼道,冷清清的公寓。偶尔传过来一阵阵人声喧哗,也是别人家的派对。韩露曾试图把星期五晚上打发在实验室里,以为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一会儿书,才发现,安静和冷清原来是两回事。星期五晚上的冷清,就算四周围万籁俱静,也很难使人安下心来。平日里所有的孤寂,所有的愁绪,都在那一刻被无限地放大、加重,压迫着心,压迫着泪腺。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就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但是今天与往常不同,韩露宁可孤零零地躲在这儿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