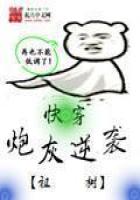在“文革”过后的中国大地上,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种迅速在民族心理深层激荡起来的“改革”之风呢?过去这个问题他没有认真思考过。他之所以搞“改革”,是因为他不能不“改革”,不“改革”医院的局面就不能维持,到了后来,他又认识到只有在医院实行真正的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一种有生气的健康的劳动秩序才能形成,于是就做了那些事情。他并没想到这些事情会被别人认为是“改革”,并且把他当作典型吹起来!但当他被吹起来之后,又发觉自己搞的这一切真是“改革”了。他不是理论家,他只是个实际工作者,但他的实践已有了更广阔的理论上的意义。他是在这种反反复复的过程中理解了这种意义的,渐渐地还发觉己的理解甚至超越了当初那些人对之作出的解释。他已隐约地看到了一条“改革”之风赖以刮起的广阔的历史的地平线了,可别人却没有看到,于是它在他自己的视野里也变得模糊了。
然而在这个冬天里,在他的深深的反思中,这条地平线却又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巾国需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这场“改革”的风暴刮起后将要摇撼的,甚至要伤害和摧毁的原野上的那些旧有的存在物。他是站在一种新的角度来珂解自己这类“改革家”的逍遇的。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这样倘起来而你却搞起“改革”来了呢?为什么你心里老有一种卢竒,不让你不甘寂寞,平庸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问题还不完全在这种使命感上,问题还在于那种仿佛来自生命本能的呼声:你不能将一生虚掷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为它留下一些什么。二者合为一体,使你不能不意识到你做的事情其实就基历史。你正在创造历史。而那来自对面强劲的风也是一种历史的力量,于是你的遭遇也就是不奇怪的了。你的生活舞台不应该再局限于医院的范围内。一个“改革者”应该寻找更广阔的舞台,演出更庄严更动人一实际上往往是更悲壮―的人生的话剧。那个苍凉的声音仍在你耳边响着:即便这样,你在你可能找到的这种新舞台上演出的日子也不是很多了。
―整个冬天他心里都越来越清晰地翻腾着这些思想!但它们毕竟是些思想而已,就象不断聚积的乌云,还仅仅在高髙的天空中停留着,并没有寻找到可以将它化为雨水降落下来的那一块土地。这天上午,市委那位名叫汪一鸣的秘书来医院找他之前,如果有人具体问到他对医院这次市人大代表选举的釕法,他只会说出一个厌恶而已。象上次一样,市里又特别分给医院一个代表名额的真正原因他是知道的。说实话,从一开始他对这次选举是没有热情的,对它的结局也是漫不:经心的。市里这次仍是要司马丽君当代表却又要在医院再走:一下过场,于领导的意志上虚假地盖上一个“民主选举”的印戳、这些年来,他在“改革”生涯中对中闰社会的特殊结构方式及其弊端的思考越深刻,对这种新的所谓“民主”的厌恶程度就越强。甚至超过了对过去那种赤裸裸的“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的厌恶。赤裸裸的“长官意志”也是一种坦:率,一种诚实。尽管是一种丑恶的粗暴的远率和诚实。而眼下这种“民主”却只让人感到一种蚀透,灵魂和骨。髓的虚伪,一种同样赤裸裸的对人的感情和尊严的愚弄和嘲笑。就:是这样,如果这件事与他没有关系,他也会听之任之的。他。明白在我们这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要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还为时甚远,这里不仅有一个方法问题,还有一个选民索质问题。令人难堪的是这次“民主选举”坯不能不同他有一些干系:他厌恶它,却不能不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当一个一能够使“选举”具有民主和竞争色彩的候选人”巧他不能。拒绝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候一选人名单不是上头指定的,而是院党委和工会方面讨论研究后拟定的。选民。们并不了解这次“民主选举”的内幕,如果医院党委:和工。会不把他作为候选人之一推出来,无疑是会使他打感到惊讶的。从这一件事里,他也又一次真切地感到『那种已在中华民族心理深层激荡起来的历史的力最的存玍,感到了真正的民十意识在哿通中闽人心中的萌生和成长。对于他今天的心境,它也是一种振奋,一种鼓舞。这种感觉在那天晚上的全轉职工大会上尤其强烈。他没打料到会场上的气铽竞站那么热烈,人们的思想竟会那么活跃。选民们对候选人的情况和选举的结果那样关心,使他不能不突然感觉到,当某拽“长官”还在把“民主选举”、作一种继续推行“长宵苡志”的工具时,苦通公民已把它汾戍了芄正行使个人民主权利的机会。他社至也没有想到以己店然会改变初衷,被选民的热情激动起来,不知不觉进入了“角色”,并且寘的按选说的要求走上它席台作了“竞选演说”。而在这时,他对这次“民主选举”的态度也改变了:比起另外那个市里内定的人大代表来,他不是更奋资格当选吗?能将岚正代表商己意志和愿望的人推举出来,参予决策本市的遼大问题。从一种更深刻的思想出发,他觉符连选票的多少邡不能说叨问题,真正既能代表群众当前利益,又能看到历史发,玄向并推动它前进的人只会足少数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有深刻洞察,且有强烈变革和开创意识的人。而他口信就进这样的人。
司马丽君却不是。如果他必须承认日己这几年在医院做的一切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那么他对司马丽钌做的事惜就不能不给予一种严仿的否定的评价了。事实上几年来正是司马丽君成了他在阪院推行“改革”的个蜇大障碍,她甚至还成了他的一个莨正的对手。正足,!以沪足有意地坚决地不接受固定工资之外的劳动报酬,他那一藝严格的资动制度才没能在医院得到彻底的实行。她是一位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的母亲,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全国闻名的肿瘤科大夫,当她对他的一套“改革”措施置之不理时,何方还发觉日己居然也没有办法“动”得了她。真的危险是:这几年在医院里,扩大一点说在社会上,司马丽君就象另一面同他的旗帜颜色截然相反的旗帜,奄不动摇地竖在那!以她那种仍被广泛称颂的自我牺牲精神影响苕周围的人。于是在陔院里乃至于本市范围内就有了两种互相对峙的―问样颇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他不能不迮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不管司马丽君足为了仆么原因坚持这种生活方式的,她的这种生活方式本荮都成了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从思想根难上动摇和干扰着他对于改革的努力,他在医院实行的“新法”。直到今天,何方仍坚持己几年前的那种观点,即认为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甩,乃至于今天仍在打仗的南部边聩的战场上。司马丽君身上的这种所谓的“自我牺牲精神”楚必要的,可贵的,徂在和平生活中,再倡导这种精神连同司马丽君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不实际甚至有害的了。妇根结底生活在和乎环境下的人更渴望安宁、幸福、舒适、自由、更充分的物质和精冲的满足,而不希望存人将他们的生活变成一种苦役,一种没完没了的不幸。牺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这种不幸,是对个人的幸福的损害。何方还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起推动作用的力量不可能是这种“牺牲楮神”而是那种能满足和刺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梦想的经济的力量,赤裸裸地说就是货币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能使人们从本能的对幸福的向往的基点上出发,树立健康积极的劳动态度,自觉服从健全的劳动体制,从而更有力地促成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恰恰又是其它领域发展的基础。
司马丽君不应该走进人大代表的行列,事实上她本人已成了“那种反历史的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什么他不应该取代她走进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呢?!
但是职工大会后他对这件事又冷淡了。他知道选举时他得票最多,第二天上午,工会主席就将结果报告给了医院所在的区委,却一直没向全院职工宣布,原因何方是清楚的:工会主席分明估计到这样一个结果是“上头”通不过的,向群众公布后就“被动”了。报告还是要如实报告一下的,因为这件事同何方院长有关系,从院长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他并不是不想当这个人大代表的,如果“上头”把这份报告退回来,让医院党委“重新研究”一下,那就是“上头”的事了,同他这个工会主席没关系了。他甚至还把有关这次选举的材料全部密封在一个大牛皮纸袋里,送到院长的办公室。何方心里清楚:司马丽君最后仍会当上这个人大代表的,“上头”的意志一定要实现。如果医院选出的代表不是司马丽君而是他,市里肯定是通不过的。这个冬天里,市委一位主要领导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否定了他在医院的“改革”,甚至还怀疑他个人的品质“有问题”。
真正使他的热情冷淡的原因别人是猜不透的。这天晚上,职工大会开过之后,他回到宿舍里,不知为什么又想到了司马丽君。开初是淡淡的,后来他的心就一阵阵剧痛起来。
猛然想到了多年前在章玉歧追悼会上她那场冰山崩塌一样的味啕大哭,那惨痛的不时抽搐一下的丑陋的嘴角。想到了第二天早上在门诊部大楼前红叶翻飞的甬道上看见的她那鬌边的儿根凌乱的令人惊心的白发。还想到了那棵树干半枯的老树,斜斜地扭曲地伸向天空的一根残枝上飙挂的一两片绿叶,冬天来了,风雪将一片树叶吹落,他觉得这棵树就要因此而死去……不,奇怪的是,到了今天,那棵老树依旧倔强地活着,而那片巳经飘落的,一使它赖以存活的树叶居然还似乎在枝头上挂着,闪烁着连死祌也没有夺走的生命的绿色!
过去一直觉得,这个身世凄凉的女人数年来之所以能坚忍地活着,坚持着那种以自我牺牲为内容的生活方式,除开表面的原因外,其中还不能没有一种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更深刻的神秘的原因。现在他突然模糊地意识到这种神秘的原因是什么了!
因为这棵老树还坚忍地活着,你才会觉得那片叶子还一直引人注目地在树梢头悬着……
也许这个世界上谁也没苻他更了解司马丽君。但是即便是他,对她的内心生活的了解也是有限的。在这个冬天,如果他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已到了人生的暮年,那么司马丽君就更衰老了,已将不久于人世了。司马丽君数年来过的这种,儿子并没有给她自己带来幸福。她是很看重自己的荣誉的,包括这个市人大代表的头衔。既然这样。他有什么权利不让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一次得到她渴望得到的东西呢?
第二天上午他上了班,他不想再为这件事费神了。事情会不了了之的。有一天区里会打电话来,通知司马丽君在某月某日到哪家宾馆报到,参加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何方没有想到,市委竟会派一名秘书专门为选举的事到医院来找他。
“何院长,市委领导让我来问一下,你们这儿的人大代表选举是怎么回事。司马丽君大夫的票数好象不至于那么低吧?”这位叫汪一鸣的秘书刚走进来,就用一种冷淡的、公事公办的口吻说。“芪院党委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刹那间何方被激怒了。从这番活觅,他又清楚地听出了市委那位领导对他个人品质的怀疑。他拿出工会主席送来的那只装有医院职工大会选举材料的牛皮纸洁袋来,冷冷地放在写字台上,推给坐在对面的汪一鸣。“都在这儿呢。你宥看吧。”牛皮纸信袋的背面,写着这次选举的结果:
何方:217票
司马丽君:101票
秦书磊:43票
肖淑琴:15票
汪一呜将这些人名和数字抄在小本子上,站起来,又冷淡地说了一遍:
“这件事因为跟何院长有关系,我就不好多说了。不过……我认为医院党委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司马丽君这个人选。这样做对医院有利。”
汪一鸣走后何方在办公室里急速地走动了两圃。他突然恼火地想到:事实上他必须同那种时时在左右局势的反历史的力量进行斗争。事实上这种斗争始终在进行。不,他不能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是司马丽君就不当这个市人大代表了。如果他们这些立志改革的人不参政,改革永远会搞不成的。他要寻找的生活的大舞台就在这里。他应该走上去,呼唤更猛烈的暴风雨,这是历史陚予他们这一批“改革者”的使命!
他重新坐下来,点上一支烟。而这时已经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医院党委为了应付市委的查询还是要再开一次会的。会上说不准会有不同意见。但他有办法做到让自己当上这个人大代表。毕竞眼下公民的民主意识不同往常了,即使市委的那位领导也不敢随意否定医院职工大会的选举结果了,所以才派了这个秘书来。作为一个“改革家”,他能依靠的就是这觉醒了的群众的民主意识。他决定晚上开党委会讨论这件事。但在开会之前,这个下午,他就要找人先把这次选举的结果写出来,张贴到医院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去。他要先把这一锅生米煮成熟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