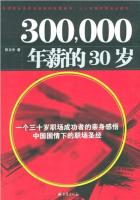大编辑伊莲颇有知性女性的风韵。我给她送过一本打印稿,她浏览了一下,给我一小时谈谈。伊莲暗示,只有顶级大作家才能有劳她这个一级编审的大驾,所以我提前赶到大楼外闲逛,预约时间到了才敲门,一开始就保持着外乡人和文学青年的双重谦卑。
伊莲拿出我的稿子,不客气地说:“你有潜力,语感不错,有质感,有张力,接地气,也俏皮。还算有点小聪明,但毛病也不少,不够精致,不够纯粹,不够大气,还臭婆娘的裹脚……”
我点头哈腰:“我今天就是看病来了——还专家门诊呢。”
她笑言:“你看病,得挂号,专家门诊更贵啦。我还免费呢。”
“深感荣幸。”
伊莲让我坐在她旁边,指着书稿第一章,一句一句地给我讲解,一个词汇一个词汇地分析,甚至连标点符号的用法都不放过,又是举例又是论证。伊莲的分析有些十分有说服力,有些却让我犯嘀咕。她说:“我虽然不太赞同古人文以载道的说法,太正经了,但也不能格调太低信口开河。”
我贸然辩解:“写东西时哪管什么格调不格调,当年您谈恋爱,难道先从爱国谈起?哦,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别给我耍聪明。”伊莲说,“这是王二的意思,你也想死后才被承认吗?”
我赶紧圆场:“爱玲说了,出名一定要早啊。”
“是啊。”伊莲接着说,“你既然引用王二的话,我也引用他一句:好的文字应该有着水晶般的光辉,仿佛来自星星。什么意思?点燃自己,照亮别人。”
我觉得她有些曲解王二的意思,只好绕着弯说:“二爷我很佩服,也很激赏痞爷的说法,玩文学,就要舍得自己,千万别拿自己当人,姿态要低于常人。换成我的土话就是:搞文学,不要被文学搞。”
伊莲笑起来:“你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怎么这么下流啊?”
我急了:“您误解了,下流是粗俗的风雅,下作是人品的卑劣。人可以下流,但绝不能下作。”
她把笔在稿纸上一拍:“是你教我还是我教你啊?”
我赶紧说:“您说您说,我想起了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也是女的。”。
伊莲嗔怒道:“我堂堂国家一级编审,就这水平呢!别忘了,我做编辑之前,已经是作家了。”
我一下蔫了。伊莲花了整整两小时,才分析完前几页。她停下来说:“你的稿子我只看了前几章,成绩大大的,问题多多的,你呀,把稿子拿回去,按我的办法,从头到尾改三遍。”
“天啊,那得改到猴年马月啊?我都已经改麻木啦。”我尖叫起来。伊莲有些不悦:“小伙子自信是对的,但到我这儿你就要碰壁。要想在我这儿出,你就得听我的,多少大作家都得听我的,你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
我赶紧说:“我知道您的好意,严师出高徒嘛,只是——”
她打断我:“我还没说收你做徒弟呢。只是——只是什么?”
“我不想再拖了,这本书已经怀胎六年了,就是打印成册也已经三年了。”
“《红楼梦》还十年磨一剑呢,这就受不了啦。”她笑,话锋一转,“你是不是有经济困难,我可以支持你,先支持你一千块钱怎么样?——我支持过好多文学青年呢。”
“您真是文学青年的恩师——应该叫圣母啊。”我赶紧道谢,婉言谢绝了,“打小我妈就教育我借钱要忍,还钱要狠。我还撑得住。”
伊莲:“那你就照我说的去改,我想了想,我把你包装成‘美男作家’吧。”
我大吃一惊:“开玩笑吧您,‘美女作家’不都臭大街了吗?再说就我这歪瓜裂枣小胳膊小腿,还美男呢。先别问党和政府以及广大读者同不同意,——城管和小脚侦缉队能放过我吗?”
伊莲大笑起来:“党和政府管不上你这事,城管也只管乱摆乱放的。读者嘛,就看我们怎么引导了。你坯子还是不错,有可塑性。”
我难为情地说:“我不是妄自菲薄,只是觉得和一帮作家比外貌有点搞笑。男作家大多很丑,这参照物也太寒碜了吧?从来没听谁拿自己和武大郎比英俊,然后还自鸣得意。”
她有些不悦地说:“作家当然跟作家比啦,总不能鸡跟鸭比吧。你不乐意?想这个头衔的多的是,光北京住地下室的准作家,就有十多万人。”
“您说得有道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我赶紧挽回,又顾虑重重,“咱们这么冠冕堂皇的出版社,这样炒作合适吗?”
伊莲严肃地说:“美女、美男,再加上猛男怎么就不严肃了呢?关键看是不是健康的美。你说人体画怎么区分色情和艺术,不就在于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引起正面的积极的愉悦的美感吗?”
看着“文学圣母”严肃的样子,我油然而生神圣的殉道感。我像一个即将送往前线充当炮灰的国民党军官对蒋委员长效忠:“感谢您的栽培,为文学献身,我深感荣幸!”
“这还差不多。”伊莲满脸愉悦。我忐忑不安地说:“我有个惟一的要求。”
“说啊。”
“只卖艺,不卖身。”我脱口而出。伊莲爆笑:“当然,谁让你卖身了?就算你想卖,谁买啊?一天还得三顿饭。”
我一路狂奔地回到“家”,按伊莲说的办法认认真真地改了几天,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按她的要求,即使我每天工作十五小时,至少一年半载才能改完。
地下室房客构成复杂,但有两个共同点:外地人,没钱。邻居是一对职业贩卖假证件的夫妇。城市里铺天盖地的牛皮癣广告就是这帮人的杰作。每天,男人从回馈中获得交易机会,谈妥后冒着被抓的风险去接头,女人则以孩子为掩护就近兜售。混熟了偶尔串门,他们毫不掩饰其生意,拿出五彩缤纷的证件让我们看。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神奇的国度居然有几百种证件。我随手拿起几本:“父母光荣证”、“节育证(上环证)”、“火化证”和“党员证”,几可乱真。女人很殷勤地拿起一个“士兵证”和“残疾人证”向我们推销:“这俩证很管用,坐公汽、去公园一律不要钱。”
男人拿起“警官证”,一脸诡秘:“有了这东西,小姐随便玩,白玩。”
“不错不错。”我指着顺子问老板,“有处男证吗?他需要一个。”
顺子落荒而逃。
地下二层入口写着B2,让你感受到双重压力,听起来却牛逼烘烘,活像一处战略要地或美军战略轰炸机。此刻,B215室里,三流歌星的声音从梁顺子的破电脑连接的破扬声器里传出来,在这个防空洞里异常低沉而有穿透力。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拖鞋的我一摊稀泥似的躺在单薄的小铁床上,一阵头昏眼花之后,头顶那盏惨白而咝咝作响的日光灯渐渐清晰起来。蛾子和蚊子在头顶盘旋。几场大雨后,室内骤然潮湿起来。一些水滴在墙上凝结,房顶的水滴开始下坠。地板上开始打滑,穿着拖鞋常常差点跌倒。我用墩布不停地吸水,最多管两个小时地板又冒水了,我就必须到厕所拧干墩布再擦。渗透最厉害的是房门口,必须放置木块或砖头才能防滑。床上湿漉漉的,湿气通过皮肤渗进肌肉,引发阵阵刺骨的凉意,让人担心患上风湿性关节炎甚至心脏病。我们找来报纸覆盖在床单上阻隔和吸收湿气,报纸上的铅字和图片很快油污一片。一有太阳,立即将床上用品拿到地面小树间拉起的铁丝上晾晒,稍微去迟了就没位置了。
每晚睡觉之前的必修课是消灭蚊子。几场大雨后,蚊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进攻性,不胜其扰。我们都没蚊帐,都厌恶蚊香味道,试了几次蚊香也无济于事,干脆奉行坚壁清野就地歼灭的政策。我们的战术是关闭房门,靠双手和旧杂志空袭蚊子。对一些停歇在屋顶或高墙上的蚊子,我们练就了空袭的绝活。一般是找一本旧书或杂志——一定要有分量,要结实,然后从垂直于蚊子的方向突然向其猛地掷出,一般成功率可以达到一半。据我们统计,平均每个晚上可以消灭上百只蚊子。其中入睡前能够消灭百分之八十多,其余躲藏起来的近百分之二十必须等黑灯后一段时间,突然开灯来个“闪击战”。通常,这样的“闪击战”要进行三到五次,才能基本肃清敌情,然后清洗沾满蚊子鲜血、生疼的双手,愧然入睡。一个月下来,这间屋子的墙体上便蚊尸遍野,血迹斑斑了。谢天谢地,在这个坚固的地下室里,因为缺乏食物,没老鼠出没,蟑螂也偶尔才见。
每天早晨醒来,看着粗粝的天花板和空无一物的四壁,呈现出死一般的静谧,只有那盏异常发白的日光灯灯管,被一两只飞蛾锲而不舍地撞击着,发出“噗噗”的微弱声音,不由得产生自我否定的幻觉……在这个隐秘的地下室,要是哪天眼睛一闭再也睁不开了,也算是彻底解脱啦。这念头让我不寒而栗。
就这种“诗意的栖居”,还TMD“美男作家”呢,想起来就咯咯咯大笑一阵,直笑得热泪盈眶。这荣耀还是让贤吧。我决定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书不能出,任何努力都是白费。此时的我比任何人都明白那句西谚“Publishorperish.(不出版就完蛋)”的含义。
我见了几个书商,看上去都形迹可疑,公司规模很小,有两个居然就一间办公室。他们咋咋呼呼地和我东拉西扯一阵,拿出一份合同,我一看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条款。我拿起合同,佯装感兴趣的样子,说回去研究一下,出门就扔进楼道里的垃圾桶。
腰包和身体日益消瘦,除了后两月房租,几乎空空如也了。但我既没向北京的朋友借钱,也没向家人伸手——反而常常打电话报平安。我既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又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者。当你把生活当成一场生存试验时,一切都会变得有趣,你的潜能也就不可思议地爆发出来并让你获得莫名其妙的成就感。
我开始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先是热水澡改成凉水澡,夏天这个不成问题,我和狱警一样的房东谈好,冲一次凉水澡一块五,五分钟洗完。然后每天两顿正餐改为一正一副。通常是将早餐由稀饭面饼改成一张小区内随处可见的煎饼果子,或附近“京客隆”副食品店熟食橱柜的一个夹心饼,都可一元内搞定,比到房东锅里舀一碗杂碎汤什么的还便宜。路边摊专供民工的馒头,三毛钱一个,就着四川榨菜或辣椒酱,喝一杯茶水,也是一顿早餐。我头一周一天两餐伙食的最低纪录是一小张陕西凉皮、一根黄瓜和一根煮玉米棒子,加起来不到两块钱,但很快这个纪录就被刷新了:一根黄瓜做早餐兼午餐,一个烤红薯做晚餐,直接和撒哈拉南部非洲同胞看齐。这样的营养和热量,居然还能支撑我繁重的脑力劳动。看来监狱里果然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但我不敢连续吃烤红薯,不是我受不了,而是糟蹋空气,使我的环保主义理念破灭;还蹂躏情绪,让我无法入定。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挑战一天一餐。这个有相当难度。我试验了几天,除了胃囊收缩剧痛,脑子也几乎处于空白,两眼浮现幻觉,耳朵发生幻听,肉身更是瘫软如泥。我忽然从动物冬眠的现象得到了启示——早睡晚起,这样可以将热量消耗降到最低。于是下午三点左右起床,先是猛喝一肚子水,五点左右猛吃一顿,晚上九点就睡。晚上尽量少喝水,要不起夜后,胃囊里的饥饿会像鳄鱼牙齿似的活活撕咬你,你就别想再入睡啦。我有过一次这样的折磨,奄奄一息时,想起了饿死的诗人朱自清,幻想着羽化成仙,和他们在天堂里相见。如果不是因为改稿,我说不定还会尝试两日一餐呢。白领梁顺子和我一样俭朴,他吃起这些粗鄙食物来,和我一样开心。惟一的不同,他每天有一顿工作餐。
减少进餐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减少上厕所的机会。这个地下室最恐惧的就是上厕所了。上百人的地下室,男厕所有三个隔断,大小便均在里面,有时候还有人在里面洗凉水澡,所以起床和入睡前的出恭高峰期就如同一场田径接力赛。通常是一个人在里面“轮蹲”,你在外面排队排到隔断门,急得你跺脚捧腹屁股抽筋,嘴巴里直嚷嚷里面快点吧,里面就嚷嚷,急什么啊还没完呢,你要哥们儿肛裂是吗?里面刚起身,外面的你或别的人就解着皮带或捏着鼻子捂着嘴巴迫不及待地侧身塞进去,瞬间,你就可以听见一阵沉闷粗鲁的噗通声和舒坦悠扬的呻吟。
一次,遇到一个窜稀的家伙,大呼小叫一阵,实在忍不住了就冲进了隔壁女厕所,引起一片惊叫和厮打声。这个强壮的搬家工硬是一边挨着劈头盖脸的谩骂和厮打,一边辩解“我不是流氓我只是忍不住了……”一边完成了高难度减负流程。他超强的功夫连闻讯而来的警察都佩服,房东夫妇和一些房客也为这个倒霉蛋说情,加上他满脸的抓伤,警察从轻发落了这场由一泡秽物引发的血案,只是狠狠训诫了一番,放过了他。
尽管可以冲洗,还有一个通风口,公共卫生间依然臭气熏天。总是有人不把秽物排泄到位,总是有人将口痰吐到地板上、便槽上或木板上,总是有人便后不冲洗,总是有人忘带手纸就将秽物揩在木板甚至水泥板上,功夫高强匪夷所思。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任何失去明确产权的东西,哪怕是暂时的,后果都异常严重。由此对于让我沦为社会贤达的伟大改革,又多了一成敬意。
没多久,我们这些久居地下室的人,就像城市里的坑渠鼠一样,日益面如菜色,头发失去光泽,骨头也突了出来。我想到了我的末日和死亡方式。首先是饿死,又觉得不太可能。在这个物质极其丰富的年代,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和体力之前,肯定会自救或被救。被人杀死?也不太可能,杀人是有动机的,为财或为色。这里穷得连一只老鼠也没有,女人瞄一眼都嫌多余。中毒或淹死?有可能。这封闭和低洼之地,最有可能的是燃气泄漏或洪水倒灌,都会让我死得很惨,全身发青七窍流血或者泡成癞蛤蟆。地震也不是没可能,北京就在地震带上而且这地下二层离震中还近了十米。一旦地震来临,十秒钟之内,头顶上二十多层成千上万吨钢筋水泥直挺挺砸下来,顷刻之间将我化为齑粉或肉饼。一千年后,考古学家可能会在这里发现一具支离破碎的人体化石,从我残存的胃囊里提取微量残存物,分析出一千年前繁荣瓷器国国都的社会万象。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依然天天去小区外的报栏看一个小时报,有时候到附近的证券交易厅看看行情,要么就躲在“家”里或到小区石凳上躺着看金庸小说。那套金庸全集和一堆《圆球时报》就像梁顺子的命根子,一回来,不是捧起金庸,就是掏出“圆球”,连自慰都敷衍了事。
金庸的作品除了断断续续看过几集电视连续剧,基本是个空白。说实话,要不是梁顺子的一再推荐和穷极无聊,我都懒得看一眼。中学时看了《霍元甲》之后,我就对武侠、武术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绝望。看了金庸小说,我对武术和武侠小说更加蔑视,那神乎其神的描述,让武术更像巫术。出于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对韦小宝这个下流坯我还是有点喜欢。但在这个治安高危的地下室,我绝对不能对梁顺子说任何金庸的坏话,弄不好他一时激愤,在我熟睡之际,拿我做他的神功试验品也说不准。
十多年前,我也看这份“外国一片糟糕,风景这边独好”的报纸,差点没看成脑残。梁顺子在看这份报纸时,经常硬给我塞一张,分享他的意淫。他常常发出的自慰般的笑声让我惊讶不已。这一次,躺在破床上的他突然来了个鲤鱼打挺,大笑:“打呀!打台湾哥们儿捐一个月工资,打以色列哥们儿捐一季度工资,打美国哥们儿捐一年工资,打小日本——哥们儿当一辈子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