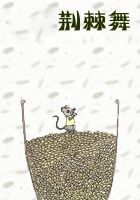姐姐了解弟弟,临阵脱逃去的地方她猜到了,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丛天舒对主持人说:“别等了,时间不够用啦,现在换人来得及吗?”
“我们婚庆公司有替补伴郎伴娘,刘总,您看?”主持人征询道。
“好吧!换人。”刘国强说。
“你说这天飞亲朋低声议论道,“到了刀刃上,他掉了链子。”
“可不是咋地,还得现据兑伴郎。多耽误事!”一个朋友说。
也有亲友说天飞做事历来稳当,不会出这种事。谁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丛天飞当不成二姐夫伴郎的现实。当地风俗姐姐出嫁,新娘的外甥押车,一多那天有课,爱开玩笑的丛天飞自告奋勇押车想发把小财,刘国强说你当伴郎吧,赏五百元。小舅子便答应了。
接张景云比五百元钱有意义,他才临阵脱逃。
车还没下高速公路,城市的轮廓渐现,丛天飞说:“我们直接去大富豪酒店,能赶上婚宴开席。”
张景云摇摇头,说:“还是送我和景锁回家。”
“大家都盼望见你,刘国强你们还没见过面。”丛天飞劝道。
“以后,以后有的是见面的机会。”张景云推辞,说,“亲戚做成,相处的日子长着呢。”
看张景云不愿去,丛天飞没再逼他,说:“我顺便买只熏兔,到你家和张叔一起吃。”
“那不成!天飞,”张景云反对道,“你必须马上返回婚礼现场。”
“你不去,我就不去了。”
张景云摆道理:本来你答应做伴郎,偷偷逃跑……天霞只你一个弟弟,她的婚礼你怎能说不参加呢?据我所知,从小两个姐姐就一直呵护你,关爱备至。
这一点丛天飞不否认。他牢骚道:“但是她们却不顾你怎么想,一切都是她们安排,大多是强加。就说你知道的吧,两个姐姐去做什么美体瘦身,竟看上人家小老板,生拉硬扯我们谈恋爱,结果,一开始就注定了不欢而散的结局。接着她们在几年前又给我安排恋爱没商量,硬把妇婴保健院的女护士天骄……”
“也许她们有些霸道、武断……可是今天你从婚礼上逃跑,说到哪里你也失礼,应向她们道歉才对。”张景云说。
“要道歉的不是我,是她们应该向你道歉。”丛天飞抱不平道,“你为我大姐在里边蹲了三年,三年啊,今天你出来,多重大的事情,她们却无动于衷。”
“与天霞婚礼赶在一起,哪个事大?”张景云批评道,“天飞,今天是你不对,何况做伴郎是你答应的,怎可食言?”
“终归是大姐二姐的意思,她们阴谋好的,让刘国强直接对我说选我做他的伴郎,新姐夫吗,我咋好直截了当地拒绝他?”
“于是,你就来个‘临阵脱逃,。”
“大姐忙没时间来接你也罢,应该安排我来接……”丛天飞仍然对大姐不来接张景云出狱耿耿于怀,“景云,你别再说啦,一会儿路过市场我买菜,咱们跟张叔一起喝酒。”
一顿丰盛的酒菜,张景云亲自下的厨。
“爸。”张景云给父亲倒酒,侄子二多坐在他的腿上,他夹菜给他吃。傻弟弟大啃一段鸡脖子。
张建国凝望儿子,很多话语都在目光里。
“爸,喝酒。”张景云说。
“喝酒,天飞喝酒!”张建国缓过神,说。
老贾这时来了,张景云喜出望外。
“景云,听说你今天到家。”老贾说,“哦,你们吃饭,看我赶你们饭碗子。”
“是老贾吧?”张建国对撇子(对心思)的人来了,高兴道,“赶紧进来,我跟你喝两盅。”
老贾刚迈进一只腿,胖婶也赶过来说:“落一屯,别落一人。”
“胖婶,一起来!”张景云将一双拖鞋扔给胖婶,说,“胖婶,我正愁绿豆芽炒不好呢!”
“小菜一碟,醋烹素炒,我炒豆芽拿手。”胖婶得意地说,进屋扎起围裙。
“老贾,这酒咋样?”张建国喜遇酒友,兴趣地谈酒。
“好酒,好酒!”老贾抿一小口,称赞道,“我在门外就闻到酒香啦,曲香味。”“我放了十几年的三江大曲张建国储藏几瓶白酒,特殊的日子他才肯拿出一瓶,“你鼻子真好使,老贾。”
“闻酒味,我有特异功能。”老贾说。
胖婶端上炒豆芽,说:“尝尝我的手艺,素炒豆芽!”
“来吧他胖婶,也喝一口。”张建国说,他今天心情特好。
“好,喝一杯你家的茅台。”胖婶风趣地说。
张建国自诩储藏的白酒是茅台,所以胖婶才这么说。
“拿茅台跟我换我都不换。”张建国说。
他们热闹地喝酒,饭后人便散去,剩下张家人。张母带回来一些鸡、鸭、海鲜。她说:“天霞、国强特意叫给你和景云带回来的酒菜,趁热吃吧。”
张建国冷眼看菜,说:“中午我们刚喝完酒,等天舒晚上回来一起吃吧。”
“那就凉啦。”张母说。
“凉啦,凉了再热!天然气没涨价。”张建国气粗道。
“我不是说了,天舒跟我说急去谈一笔业务,客户是女的,晚宴老总叫她陪客,回来时间不确定。”张母见老伴因天舒不回来生气,解释道。
张景云抱着小侄子二多,他抬头目光与母亲相遇、交流,母亲向儿子传达的某种信息,被他准确捕捉到,并理解。
“来,奶奶一天没抱二多,奶奶抱抱。”张母抱过孙子。
张景云放下侄子,来到桌子前,强颜作笑道:“爸,中午只顾喝酒我们没吃多少东西,咱们吃点儿?”
父亲理解儿子的意思,没在怄气下去,说:“吃吧。”
张家人围在桌子旁,桌子上摆着婚宴的美味。
“妈,你吃点儿。”
“我刚撂下饭碗,你们吃。”张母说。
张景云伸手撕熟鸡,放进父亲碗中一只鸡大腿,另一只给了张景锁,自己拿起块鸡胸脯,大吃大嚼,嚷嚷道:
“好吃,盐水鸡太好吃啦。”
“好吃,好吃!鸡……”张景锁跟着傻喊。
张母急忙抱起孙子进里屋,她眼里噙满泪水。
丛天舒走出西点屋,走向停在近处的出租车,服务生提一大蛋糕盒,送上车。然后到鲜花总汇,她买了一个大花篮。
望情水酒家的一个包厢里,丛天舒往大蛋糕上插蜡烛,点燃蜡烛,朱刚坐在蛋糕前,面对烛光。
“祝你生日快乐……”丛天舒道。
朱刚一脸的幸福、兴奋神色。
“吹灭蜡烛前,你许个愿吧。”她说。
朱刚双手合一,微闭双眼,微笑,慢慢睁开眼睛,说:“我好幸福!真幸福!”丛天舒深情地望他。
“天舒,”朱刚动情地说,“我看到以前的你,像似在春天的细雨中,听到你在呼唤我……”
她沉醉在柔和的气氛中,倾听他叙述:
“音乐老师挨打的事你还记得吧。嘿嘿!那天他晚间上街,有人躲在暗处,给他一砖头子……”
“后来也没找到打他的人。”她说。
“你说他这个人该不该打?老师给女生书包里塞情书……”
丛天舒猛醒,说:“打音乐老师的就是你呀!因为他往我书包里塞情书的事,我只对你一个人说过。”
“当时谁要是对你有丝毫的伤害,我都会……”
“那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呢?”
“我不敢。”
“也许那时你说了,我们又是一种结局。”丛天舒意味深长地说。
朱刚中学时代倾心她,不敢大胆表露也正是因为倾心。处在含蓄的年代,可以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当然错过爱情就是错过了流走的水,再踏进时已物是人非,世间没有飘逝的东西能真正找回来,何况他没有找寻的意思,他努力@留学生时代丛天舒的形象,美好在心灵深处一辈子。
丛天舒心情复杂,多少有些后悔,那时朱刚不在自己的视线里,充其量在边缘游走。
“奶奶把我带大,她会很多民间歌谣,常唱给我听。”生日烛光中的朱刚,怀旧的情绪咖啡一样浓,且苦。
“能唱一段吗,我很想听。”她说。
“词儿我还记得,只是调儿唱不准了。我就背诵给你听:小白菜,地里黄,两三岁上没了娘,跟着爹爹还好过,就怕爹爹娶后娘……”他嗓音发噎,眼里汪着泪。
“怎么啦,朱刚?”
朱刚哽咽,关心他的人在他三岁时到另个世界去了,双目失明的奶奶把他接到身边……他一生最渴望得到一个温暖的怀抱,在那里享受阳光和爱。
“你找到了吗?”
“奶奶去世后,我像一根芦苇,在风吹雨打中摇曳,苦苦地寻找……”
“罗薇的怀抱不温暖?”她小心翼翼地问。
“我原以为那里是温柔乡,避风港……天舒,我感到冷冰,从心里向外冷,冷得瑟瑟颤抖。”他凄然地说。
她递给他一块纸巾,他揩下眼角,说:“走进罗氏家族,事实证明我犯了致命的错误。你问我罗薇的怀抱温不温暖,如果那也称得上是女人怀抱的话,投入进去,恐怖与之日夜相伴,整日战战竞亲。生活在财富家族的阴影下,尤其是女人摆布下的男人,有幸福可言?没有,没有啊!”
丛天舒真的不懂,他身为一个集团的老总,有别墅有高档轿车,拥有财富,竟然说不幸福。
创伦理小说“什么都有,却缺一样,”朱刚反问她,“有爱情吗?”
丛天舒一字一顿地重复道:“有、爱、情吗?”
“没有!你看我在公众场合很潇洒,也很男人。但是,你没瞅我的眼睛,面带微笑,眼里含着泪啊!”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处境。”
朱刚发自内心的慨叹:普天下的男人心里都有一本心酸账!天舒,人需要财富,更需要太阳,需要温暖!
证明朱刚的理论并不难,张景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似乎心酸不足以说明今晚他的心境,血泪更为贴切。
张家棚顶灯光幽暗,侄子一多亲昵地依偎在张景云身旁,他哄侄子睡觉:
“睡吧一多,明天上学!”
“二叔,你这次回来还走吗?”张一多不肯睡,问。
“不走。”
“太好啦,二叔,你还给我当爸爸吗?”
三年后问这个话题,张景云回答起来倍觉青里,眼下的情形和三年前总是不一样。
“二叔……”
他还没想出恰当的回避答话,张母进来解围道:“一多,叔累啦,你别缠磨他,回你自己房间睡觉去吧。”
“不嘛,我跟二叔睡。”张一多不肯走。
“妈,一多今晚跟我睡吧!”张景云说。
孩子的愿望得以实现而变得兴高采烈,他说:“二叔,我拉琴得奖了。”
“好啊,一多,真有出息!”
“二叔,你听吗?我给你拉一段。”侄子要在叔叔面前表现。
“拉一段吧。”
“你吹埙,我们俩合奏。”张一多说。
张景云从柜子里取出埙,他的目光没离开桌子上放着的那双黑皮鞋,吹埙。小提琴伴着埙,声音悲悲切切,老两口泪眼对泪眼,张母说:“这曲子听来咋这么闹心,今晚景云一直在吹。”
“是啊,景云在外三年,终于回家来……”父亲从另一个角度看儿子,“天舒太令人费解,她始终没回来。”
至此张母道出实情:胖婢听人说,天舒跟一个中年大款模样的人腻在一起,明摆着的事,变心啦。过去天舒穿什么戴什么,钱从哪里来?大风刮来的,不是!卡跟头捡来的,不是!还不是吊大款的膀子。
“吊膀子哈话,是傍大款。”他愣然,老伴眼神流露出未说出口的话:说吊膀子是个文明词儿,其实那是上床换来的肮脏钱,一股下水道味。他说,“我再次提醒你,别对景云说这些。”
丛天舒用自带的钥匙开门,蹑手摄脚进屋。全家人都睡了,室内一片寂静,她进自己的卧室。
张景云房间门虚掩,灯光泄出。丛天舒在他门前伫立些许时候,推门进去。
“天舒。”张景云坐起身。
“景云,”丛天舒坐在他床前的凳子上,解释道,“我今天有事儿,没去接你。”
“天飞接我回来的……”他说。
“巳经很晚了,景云,明天细聊吧!”她起身走了出去。
早晨,张景云轻手轻脚从卧室走出,望向丛天舒的房间,里边静悄悄的。他拎起垃圾袋,出门。
三年不在家,谈不上少小离家老大回,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他觉得几分陌生了。
“景云!”
听见有人叫自己,张景云停住脚步。
“看背影像你。”老贾蹬着三轮车赶过来。
“这么早,你这是?”张景云问。
“去农贸市场开点菜卖,你出事不久,铁艺分社黄了铺。”老贾说黄得一干二净,职工们人都各奔东西。
“大家得到一些……”昨日跟老贾喝酒,没沾这个话题,张景云关心他们的利益。
“补偿?别说补偿了,就连我们集资的两千元都没给退。”
“理由呢?”
老贾望眼张景云,吞吐道:“理由,理由……”
“老贾,有话你直说。”
“说什么?算啦。”
“老贾你怎么变得这样?”张景云有点生气,说,“过去你可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人。”
“景云我俩有啥可瞒的,我不能当别人说的话,都跟你说。只是,这件事,我实难说出口。”
“老贾,你不说我也明白了,与我有关。”张景云猜到了。
“嗯。”老贾点头。
张景云感到惭愧,一时无语。
“其实大家都很了解你,也同情你。铁艺分社刚成立那阵子,是你把下岗失业的众弟兄推荐上岗的。”老贾重情重义道。
“我对不住你们大家,因我受了牵连,遭受了经济损失。”
“事情发生了,也结束了,我就不说了,当初缺钱你跟弟兄们言语一声,大家凑一凑,何必……噢,不说了。最可气的是,铁艺社的王经理,竟把我们二十几个人挑出来,说集资的两千元不退了,你们是张景云介绍来的,他卷走单位的钱,你们替他堵窟窿吧。”
张景云表情复杂,痛苦伴着愤怒。
“景云你可别有精神负担,弟兄们都表示不再提及此事……”老贾解劝道。
“在里边我就想好了,出来重新办一个铁艺社,”他说,“挣钱,加倍给弟兄补偿损失。”
“你办厂可别落下我呀,大家都愿跟你干。”
“办铁艺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待时机成熟就办。眼下,我得先找活干。”张景云志气地说。
丛天舒起床先问张母:“景云呢?”
“到街上走走,几年不在家,城市变化太大,他熟悉一下环境。”张母说。
丛天舒洗漱完毕,坐在小梳妆台前化妆,发现那双黑皮鞋,往脚上比量一下,顺手丢进柜子里,背起包准备上班。
“不在家吃早饭?”张母问。
“来不及,不吃了。”丛天舒说。
金丹坐在办公室看一份文件,工作人员进来道:“金主任!有人找您。”“请进来!”金丹放下手里的文件。
张景云走进来,望着她问:“你是金丹?”
“是你?”金丹愣然。
“三年前的一天下午,你在水库……”
“哦,想起来了,是你!”金丹想起那件快要淡忘的旧事。
“水库出事后,我到处找你,没找到。”张景云说。
金丹让座,亲自泡杯茶端给他。
“谢谢,我叫张景云。”他自我介绍道。
张景云?金丹顿然喜出望外,说:“你是张景云?”
“对呀。”
“我爸讲过你,他被蛇咬了,是你救了他。”金丹说,“那次我去看爸爸同时向你致谢,没见到你。”
情况特殊,他正被关禁闭。
“那天你悄悄离开水库现场,我总想找到你,当面致谢。”他说,“不久前我见到你一次,只是不允许我走到你面前……你父亲给了我地址。”他拿出那条牙齿坠儿项链,“你父亲让我带给你。”
金丹双手接过,笑意立刻从脸庞消失。他注意到了金丹表情的变化,缄默。她的背后墙壁上,是一幅根雕一胡须飘飘的老翁头像,它的下面草书两个字:父亲。
“我爸他好吧?”她问。
“好!他很想念你。”
金丹有些伤感道:“我是他唯一的亲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能想象得到一位老父亲对女儿的思念……可我工作忙,不能常去看他。”
张景云视线移向墙壁的根雕老翁头像,停留在“父亲”两个字上。
工作人员进来说:“金主任!刚收到份文件。”
“先放在这儿,我处理。”金丹说。
工作人员放下文件出去。
“你忙吧,我走了。”张景云准备告辞。
金丹诚意挽留道:“再坐一会儿,五分钟。”
张景云只好坐下,他说:“金丹,你父亲让我交给你项链时,有一句话转告你。见了你的面,我倒觉得没必要转告这句话了。”
金丹信任地点下头,说:“你决定。”
“确实没必要转告。”张景云说。
她给他一张名片,说:“有事打电话给我。怎么和你联系?”
“我没名片,给你留住宅电话号码。”张景云说。
沿人行步道走,张景云留意贴在商家店铺门窗上的招工小广告的内容。一家餐馆窗户上贴出:招切墩工,月薪五百元。他驻足读招工广告。
“景云!”丛天飞开车过来,将车靠近他,“你在这儿,我到处找你,快上车,大家就等你一个人。”
“去哪儿?”张景云边开车门边问。
“高句丽酒店。”
髙句丽酒店包厢内,刘国强坐在餐桌正位置看菜谱点菜,服务员一旁写菜。
“天飞怎么还没把景云接来?”丛天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