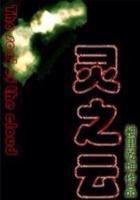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说话。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发出声音。我常常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另一只手去触摸嘴唇,然后发出一些声音。任何有声音的东西,我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也喜欢猫叫和狗吠。我还喜欢把手放在唱歌者的喉咙上,或者用手去按钢琴的键盘。在我丧失视觉和听觉之前,我学习说话的能力很强。自从得了那场病后,因为我听不见,所以也就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我常常坐在母亲膝上,把手放在她的嘴唇上,因为我觉得她嘴唇的动作很有趣;虽然我已忘记了什么是说话,但我也会学着他们的样子蠕动自己的嘴唇。我的家人说,我哭和笑都很自然,有一阵子我还能发出声音,并能拼上几个单词。但我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要与人交谈,而是要训练自己的说话器官。有一个词的意思我仍然记得,那就是“水”,不过,生病后我一直把它发成“WaWa”的音。而且,我那时已忘记了它的意思,直到莎莉文小姐教会我用手指拼这个字后,我才重新弄懂它。
很久以前,我便知道四周的人都用与我不同的方式交谈,在我不知道耳聋的人也可以学习说话以前,我就已经对自己的这种交谈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完全依赖手语的人,总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越来越无法忍受,我极力地想要改变这种束缚。我的这种想说话的欲望,就像一只想要迎风飞翔的鸟儿一样强烈。我坚持着使用我的唇和声音。朋友们一直想打消我学习说话的念头,他们害怕我学不好,那样我会更失望,但我仍然坚持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看到了一线希望——我听到了关于娜希·卡达的故事。
1890年,曾经做过劳拉·布里奇曼老师之一的拉曼逊夫人从挪威与瑞典访问回来后,便来我家探望我,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名叫娜希·卡达的聋盲女孩,她已经学会了说话。拉曼逊夫人还没有说完这个女孩子的成功事迹,我就已经欣喜万分了,我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但单靠我自己练习所取得的进步很小,我的老师就带我去见贺瑞斯曼学校的校长莎拉·福勒小姐,请求她指导我学习说话。幸运的是,这位和蔼的女士愿意亲自教我。
于是,我在1890年3月26日开始跟她学说话。福勒小姐的方法是这样的:她让我把手放在她脸上轻轻触摸,让我感觉她发音时舌头和嘴唇的位置。我很热切地去模仿每一个动作,一小时后我便学会了6个字母:M,P,A,S,T,L。福勒小姐一共给我上了11课。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说出我有生以来第一句话——“天气很暖和”时,我是何等的惊讶和喜悦。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的几个音节,但这毕竟是人类的语言啊!
不要以为,我在这短短时间内就真的能够说话了,我只不过是学会了说话的要领而已。我发出的这种含糊不清的音节,只有福勒小姐和莎莉文小姐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而大多数的人,却只能了解我说的一百个词中的一个。而且在我学会了这些基本语音后,还需要她们的帮助才能完成后面的工作。倘若没有莎莉文小姐的耐心辅导,我不可能如此神速地迈向自然的言语。起先,我日以继夜地苦练,但这也只能令我最亲近的朋友了解我的意思。后来,在莎莉文小姐不断地帮助下,我尽可能地使发音清楚,并用各种不同方法把声音连起来,发出让人能听懂的语言。甚至到现在,她还是每天都提醒我,有些字的发音不正确。
只有教导过聋哑儿童的老师才会明白我发音时的感受,也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必须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观察老师的嘴唇时,我只能依赖手指。我不得不用触觉去把握喉部的颤动、口的动作和面部的表情,而这种感觉往往是不准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惟有重复这些词或句子,有时必须练上好几个钟头,我才能学会正确的发音。我的工作就是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会令我很沮丧,但想到回家后可以向亲人们展示一下我所学到的东西时,我便立刻信心大增,继续练习,因为我期待着他们能为我的成功感到愉快。
“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个念头时刻鼓舞着我,是它让我战胜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在那段时间,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现在不是哑巴了”。我期待着能和母亲自由地谈话,并从她的嘴唇中感觉到她的喜悦与痛苦。因此我不再沮丧,并且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当我发现用嘴说话要比用手指拼写容易得多时,真是惊讶不已。因此,我在以后自己用口说话时,便不用手语了,但莎莉文小姐和一些朋友仍然用这种方法与我说话,因为这样会比让我读他们的嘴唇快捷得多。
或许,我最好能在这里解释一下手语的用处,因为很多人都对它感到难以理解。人们与我谈话时通常使用单字手语,要把字母一个一个地写在我的手上,我感觉着手指的移动,就像你们阅读的时候一样。长久的练习,使我的手指变得很富有弹性,有些朋友写得也很快——好像打字专家使用打字机时一样快。
在我能够讲话后,顿觉归心似箭。终于,最快乐的时光来临了——我可以回家了!在回家的途中,我不断地和莎莉文小姐谈话,这并不是为了闲聊,而是为了利用每一分钟的时间来提高我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抵达多斯康比亚站,我的家人在月台上拥抱了我。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了解我所说的每一个音节,她以一种无言的快乐,将我紧紧地抱入怀中。我的眼中也充满了泪水。米珠丽也能听懂我所说的意思了,她也拉着我的手吻了一下,高兴地跳了起来。当父亲以沉默的拥抱来表达他以我为荣的感情时,我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实现了:
“高山和丘陵要在你面前爆发,为你歌唱,原野中所有的树木也将为你拍手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