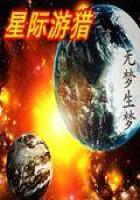爸从青岛回到天津不久,来了两位冯姓表哥。爸请他们一起吃晚饭,家人都很高兴,因为有将近两年没见面了。
妈在厨房忙开了。她知道两位表哥口味高,得让他们吃好、喝好。
“张妈,洗酒杯了吗?老爷可不许酒里掺水。一滴都不成。”
“记着哪。”张妈说,“我看这酒不够喝的。莲花白还剩一点儿,双溪陈酿也只半瓶,大表少爷又那么能喝,还得再打一坛子陈酿和虎骨酒。”
妈让张妈从地窖里拿一坛子陈酿,她说虎骨酒冬天喝好,这会儿都打春了。虎骨酒由黄榅桲和几种草药酿成,能舒筋活血,强身健体。
张妈拿了两大坛陈酿。酒坛用竹网包着,上面有两个竹提手,拎起来像个大篮子。坛口封了几层纸,上面糊着一层厚厚的泥。据说这种泥是精心调合的,专用来封酒,可使酒香不跑。
双溪陈酿有股特殊的香味,介于水果香与花香之间。我爱看他们先洗了手,然后小心地揭去封泥,刚一拿开盖子,屋里便溢满一股沁人的奇妙酒香。每当我嗅闻着山上浓郁的野花香和阳光送来各种植物的馨香时,总不禁联想起这种奇特的香味。
“我先尝尝。”妈接过一小杯酒。我见她的嘴唇红润好看,知道酒一定很香。妈把杯子递给我,说:“你着急了是不是?去搞些‘笑兰’的嫩花苞,撒在上面。等明儿早晨,就会香味扑鼻。若放在枕头底下,准保你梦着酒仙。”
妈说话常能丰富我们的想像。
妈耐心地看张妈把坛子里的酒倒进瓶子。这种酒瓶多由白镴或白银制成。中国黄酒用大米酿造,味似葡萄酒,喝前先放在热水里温一会儿。它常用来佐餐,能喝酒的人一顿饭就能喝上五六十杯。
两位表哥是大妈的侄子,都很有才华。我们在北京住时,他们常来。大表哥康贤比二表哥康光年长两三岁。他当过驻欧洲几个国家的总领事,通晓数国语言,回国时才三十五岁。虽然他常穿中山装,可他留的胡子和油亮的分头总让我们觉得他是个洋人。而且,他还爱拄着根文明棍,说话时横在手里,好像随时要打谁,有时令人讨厌。他进屋便脱了帽子,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倒使我们有机会戴着它玩。不过,我有点替他的秃头顶感到难过。
康光当时只有三十岁,个子比康贤矮些,讲话很快,与论敌争辩,言辞犀利,诙谐睿智。他虽年纪尚轻,可资历不浅,在北京上层社会很有地位。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而后因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相交甚厚,曾作为清朝末代皇帝的特使到南方与革命党人谈判。后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他是签名印在中国银行票据上的第一人。而且,他还和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配过戏。两位表哥天资聪颖,学识渊博,深得亲朋好友的敬重。
康光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已经功成名遂。但待人谦逊,从不倨傲。对孩子总是亲切和蔼,每次来我家,都问我们晚上去不去看戏。如果去,他便去买票。
两位表哥到的那天晚上,爸还没回来。妈在客厅里招待他俩,她已盼了好久。他们把妈看成是自己的姨妈,因为他们知道,妈同大妈是好友。而且,抚养妈的潘家与他们冯家是亲戚。妈有什么问题决定不下来,都要问他们。她常对我们说:“这事得等你们表哥来了再定,他们见过大世面。”
“表妹,来跟我们说说话。”两位表哥热情招呼我们,“我们有好长时间没见了。”
“你们俩都坐我边上。”康贤表哥说,“都三年了,我记得上次见你时,你还梳着两条小辫,像个小娃娃。时间过得真快,现在都成大姑娘了。我听说,你还是个学生运动的头头。我是老了,从欧洲回到北京那天,去看姨妈,你在摇篮里睡得正香呢。”
“你们男人还那么怕老?”妈问。
“西方人不爱说出自己的年龄。”康贤说,“如果跟中国人似的,头一次见面,问一位英国或法国小姐多大了,非露怯不可。即便是个男人,第一次见面就问岁数,人家也不高兴。”
“西方人可真有意思。”妈叹了口气,“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可笑,是不是?”
“听说你们都在为学生运动出力。”康光转向妈,说,“姨妈,真该祝贺您,眼下要想超过别人,除了学习,还得干点实事。竞争比我们年轻时重要多了,男女都一样。”
“梅表妹,听说你想上洛克菲勒医学院,这主意不错。”康贤打断话头说,“我前天去东城,看到了富丽堂皇的北京协和医院,翠绿的琉璃瓦,大理石的柱子和台阶,门窗漆得鲜艳猩红,华美壮观。我要是年轻十岁,变着法儿也得进去享享福。你想,从外面看,辉煌如皇宫,里面都是现代化的设备,热澡、冷浴、空调、电气炉子,中餐、西餐,随你吃。”
我和梅姐听得入了迷。妈一直在想孩子的入学问题。
“看不出你这么喜欢协和医院。”康光开玩笑说,“干脆你假装生病,我把你送进去享清福。”
“只怕你嫂子不干。”康贤打趣说,“你没听说,那儿的护士都很漂亮,她们全是大家闺秀,风韵迷人,思想开放,会讲外语,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姑娘。”
“你对协和医院这么了解,好像跟那儿呆过。你不怕我们把你说的告诉太太?”妈说。
“我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去过一两次,是看一位病友。只能呆一刻钟。就这些。”
我们都笑了。这时,爸进来了。
“什么事这么开心?”爸把帽子和外衣交给妈说。“接着说,我就爱跟家里听你们说笑话,整个下午跟那帮诗人在一起,无聊透了。”
爸躺在长沙发上,这是他从以前天津德国租界的家具店买来的。他想躺着舒舒服服地听我们聊天。
“哪来的那些无聊的诗人?是银行家还是军阀?”康光问。
“都有。他们以前只想赚钱,钱赚多了,就来买名誉。他们觉得写诗不错,可以扬名,还以为自己写诗同赚钱一样有天分。”
“我敢说那些人的诗乏味之极,真庆幸回家能摆脱那帮所谓的诗人。”康贤说。
“够扫兴的,瞧这一包都是他们的诗。”爸说。
“姑父,我要是你,就把这包扔到火炉里。”康光叹了口气。
晚饭准备好了,我们走进饭厅。
在我们家,吃晚饭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爸常说:“吃饭是一种极好的享受,劳累了一天,干嘛不好好松松心。”因此,他不论多忙,总惦记着晚饭吃什么。我和梅姐下午一放学,他便问我们晚上想吃什么。有时为做菜,他能不厌其烦地跟妈唠叨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梅姐说干嘛跟吃饭上花那么多时间,真是瞎耽误工夫。
妈马上说:“俗话说‘当官为嘴,做贼为饱’,谁不想吃好点。怎么是瞎耽误工夫?”
中国有句古话:“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我们家找的广东厨师有二十多年了,我记得都叫他宋师傅。他做的都是家常菜,但样样鲜美可口,色香俱全。他善烹调,最拿手的是做肉、鱼和鸡,不失原味,还飘散出不同的植物香。我们都喜欢看他做鸡时的忙乎劲儿,他将雏鸡切成小块,用酱油调浸一个小时再放到油锅里煎炒十分钟,放上蒜末、洋葱、青椒和辣椒,那味闻着特香,吃起来真是味道好极了。看上去倒不难做,他只是摇着油锅,鸡的颜色稍稍变黄,就算成了。这便是烹调。他在酱油里加了许多种调料,尝起来酸、甜、苦、辣、咸,五味齐全。他炒的菜家里人都爱吃,有一种特有的风味。
我最爱吃他做的清蒸鲜鱼和油炖糖醋鱼。梅姐爱吃他做的油爆羊肉,里面放了蘑菇、胡桃、竹笋和青蒜。她老让他给做爆羊肉和烙饼。有了这,她别的什么都不吃了。
妈做的几样菜,我们也都爱吃。除了招待贵客,她很少做。这天晚上,她做了两个菜招待表哥,一个是野鸡肉,放上米酒、生姜、干蘑、干笋,用微火炖一整天,一揭盖,肉香飘溢。另一个菜是鱼丸子汤。鱼丸子用鱼肉、火腿、洋葱加蛋清调制,再洒上盐和胡椒粉,放入汤中。那丸子看上去清亮透明,吃起来味道鲜美。汤中再撒上香菜和水芹。奶白的丸子与青菜相配,真是好看。
两位表哥都夸菜做得好吃。康贤对我们说:“表妹,生在这个家,你们可真有福气。你们的妈妈结婚前就做得一手好菜,你们的爸爸又那么会点菜。”
“你们吃过那么多山珍海味,还能看上我做的菜?”妈谦恭地说。
“是真的好吃,我有许多年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康贤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太谦虚了,姨妈。人家西方人可不这样说。给你们说个笑话,去年在巴黎,中国的总领事在一家大饭店设宴请客。他按中国的习惯致辞时说,准备的饭菜不好,请多海涵。第二天,饭店经理对那位领事提出控告,说他侮辱了饭店的名誉,影响了生意。”
我们都笑了。
“这是真的,还是你编的?”妈问。
“这是真事,如果你们想听,我还能讲好多。”康贤说。
“就是东方,也有不少这样的事。”康光说。“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去东京,跟新认识的一个日本人打招呼,问人:‘吃了吗?’那日本人很惊讶,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他没回答,但显得很尴尬。他们也没再谈什么,分手时人家说再见,我那朋友说‘明儿见。’跟北京,这话听起来多亲切,道声别而已。可那日本人又误会了,他第二天给我的朋友拍了封电报,说很抱歉,今天不能见。”
“有位英国朋友跟我讲,他有一次对一个温柔的日本女人发了通脾气。”康贤说,“他到东京访友,朋友不在。他有急事,就问朋友是否留了条。给他开门的女人什么也不答,只是按日本的礼节连声说:‘是,是。’但她越说‘是’,英国人越恼火。他最后不耐烦地问:‘你傻了?’那女人还说:‘是。’”
我们被逗得前仰后合。爸说:“你们知道,李鸿章老早就清楚东、西方礼仪上的差异,打手势都有不同,西方人叫你来时,手指向上,手掌对着自己,而中国人手指是冲上,手掌却对着你。”
吃过晚饭,我们都来到客厅。康光和我聊了很长时间,他问我女子师范毕业以后打算干什么。我告诉他想教书。我觉得教育在中国最为重要,它可以多种方式救国。
“我看你教书不好,你还没老到要做一个女教员。”康光说,“为什么不画画呢?缪素筠老师对你寄予了厚望,希望你将来成为大画家。除了你,她可从来没夸过自己的学生。她常给在北京的侄儿写信,问及你的情况。”
第一次去访缪素筠师,就是康光带我去的,现已成了美好的回忆。我记得,与缪师作画,多么令我沉醉,幼小的心灵充满抱负,生活特别富有诱惑力。可我不想告诉表哥我正在想什么。
“我觉得画画对中国的困难一点用没有,它只是和平时期的职业。”
“我不同意。”表哥说,“我认为每个人都该充分发挥天赋才能,画画也并非没用。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所看到的美的事物表现出来。它对我们以及社会改革家都是有帮助的。我要是你,就不放弃画画。当然,除了画画,还可以学别的,例如文学,你不是也很喜欢,努力吧。”
“孩子,表哥说的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妈说,“一跟生人说话脸就红,哪当得了什么社会改革家和教员。”
“你的那些姐妹们上的什么学校?”
“九姐去年跟三妈去了上海,上了个特别时髦的学校。那个学校还教英语、法语,每年都培养出一大批时髦小姐,能歌善舞,有的还弹得一手好钢琴。”
“这种学校是专为时髦女孩开的。”表哥说。“重复你的话,对国家一点用没有,对九妹也没好处。”他转向妈说:“我看让梅表妹去学医,她将来准是个好医生。”
康光的判断十年之后得到证实。九姐成了交际花,与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并不幸福。梅姐成了著名医生,同一位知名科学家结婚。我真为她骄傲。
康贤回北京前,又来看我们。那是个下雪的星期天,除了爸,我们都在家。花园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硕大的假山石看去好似北极的一个小岛。家里的两条蒙古黑犬那天可着劲儿地撒欢,在花园里串上跳下,雪地上留下斑斑点点的狗爪印。我爱看狗在一起戏闹,更爱看它们厮咬。客厅里飘散着梅花、水仙和菊花的香气。猫咪躺在俄式大火炉旁,沉沉地打着鼾。妈正在竹绷子上绣着花,绣针穿过绷子的声音正好与猫的鼾声合拍。这种静谧的和谐,常使我想起北京。
突然,我们听到火车驶过。我们家离车站只有二里地。妈放下绷子,叹了口气,“我就是受不了这汽笛声。”
“那干嘛不回北京?”康贤从屏风后面转出来说。他先进了爸的书房,爸不在。“她们该在北京上学,你和姑父也都没必要住这儿,尤其是姑父,成天跟那帮军阀费唾沫,能受得了?他们现在正想拉他入伙,对他没好处。我劝劝他,跟你们一起回北京。”
“就怕小六从南方回来不让他走,她儿子跟这儿上学。”妈说。
“我看姑父对那孩子根本不上心,不爱搭理他。那孩子太笨,考试两次不及格了。让他们娘俩待在天津,甭管他们。”
听康贤这么说,我特别高兴。但看的出,他对爸感到惋惜。
爸回来以后,康贤跟他谈了好长时间,爸听得很专心,并说来年(1929年)回北京。他让康贤在我们回去前跟北京找一处小点的房宅。
我和梅姐听到爸的决定高兴坏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俩跑到花园,跟那两条大狗可着假山石上下追着玩。花园里装上了电灯,照得通明。小树、山石、花坛和西式台阶、阳台上,披着一层白雪,银装素裹,晶莹皎洁,真是迷人。我以前竟从未注意过。
“住在北京,能去西山看雪景了。”我说。
“下雪天,我们去长城吧。”梅姐说。
“看那无垠的山峦披着白雪,天放晴了,还能看到野鹿奔逐跳跃。白鹤、金鹰从紫禁城飞到郊外。”
“春天来时,御花园里有美丽的孔雀伴行漫步。”
“怎么会呢?”我问。
“你不知道御花园已经开放了?”
我在脑子里编织了一幅美丽的地毯,上面有辉煌的宫殿,富丽的园林,到处是鲜花、孔雀、白鹤、金鹰。金鱼在荷塘戏水,牡丹花色彩艳丽,雍容华贵,芳香怡人。在戏院、茶馆、寺庙和各种市集,都能见到一张张亲切和蔼的笑脸。环绕京城北部的西山、长城,给人一种安全感。这是春天的画卷。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