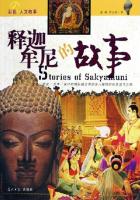这篇只可作本题的小序。关于敦煌壁画,光算长度,即有二公里半,时间包括千多年,魏晋隋唐五代宋元诸多朝代,规模之大,造诣之高,都是与希腊罗马的争辉千古。又因天时特别干燥,虫蚁俱无,故壁画色泽,明丽如新,此为欧西古文物不能相比之特别优点。惟笔者感到自己对本国文学、历史及传统的艺术所学习的很有限,虽是据实写来,挂一漏万,势所不免。这篇拙作,只可说是衷心景仰的出品,同时也想为近代对西方文化过度崇拜而有自卑感的同胞们打一打气。今天美术工作者对这伟大优秀传统的艺术遗产,也应负起光大发挥的任务。
一九七五年四月,我到达北京,知道请求到敦煌已经批准,真是喜出望外。解放后,由海外来的国人,曾去过敦煌的,寥寥可数。因为敦煌远处戈壁大沙漠的一角,一年有四五个月冻冰,在零下二十七度。平日风沙蔽天,没有交通工具来往雇用,况且西北即是接近苏俄的边疆,通常也还有十万大兵驻扎着。我不是佛教徒,也不是考古学者,但是我许下要去敦煌的心愿,已经好多年了。
在童年开始念唐诗三百首时,我常常觉到那时的人,很喜欢音乐、唱歌、舞蹈、骑射等等,和我看见的时人,很不相同。例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又或如“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都是那时的诗人日常生活或所见到的情景。有一次我问我的老师,“唐诗里的人和现在的人很不一样,他们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是中国人,可是那是在唐朝,一千多年前了。”
这答复并不解决我的问题。到了我长大,对中国艺术和文学都增加兴趣时,念到“曹衣出水,吴带迎风”两句,虽知道曹是说曹不兴,吴是吴道子,可是不懂得为什么古人把这两句作为很重要的介绍。那时晋唐原画,已无法看到,虽有摹本,也不能解决我的疑问。直到我年前到了敦煌看过真的晋唐壁画时,我方恍然大悟,为什么“曹衣出水”和“吴带迎风”二句在艺术上占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敦煌壁画里的人物,体格和衣着,表现“曹衣出水”的艺术,不计其数。换句话说,那即是希腊艺术注重人体美的精华,至于“吴带迎风”,可在壁画上的飞仙、伎乐、舞蹈等衣着及五代乐会或报恩经变等的大场面看到。画人的设计并用传统艺术手法,表现出旋律美、动作美。敦煌的人像应用“吴带迎风”的画艺,全是在飞腾的舞姿中,人像的着重点不在体积而在那克服了地心吸力的飞动旋律。所以飘荡临风缠绕的带纹,调和着佛头上的圆光,足下的莲座,以及飞禽走兽,都和那些飘飘的带纹,组成一幅广大的旋律,这也许可以说是宇宙的节奏——交响曲。
我们是幸运的,带着近代艺术的眼光去看古代劳动人民努力奋斗寻找出来的精心结构。许多重要问题,得来不费工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随武汉大学到四川的乐山避难。那里是去西康必经之路,有一次吴稚晖和胡伯渊路过乐山,他们说是由玉门关等地参观油田顺便到敦煌看看千佛洞的壁画。
吴稚晖对中国文学历史认识相当精深,十分称道千佛洞的价值,也十分憎恨王元录道士盗卖国宝的行为。他说大英博物院收买赃物和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的收购都是我们的国耻;还有日本、俄国、美国、印度也都拿去不少。那里有个埋藏千多年的山洞,那千多年前手抄的五六万本书和画,真是无价之宝,大半的送掉了!
敦煌壁画是我那时向往的,不禁打动我的心思,就问:“我们也可以去敦煌看画吗?”
吴稚晖用他老人家的诙谐口吻答道:“若是你去拜张大千做老师,或者还有办法,那里不但没有人家,也没有吃食的市场,一个人去,不冻死,也会饿死。”
胡伯渊那时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对于敦煌洞里发现藏书和古画,也十分注意。他们都是民初爱国志士,话下不免悲愤。
据说这批藏书是由四世纪到十世纪的手抄本,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法律、文学、音乐、医药、绘画、星相、艺术、农业、语文等等,这些书用四种语文写出,除汉文外,有古藏文、梵文、回鹘文、龟兹文写本等。因为敦煌气候异常干燥,虫蚊俱无,洞口且常被飞沙封闭,所以虽过千年亦无损伤。这是空前得天独厚的图书馆。至于敦煌为什么会有这四五万册的古书埋藏起来呢?原因是宋末西北连年被异族侵入,烧杀抢夺,无处得免,敦煌的僧人,于是自掘山洞,把宝贵的经典书画,分包扎好放入,以为他日战祸完毕,回来取用。谁知宋末到元明,西北一带,战争无时或止。日久也失传了。终于被那昏庸的王道士偶然发现,发了一笔国难财。
现在该从头略说我去敦煌的行程了。
由北京去敦煌得乘飞机经过兰州,再由兰州乘火车到酒泉,由酒泉再乘汽车过戈壁沙漠而去敦煌。
在四月下旬的清晨,我由北京机场直飞兰州。中午过西安,飞机停下来,全体乘客下机午餐。我随大众走入食堂,交一元人民币买午饭。四菜一汤,真是物美价廉。稍为休息后,即登原机飞兰州。
从西安到兰州的飞机上,望到连绵不绝的青绿的崇山峻岭,不久又看到不少的山上,有层层碧绿的梯田,下面是整整齐齐的成排的平房,听人说那是西安大号的公社。
近暮渐渐看见一些没有树木却多岩石的平山,据说已近兰州了。兰州机场规模不小,较之北京的差不了多少。
兰州博物馆馆长常书鸿先生及招待所一位秘书已在等待。我即与他们同车入城。
原来兰州是一座完美的近代城市,马路宽大,两旁绿树交荫。新式小楼房多欧美样式,小小庭园且有花木掩映。
常书鸿原是留法多年有成就的画家,对中国文物及欧洲艺术,都具高深认识。我很幸运能先会到他再去敦煌。
他们提议我应在兰州住两日,次早去参观兰州博物馆。那是世界闻名的一只出土的周代铜马踏着飞燕跑的发源地。此外还有许多出土的商周年代铜器陶器陈列出来。我随着李承仙、常书鸿在馆里看了两三小时,真是如入宝山,目不暇给。
午饭过后,我随常书鸿等去兰州大桥公社参观。那公社建在大桥附近的一个无树木的沙滩上。建社只有十六年,现已成一座大果木园。每年出产苹果、葡萄、瓜和李子等等,数量达十七万斤之多。
社员住在果木园的近旁的瓦房,有鸡、猪、小菜园等自留地。在招待室用茶后,社员带我去他们住家坐坐。两位中年女社员留我坐下吃茶,她们待人亲热像老朋友一样,临别还拉着手劝我再来到她家住两天歇息一下。我觉得这是祖国公社办得最成功的一点。我经过多少公社,南至罗岗,北至兰州,他们待人接物,都是一样的诚恳亲切。临别时,每人还送大袋水果。常书鸿格外对他们的花木秧苗温室注意,里面设备,光线及栽培秧苗的盆钵,既科学化,也艺术化。
次日晚饭后,因我要搭火车去酒泉,所以在午前去参观有名的兰州毛织厂。那厂在城外,规模很大,设备也是近代化的,据说出品远销南洋及欧美。那俄国式毛毡,质料及花样都超过俄国出品。毛织品衣料,用西藏高原的柔细羊毛织的,也较英国最优加士麦毛织品物美价廉,可惜我是路过不能带;但我买了一大坯沱茶,那是云南来的,多年未尝了。
兰州火车站还是旧式的,站台很矮,上车时需人扶上去。同去有两人,一为博物院女职员,一为招待所秘书,他们十分和蔼,学识也丰富。开车后,车长入房来问候,很是诚恳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