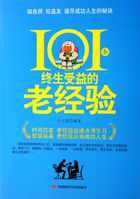这是阿拉斯加,世界的尽头。
但,这是我一生不及的梦吧。
01
我房间的墙上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一片凌厉的雪山和透彻无尘的蓝天。如果把它翻过来,就会看到上面有一行日语:Emily:ここはアラスカ、世界の終わりだ。(日语,意为“这是阿拉斯加,世界的尽头”)
A.Y.
02
A.Y.的全称是Abe Yuka,翻译过来就是阿部由佳。这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名字,它的主人看上去也很普通,头发染了浅浅的黄色,扎着一只马尾辫,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脸上长久泛着的两块红晕。“阿—比—鱼—卡”阿部努力张大嘴,一个音一个音地跟我学如何用汉语说自己的名字。“不对,是阿部由佳。”我纠正她。“阿—鳖—瑜—伽?”阿部有些不自信地盯着我看。“嘴巴要再收紧一点哦。”
“阿—噗—姚—甲?”阿部继续练习。
最后她终于把发音稳定在“阿补有家”的程度,我笑她的发音像是Google里的机器人声。
在发音问题上,阿部一直都很羡慕身为中国人的我。日本人无论说任何语言,听上去都是一股日本味儿,阿部也不例外。她能把一句简单的“早上好”发成“go-do mo-lu-nin-gu”(“Good morning”的日式发音),因此我常常笑她。可是阿部学英语学得特别认真,当时我俩在北海道的一家小酒馆打工,每天休息的时候,她就会捧着小本子自己在角落里看单词。
她说她想去美国的阿拉斯加看看,可店里人都说她一没钱二不懂英语的,去美国只会被人拐走。“我就是想去嘛。”阿部说,“I wan-to to go A-me-li-ka.”。(“I want to go to America.(我想去美国)”的日式发音)
阿部虽然年纪比我小,但她是我打工的前辈。她说她初中毕业就不想读书了,所以很早就出来打工。
“读书好没意思,我最讨厌数学课。”阿部说,“我的数学老师叫田中,是一个欧吉桑(日语“おじいさん”的音译,意为“老头子”),头发都快掉光了,眼袋有半张脸这么大。”她边说边给我比划。
“我在他的课堂上睡觉,他还用粉笔砸我。我梦到烤肉呢,烤了一桌子好肉,正准备吃,流了满桌子口水,被他一下子砸醒,到嘴的烤肉也飞了。”阿部说她到现在还恨着当时的田中老师,因为她再也没有烤过这么好吃的烤肉了。
“那是梦嘛。”我说。
“可是,真的看上去很美味啊。”阿部撅着嘴说,“那烤肉烤得金灿灿的,上面滋滋地冒着油,翻一翻,正好烤得有些焦,闻起来那个香啊,涂上佐料,别提有多鲜美啦。”
“啊……说得我都饿了。”我摸着肚子,端了一整天的盘子,腹中早就空空了。
“我也饿了。”阿部也摸着肚子,看了四周一眼,对着我嘿嘿笑起来,“反正现在老板不在,我们自己做点吃的呗。”
“好啊。”我舔了舔嘴唇。
阿部在厨房翻找了半天,对我说:“没有肉了,要不我给你做蛋糕吧,我甜品做得可好了。”
“蛋糕?好棒!”我马上提出要给阿部打下手,“要准备些什么材料?”
“芝士、黄油,然后……”阿部想了半天,“还有什么来着?”
“白糖和面粉?”我虽然不会做蛋糕,但是这似乎是常识。我开始担心了起来:“你真的会做蛋糕吗?”
“对对!”阿部一拍大腿,“我当然会做,一下子忘了嘛。”接着,阿部摆开十来个大碗,那阵势,颇有些电视上美食家的派头。“你放心啦,很简单的。”阿部信心满满地说。
半小时后,我们在飘满黑烟的厨房里被店里的大厨岩口发现,他同时发现的,还有烤箱里的一块如同石头般坚硬的黑色不明物体。“这是啥?”岩口本来就长得有些凶,他一皱起眉头来简直就像个黑社会,吓得我不敢吱声。“我想做蛋糕嘛。”阿部解释着,“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出来就成这样了。”
“这是蛋糕?”岩口扑哧一声笑了,他拿着根筷子戳了戳那坨黑色硬物,“你不说我还以为你挖化石呢。”阿部有些丧气:“别告诉老板啊。”
“那你们赶快把厨房收拾好。”岩口收起了眉头的严厉,“是不是肚子饿了?我给你们做点吃的。”
“好棒!”阿部开心极了,“我要吃咖喱饭。”
岩口大厨已经四十多岁了,虽然长得像黑社会,但是做饭的手艺却没得挑。两碟热气腾腾的咖喱饭马上就被端上了桌,我和阿部一人一份,边吃边聊。阿部对我说,她最爱吃岩口做的咖喱饭,怎么吃都吃不厌。
“对了,他是我男朋友哦,Emily可不许喜欢他哦。”阿部说。“啥?”我抬起头。阿部正将一勺热气腾腾的咖喱饭送进嘴里。“男朋友啊,boif-len-do(“boyfriend”的日式发音)。”阿部以为我听不懂,就用日式英语又解释了一回。
“可是岩口,都快四十了吧?”我尽量放低声音,岩口正在我们身后清理着被熏得乌黑的烤箱,不知道听不听得到我们的对话。“四十二了,是个大叔了。”阿部嘻嘻笑着。“可是阿部,你才十八岁哎。”我说。“是啊。”阿部一脸“那又怎样”的表情。“其实他很像个小孩啦。”阿部说,“很多时候都要我去照顾他。”
“在那儿说什么呢?”岩口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有这个闲工夫自己来清烤箱。”
“你看吧,在那儿发小孩脾气呢。”阿部在我耳边轻声说。“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你都还没出生吧。”我在心里嘀咕。
阿部转身对岩口说:“麻烦你了嘛。这个咖喱真的好好吃,怎么吃都不会腻呢。”她绽放出一个无比天真的笑脸。岩口朝她看了看,叹了口气继续抹烤箱,一副缴械投降的样子。
阿部朝我眨眨眼。
“哦……”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但又不知道应不应该追问。日本人有一个词语叫做“无关心”(日语“無関心(むかんしん)”),翻译得通俗一点就是“不管闲事”。大多数的日本人在不管他人闲事的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问长问短。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阿部根本就是个肚子里憋不住话的人。不久之后,她就把自己的恋爱经历全部讲了出来。阿部原本并不在这家居酒屋工作,她第一次来店里还是个客人。
阿部跟我说,当时他们三男三女来这家店“合コン”。“合コン是什么意思?”我问阿部。“这个嘛,就是互相不认识的男女一对一这样凑好,然后到饭店里吃个饭或者去卡拉OK唱歌这样。”她解释道。“哦,那就是联谊嘛。”我算是明白了。“中国也有合コン吗?”阿部问。“有啊,就是单身的人聚在一起互相认识,找男女朋友的活动嘛。”我说。“哦?那在中国也可以‘打包’吗?”阿部问。“打包什么?宵夜吗?”我没听懂。
阿部咯咯笑了,她说日语里的“打包”,除了打包食物之外,还表示男生把一起联谊的女生打包回家。日本人对性要比中国人开放,阿部小我这么多却能毫不脸红地说着这样的话题。“我在合コン的时候,还是挺受欢迎的呢。”阿部挺骄傲的,“那天来这里,我也是话题的中心呢。”
“那你那天有没有被‘打包’呀?”我问阿部。“有啊,不过不是被同行的男生,而是被……”阿部瞥了瞥在厨房里埋头工作的岩口大厨。
阿部说,她那天吃了岩口做的菜,只是一道很简单的咖喱饭,却让她吃出了别样的温暖。“当时我就在想象,能够做出这样好吃的料理的,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阿部用手托住下巴,一脸的羞涩潮红,“这家店刚好在招人,我就来应聘。后来进了厨房工作,给岩口帮忙切切菜什么的。他做菜真的很好吃,每天吃着他做的料理,我慢慢地习惯了这种味道,也习惯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
“虽然他是个大叔,跟我爸的年纪差不多,有的时候也很任性,还会跟我吵架。但是我每次一生气,他总是知道如何让我开心起来。”阿部说,“他只要给我做饭吃,我就一定会原谅他。特别是他做的咖喱饭,真是闻到香气就不会生气了呢。”
阿部一脸幸福的模样,让人实在无法再对这对年龄悬殊的情侣多说什么。
虽然我的年龄比阿部大几岁,但是有时,我真的觉得她才是岁数更大的那一个。她工作的时间比我要长,比我更有经验,常常会在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来帮我解围。
有一回,来了几个人高马大的客人,他们一进店里就点了不少酒,还不等我们端上小菜就呼的一声喝上了。他们喝了不一会儿,其中一个人把我叫了过去。
“小姐,请给我一个haizara。”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虽然心里有点紧张,但是我瞥到他手里拿着的香烟。“大概是问我要打火机吧。”我心里猜。
可当我拿着打火机给他的时候,他却显得很生气:“听不懂日语吗?我要haizara。”
他的声音非常响,引得店里的客人都纷纷侧目,这让我很害怕,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才好。“不好意思,她是新来的,有点紧张呢。”阿部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往桌上放上一个烟灰缸,“这是你要的haizara。”
“原来haizara是烟灰缸啊。”我后来对把我救出困境的阿部说,“我从来没有在教科书上学到过这个词。”
“你不抽烟吗?”阿部问我。“当然不抽。”
“那真是太可惜了。”阿部掏出一支细长的女士烟,送进嘴里,接着掏出打火机点着,“这款烟草可好了,薄荷味的,很香。”
阿部熟练地吞吐着烟圈,这让我对香烟的味道也有点好奇起来。“来一口?”阿部用手夹住烟,递到我跟前。我接过烟,试着放进嘴里吸了一口,香烟的味道比我想象的要清淡得多。
“不算难抽吧?”阿部问我。
我点点头。以前一直觉得香烟是毒蛇猛兽,只要一抽烟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坏孩子”,但这次发现,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我问阿部。
“大概两三年前吧。”阿部接回烟,一边抽一边说,“我的父母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别说抽烟了,就连坐姿稍微不端正一点他们就会责骂我。后来我离开家,一直一个人生活,抽烟什么的都算是小事了。”
阿部从来没有说过她家里的事,这让我有些好奇。可当我向她询问的时候,她却一改平日的开朗,默不做声起来。“告诉你哦……”她突然说,我以为她要告诉我关于她家里的情况,竖起耳朵来准备听。
“其实以我的年纪,是不能抽烟的。”没想到她一下子扯开了话题。
“你要帮我保密哦,si-ku-le-to。”(“secret(秘密)”的日式发音。)
03
阿部告诉过我,她来自东京,是因为憧憬冬天和积雪,才会来北海道打工的。
在我们工作的居酒屋附近有一个滑雪场。时值冬天,北海道的山已经早早堆满了雪。那段时间,阿部每天都兴奋地望着店外面的积雪。
“我们去滑雪吧。”
一天,我正在店里抹桌子,阿部跑到我身边来说。
“滑雪,听起来不错哎。”可我又转念一想,“不过这几天客人这么多,老板是不会给假的啦。”
北海道本就是旅行圣地,自入冬来,每日更是多了不少游客。“翘一天班咯。难得看到这么大的雪,你不想去体验一下吗?”
“翘班不要紧吗?”我有些忧心地问阿部,“老板会不会生气啊?”
“顶多就是发发脾气嘛,没什么大不了的。”阿部毫不在意地说。
阿部看上去颇有经验,我便也放心下来。
北海道的雪是有名的粉雪,干燥、细腻,雪质极佳,穿着重重的雪靴一脚踏上去,就仿佛踩在雪白的沙滩上一样。虽然天色尚早,但周围早已有了不少滑雪爱好者。他们在雪地上嗖嗖划过,飞快得像是一道道影子。
阿部在初学者用的平地上教了我几个基本姿势,譬如滑雪的时候要微微蹲下,将重心转移到大腿;又譬如利用内八字的脚型刹车。她看上去颇为专业,在雪地上娴熟的动作让我很是羡慕。
过了一个多小时,已经摔了几个屁股墩的我坐在雪地上休息,看阿部自由地在我面前的雪地里滑来滑去。“我觉得你滑雪的时候像只小鸟一样,”我对阿部说,“好像要飞起来似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所以很是兴奋呢。”阿部见我坐在地上休息,她也过来陪我说话。
阿部长大的地方四季如春,可是她一直都向往着北国的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