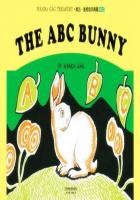海盗的进攻纯粹是一次冒失的突袭;这就足以证明胡克考虑不周,因为,要对印第安人发动成功的奇袭,是白人的智力所达不到的。
按照半开化民族的不成文法则,首先发起攻击的总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很狡黠的,他们总是在拂晓前出击,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白人战斗力最低落的时候。此时,白人在那片蜿蜒不平的山地的最高点上修筑了一道简陋的围栏。山脚下,小河奔流;因为离水太远就不能生存。他们就在那儿等待着进攻的号令。没有经验的新手,紧握手枪,踏着枯枝来回走动;老手们却安安逸逸地一直睡到天亮。在黑漆漆的漫漫长夜里,印第安人的侦察兵在草丛里像蛇一样地匍匐潜行,连一根草叶都没碰倒,就像鼹鼠钻进沙地后,沙土无声地合拢一样。除了他们偶尔惟妙惟肖地学着草原野狼,发出一声凄凉的嗥叫外,别无其他声响。这声嗥叫又得到其他人的回应,有的人叫得比那不擅长嗥叫的草原野狼更好。寒夜就这样渐渐过去,长时间的惊恐对于那些初次体验的白人来说,真是难熬之极;可是,在那些有经验的老手看来,那些阴森可怖的嗥叫声,以及更加阴森可怖的寂静,只不过说明黑夜是如何行进罢了。
这种情况,胡克原是一清二楚的,如果他忽略了,就不能因他的疏忽而原谅他。
印第安人呢,他们坚信胡克会信守自己的准则,他们此夜的行动,正和胡克的行动相反。使他们的部落闻名的那些行动,他们都一一执行。他们感觉的灵敏,是文明人既惊羡又害怕的,只要一个海盗踩响了一根干树枝,他们立刻就知道海盗们已经来到了岛上。眨眼间,就响起了草原野狼的嗥叫声。从胡克的队伍登陆的海岸,到树洞里的地下之家,每一寸地面都被他们穿着脚跟朝前的鹿皮鞋暗地里侦察过了。他们发现只有一座土丘,山脚只有一条小河,所以胡克别无选择;只能在这里暂驻,等候天明。印第安人极诡谲地把一切布置停当之后,他们的主力部队就裹起毯子,以他们那个种族的男子汉最珍贵的镇定态度,守候在孩子们的家上面,等待着那个严峻的时刻,去拼死一战。
他们虽然醒着,却正做着美梦,梦想黎明时严刑拷打胡克,却不料反倒被奸诈的胡克发现。据一位从这次屠杀中逃生的印第安侦察兵说,胡克在那座土丘前根本没停留,尽管在灰蒙蒙的夜光里,他肯定看到了那座土丘。他心里始终没有打算等着印第安人来攻击,他连等待黑夜过去都等不及了;他的策略不是别的,是立刻就动手。迷惘的印第安侦察兵原是精通多种战术的,却没想到他有这一手,只得无可奈何地跟在胡克后面。当他们发出草原野狼的哀号时,终于暴露了自己。
勇敢的虎莲身边聚集了十二名最强悍的武士,他们突然发现诡计多端的海盗正向他们冲来。梦想胜利的纱幕,立刻从他们眼前扯开。要想收拾胡克是办不到了,现在是他大肆行猎的时候了。这一点他们心里很明白;但是,他们的表现,恰如印第安人的子孙那样。假如他们很快地聚拢,列成密集的阵势,敌人就很难攻破;但是印第安种族的传统禁止他们这样做。他们有一条成文的守则,凡是高贵的印第安人,在白人面前不可表现得惊慌失措。海盗的突然出现,尽管使他们惊骇,他们却都巍然屹立,连一条肌肉都没颤,就好像敌人是应邀宾客。这样英勇地遵守了惯例之后,他们才握起武器,发出了震天的喊杀声,但为时已晚。
这哪里是什么战斗,其实是一场大屠杀,我们不去细说了。印第安部落的许多优秀战士就这样死去了。不过他们也不是白白死去,没有一点功绩;随着海盗瘦狼的倒下,阿尔夫·梅森也送了命,再也不能侵扰西班牙海岸了;还有乔治·斯库利、查理·托利和阿尔塞人福格蒂等人也一命呜呼。托利死在可怕的豹子的斧头下,豹子和虎莲以及少数残余部队,终于杀出一条血路,逃了出去。
在这次战斗中,胡克的战术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还是等历史学家去裁决吧。假若他呆在土丘上等待正确的时机再交手,他和他的部下说不定全都被宰了;要评定他的功过得失,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才公道。也许他应该做的,是预先通知对方他要采取新的策略。不过如果那样,就不能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会使他的战略计划落空。因此,这是很难下结论的问题。不过,他的智慧能构想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计划,他狠毒的天才能实现这个进攻,我们尽管不情愿,也不能不佩服。
在那个胜利的时刻,胡克自己的心情如何呢?他的手下人无从知晓。他们气喘吁吁地擦着刀,远远地躲开他的铁钩;他们的贼眼偷偷地斜睨着这个难以捉摸的怪人。胡克心里一定是扬扬自得,不过不必露在脸上。在精神上和现实中,他总是远离他的部下,永远是个阴暗孤独的谜一样的人物。
不过,这一夜的活儿还没完;胡克出来并不是为了杀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只不过是用烟熏走的蜜蜂,他要取的是蜜。他的目标是彼得·潘,还有温迪以及他们那一伙,但主要是彼得·潘。
彼得只不过是个小男孩,可胡克为什么那么恨他,这真叫人琢磨不透。不错,他曾把胡克的一条胳臂喂了鳄鱼;由于鳄鱼穷追不舍,更使胡克总是身处危险中。不过,这也很难解释,胡克的报复心为什么这样残酷和毒辣。事实是,彼得身上有某种气质,引得这位海盗船长暴跳如雷。不是彼得的勇敢,不是他那逗人喜爱的模样,不是……我们用不着乱猜了,因为我们都很清楚那是什么,不能不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彼得的那种自信满满的傲气。
正是这个,刺激着胡克的神经,恨得他的铁钩打颤;夜里,这种恨像一只虫子,扰得他不能安睡。只要彼得活着,这个受折磨的人就觉得自己像是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笼子里飞进了一只麻雀。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钻进树洞,或者说,怎样把他的喽啰们塞进树洞。他抬起他那双贪婪的眼睛扫视着他们,想找一个最瘦小的人。水手们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不惜用棍子把他们捅下去的。
同时,孩子们又怎样了呢?在刀枪声乍起时,我们看到他们一动不动像石雕一样,张着嘴,伸出手臂向彼得求救;现在回头来看,只见他们闭上了嘴,垂下了手臂。头顶上的喧嚣声平息了,像初起时狂风刮过似的那样突然;但他们知道,狂风过后,他们的命运已成定局。
哪一方得胜了呢?
海盗们趴在树洞口屏息聆听,听到每个孩子提出的问题,不幸的是,也听到了彼得的回答。
“要是印第安人得胜,”彼得说,“他们一定会敲响战鼓,那是他们胜利的讯号。”
那只战鼓斯密已经找到了,这会儿他正坐在鼓上。“你们再也甭想听到鼓声了。”斯密低声嘟哝着,声音低得谁也听不见,因为胡克严令不许出声。使他惊讶的是,胡克冲他打了个手势,令他击鼓;斯密渐渐地领悟到,这是个多么阴险毒辣的命令。这个头脑简单的人,或许从来没有这样敬佩过胡克。
斯密敲了两遍鼓,心花怒放地静听反应。
“咚咚的鼓声,”海盗们听见彼得喊道,“印第安人胜利了!”
不幸的孩子们一声欢呼,上面的黑心狼听着,如同美妙的音乐。接着,马上传来孩子们纷纷向彼得告别的声音。海盗们听了莫名其妙;不过,他们所有的情绪都给阴险的欢喜占据了,因为敌人就要从树洞里爬上来了。他们互相奸笑着,摩拳擦掌。胡克迅速、悄悄地下令:一人守一个树洞,其余的人排成一行,隔两码站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