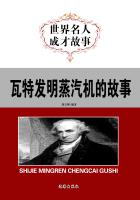马加
一生当中,我最怀念的地方就是延安。在延安,我最怀念的一位亲人,就是申蔚。
1942年的清明节后,春天又来到了延安,西北的黄土高原,晴格朗朗的天空,万里无云,凤凰山展开绿茸茸的翅膀,从杜甫川到杨家岭的沟沟岔岔,到处是一片生机盎然。在抗战大动荡的时代,有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为了奔向心中的革命圣地,经过万水千山,聚集到宝塔山下。
我和申蔚本来是萍水相逢。她生在河南,我生在东北,一条红线把我俩牵到延安,牵动这条红线的便是曾克同志。
那年春天,我在延安蓝家坪“文抗”从事专业创作,经常和曾克见面,申蔚是曾克在开封北仓女中的同学,又喜欢文艺,和曾克常来常往,我俩就这样认识了。
1942年,中国抗战到了相持阶段,需要战略上的转变。延安提出整顿“三风”,动员知识分子接触工农兵,深入实际,朋友见面时常常把这个题目作为话题。
曾克热情坦率,开门见山地说:“申蔚,很久不见,你到哪里去了?”
申蔚是一位内向的知识分子,在开封北仓女中就参加了读书会,编抗战墙报,却从来不显山、不露水。她参加过范文澜领导的战教团,现在参加中央妇委调查团,常和群众接触,态度含蓄,说话细声细语。
“我下柳林乡了。”
“我知道了,就是女乡长乔桂英的家乡。”
“乔桂英这个乡长可好啦!”
申蔚有一张椭圆的脸蛋,两只聪明而又水灵的眼睛,眉梢子在微微闪动,她讲起陕北妇女怎样请她吃羊肉、纺线线……
“曾克,我说也说不完,你一下乡就知道了。”
曾克说:“最近,我知道毛主席找‘文抗’的几个作家谈话,可能和下乡有关系。丁玲让罗丹开一份作家的名单,老马,名单上还有你的名字。”
曾克把视线转到我脸上这工夫,她的儿子在窑洞里醒过来了,曾克过去照顾孩子,申蔚准备回妇委去写材料,曾克对我笑一笑,有意地说:
“老马,请你代劳送客,我就不动地方了。”
我跟在申蔚的身后,走下蓝家坪“文抗”的窑洞,穿过柳阴路,迈过台阶,跨上一条羊肠小道,前面就是延河的沙滩,遍地铺着鹅卵石,河里的浪花闪着粼光。我不知道是被延河的景致吸引住了,还是迷路了,踩在鹅卵石上,歪歪趔趔,申蔚却是那么利索,灵巧地跨过了河。
我为了打破寂寞,借题发挥说:“我听曾克说,你们北仓女中许多女同学都很进步,主要是请了一些进步教员,又是文艺界前辈,像楚图南……”
申蔚微微一笑,又补充说:“还有诗人柯仲平。”
我在东北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喜欢柯仲平的《风火山》。
申蔚边说边走,三步两步跨过了河,飞燕似的奔向杨家岭的妇委会去了。
杨家岭的山麓是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一色青砖结构,白灰天棚,方砖铺地,方格的玻璃窗子,油漆门。这座不小不大的楼房里,就是随后举行世界闻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地方。毛主席亲自接见近百名作家和艺术家,和每一位同志一一握手。会议开头还讲了话——“引言”部分。中间休会10日,接着是作家个人发言。萧军是东北讲武堂炮兵科出身,心直口快,第一个放了炮。
在大会发言的空隙时间,我到中央妇委去找申蔚,她看我突然到来,兴奋又惊奇。
“我听说延安文艺界开大会了。”
我说:“今天是作家个人发言。”
申蔚却说:“听听别的作家发言,也会有一些精彩的东西。”
我们闲谈了一会,我又回到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大会的发言正达到高潮。胡乔木同志正在批驳萧军的观点,认为现在整顿“三风”非常重要,将来也不会像萧军说的,再整顿“六风”。
延安的整风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整风中,我离开“文抗”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一次小组会上,一位同志翻旧账,批评我到中央妇委去找申蔚是“自由主义行为”。申蔚也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徇私情,认为我不仅犯了自由主义,也有爱情至上主义。
我坦白地承认,我有爱情至上主义,但心里却很难克服。
以后,我俩便和延河结下了缘。在晚饭后,我常约她出来散步。离开中央妇委宿舍,经过毛主席住的那排窑洞,出了沟口,走到延河岸边,黄昏以后,晚霞从蓝家坪山头褪去,山谷里的驼铃叮当地响着,从三边来的老客正准备打尖歇脚。只有不疲倦的延河水潺潺地流着。
在蓝家坪对面的河边,有一块青色的卧牛石,不知是哪年洪水暴发,从山沟里冲下来的,像花园的亭子,成为我俩幽会的地方。我们坐在卧牛石上,听听流水的声音,说着知心话,迎着神秘的夜幕,生活在延安这地方,真是太幸福了。
夜深了,人静了,蓝家坪虎头峁山顶上下了雾,仿佛蒙了一层轻纱,远处杨家岭的窑洞闪出点点星火,在夜雾里滚动。
申蔚靠着我的肩膀,轻声说:“毛主席又在写作了,《论持久战》就是在这样的窑洞里写出来的。”
我说:“毛主席给黑暗的中国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申蔚回想起幼年丧父,孤女寡母过着清贫的生活,河南连年遭受天灾人祸,水旱蝗汤,民不聊生,一二·九运动时期,她就参加民先队游行示威、卧轨请愿,在河南的战教团做过女生队长,到了延安才结束了逃亡生活。我的逃亡生活更是不堪言状,失学、失业、失恋、饥饿、蹲拘留所,什么滋味都尝过。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有多少共同的语言,延安是我们必然的归宿。
在延安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我常常和申蔚会面,少则三天,多则五天,特别是礼拜天,会面成为我们的神圣义务。
7月中旬一个星期天,我离开蓝家坪“文抗”,绕过小砭沟,跨上羊肠小道,准备去杨家岭和申蔚会面,刚走到延河渡口,忽然发现延河发了大水。连日来上游下暴雨,山洪暴发,波涛汹涌,无边无岸,河水把蓝家坪和杨家岭分成两半,已经断了行人。这种严峻局面的出现,实在出乎我的意外。回蓝家坪去吧!自己不甘心;迎着波涛过河,却担心生命危险。我又一想,一个人从事别的事业,不也同样担着危险么。我的决心下得很快,随即就脱掉了衣服,用左手举着,右手划水,顺着延河的急流,向着下游浮去。游过蓝家坪前面的河心时,我望见我们常常幽会的卧牛石,河水浩荡,已经淹没了半截石头,露出青色的岩面,迎着凶猛的河水,激起层层的浪花,卧牛石脚下形成一个圆形的漩涡,从上游漂下来的谷草和树叶,在那里打漩,人要掉到漩涡里,也会丧失生命,我游到漩涡跟前,觉得有些恐怖,用右手拼命地划呀,用尽全身的力量,才离开卧牛石的漩涡,到了杨家岭的对岸,松了一口气。
申蔚对我这次的冒险行动又气又喜欢又很惊讶!
“这样大的洪水,你怎么过来了?”
我不讲洪水的危险,反倒轻描淡写地说:“我一下决心,就浮过河来了。”
“你看有别人过河么?”
申蔚对我的态度不满,撅着嘴生气,直率地劝告我说:
“你知道吗?妇委的一位同志对我说:申蔚呀!你交的这位朋友,我看有些冒里冒失。”
我看她真生气了,才认了错:“我的老毛病又犯了。”
“有毛病就改一改嘛!”
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有的女同志吃不了苦,就走了别的“路线”。申蔚自尊心很强,偏偏看上我这个穷光蛋。当时,我刚从敌后根据地回来,窑洞里没有什么摆设,一件日本军用大衣,一件日本军用毛毡,一顶钢盔,一枝钢笔,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和申蔚结婚的时候,就把那顶钢盔当锅使用,煮延安的枣子吃,生活过得非常甜蜜。但好景不长,后来,抢救运动比洪水还要凶猛。隔着延河,我和申蔚两年没有见面。运动到了高潮,有人向我提出问题,让我在斗争大会上交代。消息传到中央妇委,妇委一位女同志劝告申蔚和我划清界限,申蔚痛苦万分,夜里睡不好觉,几次呼唤我的名字,那位妇委女同志很不理解申蔚的感情,非常惋惜地说:
“申蔚,你图马加个什么?”
如果说,人类社会确实有高尚的感情,当时的延安就确实存在着这种友爱和爱情。
抗战胜利以后,申蔚本来有机会可以回到河南故乡,早日与久别的母亲团聚,但她却同我奔赴险象丛生的东北。我们在穿越蒙古草原时遭受到叛变的队伍袭击;在佳木斯群众斗争大会上,敌人打黑枪,我们再次遭到危险。她来到作协同我一起深入生活,辽南的苹果园子,新民的辽河套,哪里都有我俩的脚印。我的许多作品都凝聚着她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她在我的创作上花精力太多,留给自己的时间却很少,她是在疾病中写了《青春的脚步》和《雨后彩虹》。她除了无私奉献和忘我劳动,还图个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中,我俩被下放到昭盟的深山老林,天寒地冷,积劳成疾。十几年来,她一直被病魔纠缠着,先是肾功能不全,后来变成尿毒症。申蔚心情沉重,她说:“我看,尿毒症是一种绝症,许多人进了医院,到头来都是人财两空,把钱用在正经事上吧。”
“什么叫正经事?”
“比如,你的文集,十年来只印了三本,还有三本压在出版社。”
我和儿子说服了申蔚,自己买药治疗,她的病才有好转,体温、血压正常。经医生许可,同意申蔚暂时回家做透析治疗。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这个家呀,它坐落在沈阳新东遗址的南边,面对着辽宁大厦,遥望着北陵公园,新开河流过室前,墙外是一片绿幽幽的树林子,掩盖着我那小小的绿野书屋。这里环境幽美,空气新鲜,我在这里写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度过幸福的金婚,我们珍藏的每一张生活照片,都成为历史记录。
我们打开相片簿子,温习一下过去的生活,第一页是1946年在佳木斯合影的照片,那年申蔚27岁,却显得分外年轻,穿一件翻领制服,圆润的脸蛋,伶俐聪明的杏仁眼睛,独具一种风采,真漂亮极了,申蔚看了看自己的照片,也觉得惊奇了:
“我有这样漂亮么!”
“你还有一张最漂亮的相片,那是在张家口照的,可惜你为一点小事发了脾气,把那张相片撕坏了。”
“不要谈了,我们看看最好的延安照片。”
谈到延安,却展开了我们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宝塔山、杨家岭、凤凰山、清凉山、王家坪、水砭沟、蓝家坪、枣园、桃木、延河,我们幽会过的卧牛石,每一个地方都使我俩深深怀念。
我俩还未来得及看金婚照片,三个儿子进屋来了,好心劝告说:
“妈妈,回家,不要太兴奋了,早点休息吧!”
回家的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安宁,屋子很温暖,过了半夜,外边刮起风,窗外的葡萄叶子抖擞着,墙根下的蛐蛐打着嘟噜,有点荒凉味道。
就在那工夫,我听到申蔚的被角动了一下,声音很轻,我问:
“你醒了么?”
“我醒了。”
“你想什么呢?”
“你的文集应该出版,哪怕自己买书号。”
“你不要再说了,你的健康就是全家人的幸福。”
申蔚再没有往下说,显得很温存,又很兴奋,有点像小孩子淘气对我说:
“你亲亲我吧!”
我亲了亲她,还想搂搂她,忽然想起她做过手术,身上还安着胶皮管子,医生曾经嘱咐说,尿毒病患者,最怕感染,我就把胳膊放下了。她问:
“你怎的了?”
“没有怎的。”
“你还记得那年延河涨洪水你浮洪水过河……”
“是啊!”
“当年我们来东北,和国民党夺天下,国民党坐的是飞机,我们用两条腿走路,我们首先占领了东北,这就是延安精神。”
“我多想看看我们幽会过的那块卧牛石啊!”
由于申蔚的病情不稳定,我俩在家住了三天,又回到了部队医院。虽然多次用药、输血,并没有控制住发烧。她常说胡话,我很不放心,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可怎么和医院联系。
我再三说服儿子,要留在医院护理,儿子们怕我累垮身体,把我留在家里。9月22日凌晨4点钟,儿子从医院派来一辆汽车,接我去医院,我问司机,司机不太清楚说:大概申蔚有话要和你说吧。我想申蔚的病好转了吧?还要买药么?我下了车,气喘喘地爬上医院楼梯,直奔熟悉的214号病房,心里直跳。今天的病房分外安静,灯光暗淡,被单上发出苦药的气味,医生和护士都不在屋子,我的儿子伏在床头上,脸色惨白,痛苦地哽咽着。申蔚还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仰着脸,已经闭上她那双聪明伶俐的杏仁眼睛,看着这情形,我的心都凉了。
“申蔚!申蔚!”
我喊了一声,两声,尽管我的心里有千言万语,她已经不能回答我了……